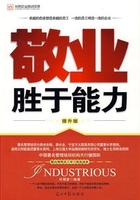耀柘孩子般的睡颜,却仍放下警惕。锦落看着,眼里酸涩。
忽然,耀柘一个侧身,环住了锦落的腰。他在梦中呢喃:“求你,不要再离开我。”
一句话,令锦落泫然泪下。她反环住他,将头轻轻埋进了他的怀里,模糊地呢喃着。恐怕只有窗外清冷月光可以听见,她在重复着什么。
我在,我在这里。
当锦落从晨光中醒转时,发现自己竟爬在床沿上。而床,已空空如也。昨晚照顾耀柘,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锦落起身,披在她肩上的什物也顺势落地。她回身,看见那件云纹缎面狐裘。俯身拾起,手指轻缓掠过柔软光滑的皮毛,锦落心里忽生暖意,有不顾一切的冲动。但转念间,她已将那狐裘放下。
忽然,一只鸽子飞进房间降落在窗棂上,朝锦落发出“咕咕”的声响。锦落赶紧走过去,迅速拿下了绑在爪子上的小纸条。匆匆看过后,就急忙毁掉了。恰逢这时,几个丫鬟提着食盒走了进来,将早点次第有序地摆放在桌上。
小米粥。芙蓉酥。水晶糯。甚至还有几碟开胃的小菜。锦落略微惊讶,自己不曾吩咐过早膳。问正要退出去的丫鬟,说:“是王爷吩咐的。”说完就退出了房间。锦落静默地看着桌上的早点,不辨悲喜。
呆立良久,她才坐到桌前,仔细地吃着眼前的食物。仿佛山珍海味琼浆玉露,需细细品尝。
一滴泪,砸碎在了青瓷花碗里。
这一日,锦落都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修剪盆景时将花尽数剪去。刺绣时戳破手指。收拾布置房间却又将瓷器打碎。最后,她索性百无聊赖地坐下来,看天光的转换。而心底,仿佛总压着什么东西,沉重而烦闷。
子夜时分,耀柘才回到王府来。锦落照例掌着灯,等候在屋子里。耀柘看了看锦落的房间,踟躇片刻,还是朝书房走了去。
耀柘刚在书房里坐下,锦落就已端着一杯安神的清莲茶走了进来。她依旧是低眉敛目,默默不语。她将茶放下后,便即刻转身朝外走去。忽然,一手上忽然传来的力道停止了她的脚步。
“怎么?既然敢来送茶,又何一副急于撇清自己的清高模样。苏锦落,本王倒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话一出口,便刺得锦落浑身一震。她勉强自己,扯出一个微笑:“王爷多虑了,妾身只是怕王爷辛劳,所以不便叨扰。”
“不要这样跟我说话!” 耀柘猛然拍案而起,盯着锦落的眼仿佛在火海里淬过一般。锦落忽然抬眼,势均力敌地对瞪回去,眼里满是倔强的闪光。不时,却渐渐蓄满了泪。以前,她何曾受过这等羞辱,更别说,对象是他。
两人在沉默中对峙良久。最后,锦落低眉就笑,虽说是笑,却藏满凄凉。两行清泪,也终于潸然而下。而忽然,耀柘一把拉过锦落将她狠狠地揉进了怀里,恶声气地说:“苏锦落,我是疯了才娶你进来这么折磨我!”
幽兰芬芳,暗香叠涌。锦落此时大脑一片空茫。这个怀抱,暌隔数年,竟还是这般熟悉。就仿佛深渊沼泽,令她情愿深陷,难以自拔。就如同穿越幽远的时光,落在她面前的,一枚等待已久的奇迹。
终于,可以在他的怀里,肆无忌惮地哭泣。
这时,竟有黑衣人破窗而入。手中利剑直刺耀柘后背而来。电光火石间,已是来不及隔档。锦落用力一转,那剑便穿锦裂肤,刺进她的身体里。顿时,鲜血逶迤而下。锦落意识模糊里,只听见喧嚣声中,那一句温暖如春:“不怕,我在这里。”
锦落从昏迷中醒转过来,距离被刺那晚已过去六个日夜了。当她睁开眼,竟看到耀柘趴在床沿上,睡着了。
难道,他一直不眠不休的陪着自己?锦落用手,轻轻落在了他的头上。那种温暖,又几乎让她落下泪来。或许是牵动了伤口,又有情绪的起伏,锦落不住地咳嗽起来。这将本就浅睡的耀柘惊醒。
他看到锦落醒来,眼里波澜不惊,却默默地执起她的手,放到自己的脸颊边,轻轻摩挲。看着锦落的视线,也是不动丝毫。最后,他用沙哑的声音缓慢地说道:“大夫说那剑上淬了毒。虽然伤口不深,却是极凶险。我真的好怕,你再次离开我。”
孩子式无力心酸的语气,令锦落一阵黯然。她抚摸着他因疲倦而颓靡的脸,柔声说:“不会。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随着日子的推移,锦落的伤也渐渐好了起来,却落下了畏寒的病根。眼看天气渐渐转凉,锦落出房门的时也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静静地坐在窗前,看窗外一片天高穹蓝,云卷云舒,眼底是一片难以化开的阴郁。
只有当面对耀柘时,才能勉强地笑出来。耀柘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只当是身子太虚,影响了情绪。于是他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
他们俩,仿佛回到了初见一般。那些隔阂仍是有的,只是不愿在去注意了。如今,没有什么不好。
某一日,阴霾的天空飘起了净白的雪粒。转眼,已入冬了。而父亲的案子,拖了那么久,也终于将有消息了。锦落有些落寞地想,却期待又惧怕着答案的到来。
这日,耀柘从朝中带回了消息。父亲的案子终于尘埃落定。死刑免去,改发配边疆,即日启程。锦落听得这一消息,只觉胸口一闷,眼前一黑,昏了过去。而心里的忐忑,也随着死去了。
原来,他竟还是这样恨着,不肯放手。
夜色深浓,没有一丝光亮,只有绵密的雪冷然而无声地悠然坠落。平西王府的后门被悄然打开一条缝。一个身影静而疾地走了出来,朝着在夜雪里静候已久马车走去。当身影完全消失时,马车忽然朝着前方迅疾地奔跑起来,激起一片尘雪。
空旷的街道,回响着马蹄溅地的清脆声响。
马车里,锦落抖去身上的残雪,面容憔悴,神色无光。而坐在一旁的,正是碧云庄少主沈怒,锦落青梅竹马的哥哥。此时他神情焦急,望着锦落却又欲言又止。最后脱口而出:“阿落,辛苦你了。”话一出口两人皆是一愣。
“拿去吧。一切都结束了。”锦落将方才一直紧紧拽在手里东西递了过去。尔后,将眼神望向窗外。
而接过东西的沈怒,脸上顿时一片欣喜。车内微弱的烛火,竟将他映出一片灿烂光华。
事情原来是这样。这一切,都是沈怒的设计。他说耀柘早已因着锦落的关系对苏家恨之入骨,所以苏老爷的突然获罪便是耀柘一手策划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对苏家手软。要救苏家,唯有将耀柘一举扳倒,而由沈怒在疏通人脉,可救得苏老爷。
于是,赌耀柘对锦落仍念旧情,去向他求情。本想是假意说以为奴为婢报答,混进王府,寻得机会偷得兵符。兵符丢失,乃是不可赦免的大罪,自然就能将他扳倒。却不想耀柘竟提出以娶她为条件,于是只能将计就计。
锦落是一直爱着耀柘的,对他亦抱有很深的愧疚,同时为了救父亲,她才甘愿在他身边忍受他的冷嘲热讽,她以这样的方式来偿还。
而中间的行刺,是沈怒为锦落进一步赢得耀柘的信任而设计的戏码。却不想,在这之后,锦落看着耀柘对自己的好,又重燃了希望,以为耀柘可以就此放手,两人便这样过下去。但当沈怒通过信鸽带来苏老爷的一封书信后,这种希望也渐渐熄灭了。
那信里不过写的是要锦落不必担心,但纸张上触目惊心的点点血迹,却刺痛了锦落的眼。而当最后得知父亲被发配边疆的消息后,彻底绝了望,这才将兵符偷了出来。而王府,也是回不去的了。
但一旦想到耀柘即将的下场,锦落心仍是一阵一阵地疼。那些不舍不忍,折磨得她快疯了。
寒风呼啸。黑夜里雪依旧绵密地下着。空明流光里,那王府里的亭台楼阁,莺光水榭,都已渐渐远去,最后隐没了。
这一场联翩的冬雪,终于下到了极致。
而锦落不曾料到的是,在她进入沈府后不久,便被软禁了。她不曾想,沈怒竟执意要娶她为妻。她不肯,便被软禁了起来。这次,她感到了彻骨的寒冷与绝望,如坠冰窖,生死不能。就连最后这个值得信任的人,也不复存在。
那日锦落正与沈怒闲聊,对方忽然唐突地提出:“阿落,不如,你嫁给我吧。”锦落吃了一惊,看着沈怒,摇了摇头:“不,沈大哥。我……上次就已说得很清楚了,我并不喜欢你,所以……”
“不要给我提上次你拒亲的事!”沈怒忽然大喝,继而冷笑,“今非昔比,嫁过人的你,还有什么资格再挑三拣四。”这一席话如同寒水,将锦落浑身淋了个遍。她的脸色蓦地苍白如纸。
沈大哥,怎么会成为如今的模样?在锦落的印象里,他一直是一个儒雅谦恭温和的男子。而她已不及多想,只是摇摇头,低声呢喃:“是啊,我已是残花败柳。如此不济的我,又何苦再来害人害己。”
“阿落,我……”沈怒欲言又止,口气也软了下来。最后没再说什么,走了出去,对外面的人吩咐:“照顾好苏小姐,她若不见了,唯你们是问!”锦落苦笑,她若跑,又能跑去哪里。
日子渐渐推移,沈怒的耐性也几乎被消磨殆尽了。这日,他再次愤怒:“告诉你,苏锦落,嫁不嫁,已由不得你了。”
“沈大哥,那等我爹回来,你如何向他交代!如果我爹知道你逼我,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爹?”沈怒忽然冷笑:“不放过我?难道他要请阎王来拘我的魂吗?他早就死在发配的路上了。不过,你还真是天真啊,到现在都还以为我会去救他。告诉你,当初诬陷慕容耀柘,就有你爹一份子。若非后来慕容耀柘傻到暗中保护他,他早就被王爷党给杀了。不过,我们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失败者知秘者继续活在这世上。不过他倒不是一无是处,正好利用他来牵引你上演这一出戏。不然,怎么能轻轻松松就获得这兵符?”
“这一切竟是你计划的?你利用我?我爹都是你害的?”锦落被这突如其来的真相淹没了,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已陌生至极的男子。“那,那耀柘他?”说到这里,锦落已哽咽难语。
“放心,他不会那么快死。等他来参加完我们的亲事,我再送他上路。”诡谲阴冷的话语,一字一句,寒进锦落心里,被砸碎。
世界颠倒。日月无光。
锦落却忽然乖巧,不再吵闹,顺从地接受沈怒的安排。而沈怒看她心灰意冷的模样,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终于,让锦落寻得了机会。
沈怒出府办事,锦落绕过守卫溜出了碧云庄。她一路奔跑,心里只想着再见耀柘一面,告诉他所有的真相。这强烈的意念,支撑她至今。至于以后,她不愿再多想。或许死,才是她唯一的出路。
终于,她冲到了门口。但门前的侍卫却并不放她进去。最后她不得不亮了自己王妃的身份。但那两个侍卫却只是鄙夷地看着她。仿佛眼前的女子不过又是一个攀龙附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