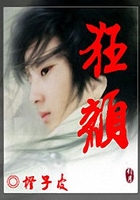第 56 章
待山脚下养精蓄锐两日后,无尘一行带领着两千士兵与五百工匠在依图所示的山岗下连续挖掘了三天,在第四天的早晨终于挖到了厚实的山门前。正欲着手开启山门之际,一飞骥掠进山岗,但瞧那生风的铁蹄就可认出一二,这匹宝马绝对也是出自西凉难得一见的骅骝宝马,相传汗血宝马便是由此马配种而得。这在中原大陆本就属罕见马种,更遑论是在岑北。
只见那匹比寻常马匹还要高出三分的骅骝宝马一路无阻驶到山岗前,纵将士还未反应过来,那马上一袭红褐色大袍者便已踏风翻飞着掠到了山门前,五步并作两步行至无尘跟前,单膝跪地时,一封蜡封的千里加急文书高举过顶,沉声道:“大王有命,无尘公子速速回城不得有误。”
无尘挑了挑眉,竟自接过呈上的文书,若非事态紧急,断不会令骅骝宝马赶赴送信。无尘未有耽搁,展开便匆匆扫视,瞬,眉头拧紧,回身看了看临进的山门,吩咐道:“易行留在此在看守,命士兵们将山门重新掩埋起来,整个山岗戒严,不许任何人进出,违者杀无赦。”
从未见过无尘如此严肃,易行未敢怠慢,垂首领命。
扫视了一眼在侧的南柯,又道:“国师就烦请荛将军代为送回,无尘先行一步。”
声过,人已纵身跃上了山门前的骅骝宝马之上,脚下用力一蹬,再一声高喝,马儿吃痛,蹄下犹自生风,踢踏着朝来的方向飞驰而去,众人只见一片扬尘飘浮,那一人一骥早已不见了踪影。
南柯犹自追上两步,却也被一时飘浮不散的扬尘呛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竟自挥着衣袂甚有不满,“怎么这样呢。”
“国师请吧!”
猛然间一个低沉的嗓音出现在身后将他吓得不轻,竟自抚着胸口愤懑不已,扭头便是嚣声不断,“你谁呀,将本国师吓坏了你赔的起吗?你有几个脑袋啊,大王可还等着我服侍呢,诶喂,你干嘛!啊……”随着一声尖叫迭起,那个荛将军与南柯的身影通通不见了踪影。
甫一进得皇城,无尘便一路从外九门急行至内廷,路遇宫人、内侍无不退避三分。但瞧在望的山门而不入,此事绝不单纯。而一向谨慎有度的无尘也会如此紧张,不竟要让人臆测,是景帝出了什么事?还是王朝内遇到了什么威胁?
待行至宫殿,景帝早在在殿中来回踱步不知多久,但见无尘进门便自向他迎了上去,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惊吓,拽着无尘的手腕,神秘兮兮道:“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回来找我报仇的,怎么办……”
无尘拢起眉头,景帝在信中所阵不尽详,他只知道伏军的那一对子女没有死,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却不知景帝在担心什么。
“父王,父王,他们就算还活着也对王朝,对您构不成威胁,您务虚过分担忧。”定住景帝的双肩,似想让他清醒些,但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无筝那家伙干什么去了。
“不,不,你不知道。”景帝犹自挥了挥手,踉跄着栽进宝座内,神色恍惚的继续说着,“伏君手下有一批比离石的神鬼军团还要恐怖的死士,当年若非他手下出现叛逆之辈,孤,孤怕是早已被他拉下了台。几日前有秘报传来,他的一对子女尚在人间,孤,孤担心他们会为了伏君复仇而卷土重来。”
“秘报?”无尘不禁重复咀嚼着这两个字,回望景帝时复又问,道:“可靠吗?”
景帝却是闭了闭眼,“这条消息的来源绝对可靠,你现在立马带兵前往渔阳将他们围剿擒回。记住,不要伤了他们。”但不知这后面一句是景帝突发了善心,还是良心难安而下不去杀手。但无尘却更是蹙紧了眉头难以舒展,看着景帝欲言又止,对于当年的事,他知之甚少。
越往北地,越感觉夏日的酷热,道路山林的苍翠逾发的稀缺,眼前的景致亦是越发的粗犷无垠。举目望去,成片成片麦田里的作物被暑气熏蒸的越发越发的金灿,麻雀扑翅着羽翼在田间地头来回的穿梭,不时的还能看见三三两两的农民支起身来擦拭擦拭额头的汗水,或是阵一大碗山泉来解渴,歇息片刻便又弯身收割着成熟的麦子。
含玉坐在马车里时感新奇,看着窗外的景致倒是认真的很。即墨是沿海之城,四季不分,一年到头都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景色,北地却不同,四季分明。她更没看见过一片麦子地可以这样的无边无际,犹似望不到尽头,她不竟要想,这样一片作物得收割到几时。
“累吗?”这一路,萧禹问最多的话就是,‘累了吗’‘渴不渴’‘饿不饿’‘要不要停下歇歇’
含玉总是摇着头,然后给他一个微笑,证明她不累,不渴,不饿,她就那样一路看着,听着进了渔阳。那是生她的地方,所以她想认真清楚的将它们烙印在自己的脑海深处。
“哥哥,你可以讲讲我小时候的事么?”突然回头,她发现自己好像还没从萧禹口中听到过关于自己儿时的事,除了在白帝城的半年时光,再之前的事她已没什么映象了。如今越来越临近家乡,她却又迫切的想要知道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的过往,那也将会成为她美好的回忆。
“你小时候……”看向窗外,神思悠远,那的确是值得回味的时光。他的眼眸亦是不自觉的放柔了,那浅藏的记忆便毫不掩饰的跃然于眼前。突然,他笑了,笑得既甜蜜又幸福,缓缓开口,幽幽道来。
“自从你会叫我哥哥开始,便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缠着我,不论是吃饭睡觉,就连我习武练剑的时候,你也要坐在一旁看着。有一日爹娘外出,令我在家好生看着你,可没想他们前脚刚出门,你便拉着我到后院的老槐树下,让我带着你树上去端鸟窝。”
犹自闭目感受着,恍惚回到了儿时,继续道:“我那时仗着学了几天功夫,便真就抱着你飞上了树头,只是下来的时候散了气,摔的不轻。而你,为了护住鸟窝,倒把自己的手摔骨折了。”
含玉偏头看向萧禹,柔声道:“哥哥当时一定很自责吧!”
萧禹点了点头,失笑,道:“我没想到你一个两岁的娃娃折了手骨不但不哭不闹,还转回头问我‘哥哥摔痛了吗?不哭不哭,萱儿给你吹吹。’”
含玉诧,失声道:“哥哥当时哭了!”
“是阿,看着你那小手上的斑斑血迹,我吓坏了,谁知道你却把那个完好的鸟窝递到我面前,说是把它安在屋檐下,鸟儿就不会被风吹日晒了。”
含玉亦是忍不住失了笑,她想,若换成是现在,她也会这样做吧!转念又问,“那爹娘回来,哥哥怎么办。”
“你不哭不闹倒是把娘吓得哭了好久,爹本来要揍我一顿,可是你那一副谁敢打哥哥我就跟他拼命的模样倒是令爹哭笑不得,后来爹就罚我闭门思过一个月。”
“哥哥,这些年你一定找我找的很辛苦吧!”抱臂倚上萧禹的肩头,心头苦涩难掩,想她这些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即墨,却也不想萧禹为了找自己得吃多少苦。
“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回来了,这,比什么都好。”伸手按住她的手背紧了紧,当年因一时的疏忽才导致他们兄妹失散十五年,现在寻回来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一路上,谣静却是睡的多醒的少,就连同坐一厢,她照样能美美的睡去。直到抵达渔阳,她犹自大梦初醒,看了看两人,呵笑着,道:“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你可以继续留车上睡觉,没人会赶你。”竟自将含玉扶下车,萧禹却未有好气的丢了句。
“我睡够了,等等我。”扶着车厢竟自跳下车去,追着前的的两人跑了上去,“这就是婆家了。”三人驻足一破败的庄院前,谣静犹自开口说着,没有什么不满,却是更显兴奋。
萧禹不甚喜悦,他倒宁愿谣静像在车内那几日一样,醒着的时候总是比睡着的时候令人讨厌。
近来谣静亦是越发面皮增厚了,对于萧禹依旧不甚待见的态度她倒是越来越无谓了,反正跟着,他迟早有一天要接受。
含玉却觉好笑,这样的两个人,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但又缄口不问他们之间的事,毕竟萧禹不喜说他跟谣静之间的事。
他们只是在庄院前驻足了一会儿,并未进到里面,萧禹带着她们又去到了另一个地方。
山顶的一片空地上寸草不生,就连方圆之内亦是没有半株绿荫。这个地方视线极佳,对于山下的城市一览无遗。空地之上赫然静置着两座大小一至的坟墓,周围亦不见有寸缕杂草,许是经常有人打扫的原故。
行至墓前,两方汉白玉墓碑上未见半个字迹。这不禁又要令人臆测,谁人这样粗心。
见状,含玉愣然转向萧禹,想要问什么却始终开不了口,眼中早已噙满泪花,这会儿再见此景,更是默默的淌着热泪在墓前跪下。
萧禹亦在含玉身侧跪下,看着面前的两座坟墓就像是又看见了他们一样,他笑了笑,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难得的轻柔,“爹,娘,孩儿不孝,时至今日才将萱儿寻回。从今往后,孩儿会将萱儿保护好的,你们放心。”
“爹,娘……”含玉亦是痛呼着叩伏在地上,声音早已哽咽,一时悲恸的难再说出一句话。
萧禹竟自将含玉扶起,轻拭着她的眼角,展颜一笑,“傻瓜,回来了,该高兴才是,你这哭哭啼啼的该让爹娘伤心了。”
含玉忙又握住萧禹的手,甚是不解,“为何墓前空碑,这让爹娘地下怎安生。”
是阿,不孝的子孙才会对先人做出此等行径,且不论其他,单以此就可逐出家门,死后不得入本家宗庙。
萧禹扯着嘴角露出一丝苦笑,转身踱至山边,看着远方,一时默然。
“为何?”含玉却是非要得出个所以然,见萧禹默不作声,便就追至身后,又问。
幽然的叹息声从萧禹的口中传来,犹自隐忍着,淡淡道:“当年那近乎毁灭性的一役使得不落王朝几乎覆灭,爹是主导者,事败后落井之声四起,景帝更是为了以儆效尤,决议以渔阳为首的代君,云中君,湘君,乃至越君处以极刑,而渔阳所有参与谋反之辈不论身份地位,皆处诛族之罪。”
但听萧禹毫无情绪波动的述说,含玉咬了咬唇角让自己不至哀恸的痛哭出声,别过头,却是忍不住泪涌如柱。
萧禹继续道:“危急时刻,虔忠将军以自己的一对儿女换了我们,乐先生与斐将军各自带着你我连夜出逃,可,当我们逃至国境之南时,斐将军却在路上不甚与你失散。”
“斐将军也是因为此才上落霞寺出家,他觉得对不起爹娘,更无颜面对为此而牺牲的虔家子女。他虽然一直不说,可是我知道,他当时被大批追兵围捕,若不将你藏匿,成擒必是两人难逃。只是,当他回去找你的时候,你早已不见了踪影。”
“事后我们暗地里散发了一批死士在南地方圆百里搜寻,可使终没有你的半点音信。待我们回到渔阳,已是两年之后,乐先生通过一些江湖朋友,将爹娘的棺椁迁回了渔阳。当时王朝内仍是不遗余力的四下搜捕着各地叛君的余党,乐先生始终不敢在墓碑上落款,生怕让他们寻出蛛丝马迹。自那以后,他便带着我离开了中原,去了关外。”
待将这一段辛酸的历程道出,萧禹亦早已泪沾满面。不是不会伤心,不是不会落泪,更不是不记仇恨,只是这么多年时光已令他看开了很多事,争那一时的名利不如纵马江湖来得痛快,这天下谁爱争谁争去,他不稀罕。如今已寻回了含玉,他再也无所求,只要将她带去关外避世,此生便也无撼。
一阵残风卷过,天地之间悄然了没入了黑暗的怀抱。薄雾亦是在悄然胧住了整片山间。依稀的,还可听到一个微弱的脚步声从蒙胧中走来,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渐渐在薄雾中显出形来,看着又让人觉得是个熟悉的身影,他就那样径直朝着山地里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