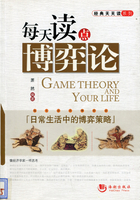盯着那颗石榴,眼眶忍不住发红,腹中又是翻腾不定,心中像是嚼了苦莲子止不住的酸涩,“呕!”的一声将早膳全部吐了出来。
背后被人轻轻拍着。
好一会,她才将胃里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只剩下干呕,一方丝帕递到她的眼前,“霍帝师莫要惊慌,这红果虽然剧毒,可只要没有破开那层表皮,便是无妨碍的。帝师恐怕忘了,这方红果园还是你下令种的。”
只有那个变态才会种这种东西!她不该感到奇怪的!
霍凤恼了恼,心智微清,忙接过那方丝帕先拭去面上泪痕才站了起来,赧然,道,“对不住,这帕子我会再还你一块。”
冷和笑了笑,伸手托住她的腰扶着她站起来,眼里俱是复杂莫名的神采,“不妨事,我送你回去吧。”
沿着长廊往前走,霍凤有些尴尬了。
她看看托在她腰侧的手,再看看两人几乎要靠在一起的身子,鼻息间尽是淡淡的药草香气。最后抬头,身旁的男人很淡定的走着他的路,似乎丝毫没有感到这样的亲昵有什么不对。就是那股子淡定,让她几次想说“您老能不能离我远点”只得吞回肚子里。
冷和的气质跟她那个恨不得踹死偏偏又忘不了的初恋有八成相似,再这么走下去,她怕她会狼心蠢蠢不由自主再陷下去。不成不成,前车之鉴尚不远矣,这人又是霍凤的准妹婿,姐妹为了一个男人大打出手这种事情实在是太狗血,她可不能放手抢下去。
怎么办,怎么办?
她的眉头全部皱在了一起,又是激动,又是叹息,表情变幻不定的如同开了染坊。
冷和瞥了她一眼,些微笑意闪过眼底,却是抬眼,继续淡定的往前走。紧贴在霍凤腰侧的手松了松,听到她稍微舒了口气,他暗笑,手再贴了上去,比刚刚贴的还更紧一些。
她舒了一半的气登时又吊了上去,急促的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
他上扬嘴角,好不容易将笑意给憋了回去。逗她,其实很好玩。
她倏地往下一蹲,“我鞋带掉了!”
冷和愕然,低头看向她的脚,她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大脑登时有些断线。
她今儿穿着的可是一双白色软缎莲花朝鞋,别说是鞋带了,连一条线都没有。
冷和再也忍不住,背过身子朝着碧水蓝天,肩膀不停的抽搐。
抽吧,抽吧,看抽不死你丫的!
霍凤发恼,面无表情的站起身,假笑,“冷御医您慢慢笑,我先走了。”
冷和微笑颌首,“帝师慢走,我想起来我太医院还有事情要做。”说罢,他拂拂自个儿的衣袖,云淡风轻的,离开。
背影很潇洒,翠白的御医朝服在翠柳之间显得风姿潇洒。妈的,看的霍凤忍不住磨牙骂人,现在想起有事情要做了,那他刚才跟她磨了那么长时间是干嘛来着!
不远处亭台上,有两人坐着下棋。
棋盘上黑白纵横交错,但黑子已经好久不曾落下了。执黑子的手纤细而洁白,食指间残留着残红,恍若鲜血。
看着霍凤与冷和往相同的方向离开,夏侯逸才收回视线,漫不经心的笑,“看不出来,原来冷和到如今还存着这样的心思。只是不知道霍帝师会如何处理,这戏越来越好玩了。”
司马天熙哼了声,黑子落下,淡道,“你输了。”
夏侯逸呆呆的望着自个儿被杀的片甲不留,一点情面也不留的的棋盘,抬眼,面前唇角含笑但眼底全是凶戾煞气的皇帝陛下正在很有闲情逸致的拾子,嘴角不由抽搐,“陛下,您其实可以再杀的狠一点的,没有关系。”
忽的想起流传在宫闱间一个非常隐秘非常不可信非常荒谬的传闻来。
他心一跳。
莫非……不该吧……明明是对头……他胆子小,千万别吓他。
可是,他怯怯抬眼,打着哈哈试探道,“陛下,那天是你在小巷子发现霍帝师的,霍帝师她……”话还未说完,就见着对面的男人冷冷的开口了,“根据约定,你明天必须要去千荒山替孤去取白凤花。”末了,他还加了一句,“亲自去取,否则孤饶不了你。”
“什么!为什么要我亲自去!白凤花可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你想要我死吗!”夏侯悲了,怒了!
司马天熙丢给他一记冷眼,起身,离开,毫不拖泥带水。
夏侯逸盯着那个毫不留情的背影,悲愤莫名,为什么他会有种错觉这人是在迁怒,彻头彻尾的迁怒。
错觉,一定是错觉!
一阵劲风拂过,好冷。
一切都在进行着,像是按照某人安排好的脚本一般,巧合的,让人不由不感慨那位剧作家的狗血。如果,这是一本小说的话,如果她是其中的主角的话,霍凤真的要叹一声气了。
老爷,你其实可以更狗血更糊涂一些,但小的只想安分守己的做一个配角,攒够全部的钱,然后逃到所有人都找不到她的地方。
鉴于天启王朝没有办法可以长期保存尸体,所以前日如夫人的尸身便入棺安葬了。除了小园子眼睛红的像只兔子以外,下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她流眼泪。仿佛那棺材里躺着的不是一个曾今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只无关紧要的畜生。
凉薄的让她忍不住心惊。
沈今笑,主子愈发心软了。
她睁大眼睛脸不红气不喘,年纪大了,本来就是会心软的。
然后看着沈今笑的一脸的莫测,仿佛自个儿的所有的秘密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了。再然后,仓皇逃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