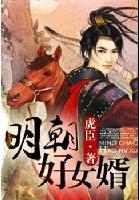这支骑兵队伍,最少有七成是自张守仁入大别山后精挑细选出来的豪杰之士,之前有不少就是杆子土匪中的强悍之徒,经历过在山中长达半年的魔鬼训练,再有大把的银钱和赐给的田宅奴仆,每一个人均是敢战死战的亡命之徒,前番张守仁攻掠至归德,再有在正面战场打败李擅的三万大军,这支突骑军亦是飞龙军中的主力。
因为太过缺乏战马,无法大规模的组建骑兵队伍,张守仁决意以精博众,要以少量的骑兵队伍,在局部战场上对抗那天下无敌的蒙兀强兵。
有了这个决定,他方才以手中最强悍的主力,全部交由吴猛,正式组建成军。按他原本的想法,这突骑军需以高头大马,以泰西人那般的全身锁甲和钢板,加上罩住整个头部的头盔,再把战马以全身披挂,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装骑兵。只可惜,战士还可以通过挑选的锻炼来寻找,而负担起重达三百多斤的武器、装备、盔甲的战马,却是当时的中国无处寻找的。虽然不能如愿,却也是尽量减轻盔甲的重量,突出重点部位的防御,在战马头部加上防护,如此一来,也是当世之时,中国大地上最装备最为精良,战力最为突出的重骑兵了。
这样的重骑兵,虽然在机动性上比之中国一惯的轻骑兵要差上一些,在防护和冲击力上,却又强过许多。当年金人攻下宋朝时,使用的铁浮屠,拐子马,便是在防备上还要越过突骑兵的重骑兵。只是使用不当,被宋将以长刀破之,自此之后,中国便再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重骑,这不能不说是在冷兵器战史上的空缺与失败。
蒙兀人西征时,征至匈牙利时,该国除了自己征集大军,又有波兰人三万人来援,蒙军主帅是身经百战的速不台和哲别,在正面战场相决时,蒙兀人无论是远射的重型大箭,又或是骚扰用的小箭,都无法伤到波兰骑士的重型板甲。好在速不台经验丰富,一看对方如此难打,干脆下令全军后撤,让波兰骑士误以为蒙兀军不敌,纵骑追赶,而蒙兀军全做两队,在两侧将三万波军全数包围,以小箭射伤敌军战马,然后重骑兵以长矛和铁锤击伤打死那些倒地的波兰骑士,象波军这样的重装骑士,主要是以正面突击来打跨敌人,面对敌人无休止的后撤,袭扰,毒烟,铁矛,终于溃败不敌,全军逃散。而蒙军一见对手逃窜,立刻放开通路,任凭他们逃走,一边以优势兵力打跨来不及逃走的敌人,一边轻骑追杀,波军队列散乱,溃不成军,装甲笨重,单兵做战完全不能发挥其战力,这一战后,主力尽陷蒙军之手,全国震动,连西欧的法国等诸多大国,皆是惊慌不已,整个欧洲即将面临着蒙兀铁骑无情的践踏。若不是窝阔台大汗突然逝世,蒙兀主力回到草原选取新汗,以当时欧洲落后的战术思想和战法,必定会惨败在蒙兀人手中。
有此一役,后世之人常以为重骑兵面对蒙兀轻骑全无办法,或是蒙兀人队中全是骑射手,而没有重骑。其实这都是后人的误读,蒙兀人不但有重骑,而且均是身强体壮,擅长勇猛之士,当敌阵无法突破,防御坚实,射手无能为力时,均是重骑兵以坚忍强悍的战意,不畏死伤,勇猛直前,而在蒙兀之前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因为没有重骑兵来突破敌阵,威压敌军,仅以骑射手来做战,是以在战斗力上极其有限,并不能对中原王朝造成致命的打击和伤害。而蒙兀人不愧是一个天生用来征战的民族,在开初只用骨头箭矢打猎和征战的弱小民族,迅速壮大和吸取了各族中先进的战争经验和先进的武器,拿为已用,方才成为当世时普天下无人能敌的劲旅雄师。
张守仁决意投入所有的力量,一定要在飞龙军中建立一起一支精锐无敌的重装突骑,就是知道,在很多时候,步兵行动缓慢,对着游牧民族的骑兵队伍,守备有余而进取不足,就是能在正面战场上打败敌人,也无法扩大战果。这也是在蒙兀人初兴起时,金国或是夏国,甚或是花刺子模,都偶然打败过蒙军几次,却并不能扩大战果,而蒙兀人四散而逃后,又迅速集结,稍事休整后,强悍的战士就能又再一次对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敌军以致命的打击。如此一来,敌军自然是大败亏输,一溃千里。只要飞龙军内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集中所有的战马和精良的战士,长年在马上征战,时间久了,自然就有一支可与敌人正面硬撼的精锐骑兵,进可攻,退可守,庶已可以一扫前弊。
突骑军如此重要,军营并没有设在别州,而是直接就在颖州城内,放在张守仁的眼皮底下,军中稍有动静,便可立刻知晓。吴猛是一员难得的大将猛将,却并不是跟随他打下基业的心腹,军中将领,对他多有猜忌之心,张守仁命他为节度副使,诸将并无疑虑,副使的虚职,并无作用,到是这突骑兵马使一职授与吴猛,使得众将心中疑惑,不知道张守仁是何用意。
与前些时日在第一军营外所见不同,突骑营的营门,却并没有那么大的规矩,张守仁一行数十骑,只在营门前略一停顿,那把守营门的别将并没有要求验明符信,就立刻放行。
张守仁见他一脸憨笑,立身营前,忍不住呆着脸问道:“这别将,怎么不加验查就放人进营?军中不比别处,怎么可以如此随意?”
那别将向他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然后方笑道:“末将虽然是在大别山中才跟随大人,不过也算见过大人几十面了,说句不中听的,大人的相貌别人还能伪装,这种气度神情,举止风范,是一般人能装的了的?因为如此,末将这才不必查验,就直接放入营内。”
“喔?可是本使在第一军营前,守营的军将,虽然明明认得本使,却仍然认真查验,然后方才放行。吴兵马使当日也曾随行,他没有和你们宣讲么?”
那别将淡淡一笑,答道:“吴兵马使确实是讲了。对第一军的训练和军纪,很是赞赏。不过,他也说了,军人虽然一定要遵守军纪,却也不必太过教条。心眼活泛到不守军纪固然不好,不过一切全照着规矩来,一点儿血气和变通也没有,那也不是一个好的军人。”
见张守仁神色木讷,他也不知道这节度使大人是喜是怒,只是将心一横,又道:“其实末将也知道大人的意思,是要军人们眼中只有军规。只是,咱们到底是大活人,不是笨蛋和蠢才,若是连大人也要查验,那将来有人要对大人不利,只要符信下来,咱们也听命不成?”
他这话一出口,张守仁旁边的一众亲兵一起喝骂道:“真是大胆,当真无礼。”
有那动作快的,已经跳下马来,意欲上前将那别将擒拿。
张守仁面色一寒,喝道:“谁叫你们动手的?”
那几个亲兵讪讪停住,不敢再动。却听张守仁笑道:“你的话,近似狡辩,不过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当年周亚夫将皇帝挡在细柳营外,虽然得了赞誉,其实也得罪了皇帝。军队到底是谁的军队,他周亚夫也是迷糊了。”
说罢,哈哈一笑,不再与这别将多说。打马一鞭,冲过木栅营门,向内里而去。
每个将军都是不同的性格见解,张守仁自然不会苛求每人带兵的风格一般相同。军纪重要,不过打造一支有灵性,有着将领强烈个人风格的军队,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他现在考究的,不是吴猛在这些小事上的作法,而是他整训军人,训练战术战法的手段方法究竟是不是与自己一般无二,能达到让突骑军在飞龙军中首屈一指的目标。除此之外,其余的小事便由得他就是。
这军营占地甚广,原本在颖州城内,很难寻得这么大一块空地以做营地。只是这些年来兵荒马乱,人口离散,城西这一片大量的民宅荒废闲置。前次战时,不少房屋被拆平,或是充做栅栏,或是修成壕沟,拆平了大片民宅之后,便空出这么一块地方,稍加修整,又建起大片的木屋做营房,其间有过千亩大的地方用做演武场,虽然比在城外寻一片地方做兵营还要窄小一些,却也勉强敷用。
由营门而入,一路西行,约摸过了小半里路,一路上的营房却是空空如也,待接近军营正中的校演场时,方才看到前面尘土飞扬,乱糟糟厮杀叫喊声渐渐响亮起来。
再稍近些,便见几千名突骑将士,骑于马上,身上披着的却不是制式的黑色盔甲,而是更加沉重的校演用的板甲,连同头部,均是深藏其中。而战马身上,也是披挂沉重,跑动起来,扬起了大片的尘土。
张守仁止住亲兵和营门守卫的通报,并没有太靠近正在进行战术演练的突骑将士。他咪着眼看了半响,待见到所有的突骑将士均是身负着两倍沉重于制式盔甲的板甲,手中拿着比平常重两倍的武器,却仍是动作如常,并没有显的特别疲 惫,挥手动作之间,仍然中规中距,并没有特别的混乱。
只是除此之外,这些混乱中的骑兵殊无战法,一个个分成小队,来回胡乱冲杀,甚至连最基本的小队的队列也并不能保持,不少战士,只是凭着本能和自己的勇力,在胡乱砍杀。
他正欲前去讯问,却见吴猛亦是身着重甲,骑着战马巡唆到自己身前不远,向着几个连人带马倒在地上的将士大声训道:“你们这群小子,鸟毛没长齐,就敢在我面前强横。说什么队列训练,战术突进,现在看看,一个个成软脚虾了吧?都给老子起来,继续打。”
说罢,连吐几口唾沫在那几个将士身上,却是边吐边笑,又叫道:“老子有言在先,凡是训练时摔倒的,大伙儿想怎么就怎么,不想做孬种的,就好生照管自己的马,好生锻炼自己的力量,什么战法?真的打起来时,靠的就是自己有力气,战马靠的住,有这个基础,再练习队列。你们现下的实力,也就比楚军强一些,遇着蒙兀人,那只是一个死字!”
他如此蛮干,张守仁身边的亲兵均是看的咂嘴不已。再扭头看那几个陪同进入的营门守卫,均是一脸苦色。
张守仁招手唤过一个守门突骑,向他笑问道:“怎么,吴将军练兵,全是这般练法?”
那小校苦着脸道:“可不是。吴将军自从接了印,从不按以前的法子来练兵。都是让咱们拿着重兵器,战马都是戴了重甲,就这么从早打到响午。下午就举石块,练身体。这么些天下来,兄弟们一个个都累的吐血。人也算了,现下的突骑营中,就是战马见了吴将军,也得打哆嗦。”
张守仁听的发笑,仔细打量那突骑军人,见他虽然是在叫苦,脸上却是神采奕奕,精神十足,身上的衣甲颜色破旧,兵器破损,却仍然是掩不住的勃勃英气。
他又问道:“吴将军可曾说过,为什么要这么练兵么?”
那小兵精神一振,答道:“他说了,什么狗屁战法,阵形,到了战场上一个个是孬种的话,再好的阵形也没个鸟用。就咱样这群鸟人,也敢称什么精兵,他非得把咱们的卵子操练下来,挺的住的才是精兵,挺不住的就滚出突骑。”
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向张守仁道:“这吴将军也是个猛人,校演场上可是一点情面不留。说来也怪,这样练法,咱们虽然是累的跟狗似的,心里却也是痛快。只盼着将来能在战场上,痛痛快快的厮杀一场,不能让这狗头低看了。”
他显然是和同僚在私下里骂过不少次吴猛,此时回张守仁的话,却也忍不住带出来“狗头”两字,待说完之后,猛然省悟,立刻吓的脸色惨白。
张守仁却恍若不闻,只低头沉思片刻,便笑道:“算了,这里不必看了。咱们立刻出营,不必打扰吴将军练兵。”
他如此吩咐,旁人自然不敢多说,一众亲兵在守营突骑的带领下,又从来路返回,迤逦而出。一众亲兵拿眼去打量张守仁的脸色,只见他微微带笑,显是愉悦之极。各人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都知道他对军纪和队列操演要求极严。飞龙全军之所以屡败强敌,就是靠的军纪和战法。而今日吴猛这般的做法和说法,等若是挑战张守仁在突骑军中的权威,他不但没有半分恼怒,反而面露喜色,当真是奇之怪之,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张守仁心中却也是百味杂陈,一则以喜,二则以忧。喜的是吴猛这样的练兵法,显然很配合突骑这样性质的骑兵队伍,男儿热血,豪杰志气,照这样练法,到后来再加上阵法演练,突骑必定会成为一支无敌雄师。忧的便是将领的个人魅力太强,使得麾下将士归心,现下的三千突骑是张守仁手中的王牌,主力中的主力,对张守仁忠心不二,但是就怕时间长了,对吴猛也是言听计从起来,不免有些忧心。
“大敌当前,还是不要想这些无谓的事好。”
他心里嘀咕一句,摇一摇头,把这些不好的想法驱赶出去。突骑军中,有着大量的间龙细作,还有军正司下的军法官,再有各级的军官,都是跟随他时间很长的老人,料想各人就是对吴猛归心,也不会有什么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