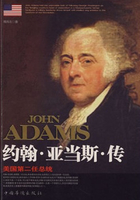1928年他们一同到上海,一起住进萨波赛路的一座公寓。丁玲与胡也频住二楼,沈从文住三楼。他们共同创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周刊。1930年“红黑书店”因债务问题倒闭。为了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胡也频去济南教书。第二年,因胡也频宣传革命思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当时,丁玲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处境很艰难。沈从文陪同她将孩子送到湖南常德的母亲处,由母亲抚养。此间,沈从文对丁玲热情相助,关怀备至。不料这年的秋天,丁玲却与冯达同居了,沈从文心中非常恼火。此后他与丁玲就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在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的文章,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绑架、陷害作家的不法行径。还曾托请胡适通过当年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营救丁玲,但未能奏效。
1933年社会上传闻丁玲被害后,沈从文写了《记丁玲》及《记丁玲续集》。此书于1939年9月在上海出版时,丁玲已经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来到延安。在陕北的丁玲对沈从文的这两本书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的冬季,一位日本友人将这两本书拿给丁玲看,丁玲觉得沈从文在书里对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评价有失公允,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她还对沈从文以低级趣味描绘他们的生活非常恼怒,沈从文在他的文章里说,他和丁玲、胡也频曾经同住一处,朝夕相伴,给人一种混淆的概念。丁玲认为用含混的语言混淆视听,这无异于往她的身上泼污水。后来丁玲还听说她被捕后,沈从文胆小怕事,不敢出面营救她的传闻。从而得出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的结论。这种伤害沈从文的感情之言,挫伤了她与沈从文几十年的情谊,由误解而反目,导致两位老友在晚年分道扬镳。
亲情沈从文是画家黄永玉的表叔,年龄比黄永玉大21岁。他们被称作是湘西飞出的两只“金凤凰”。
黄永玉是常德人,他的父亲黄玉书毕业于常德师范,在男小学当校长,曾以通草作画捧回巴拿马赛会铜奖;母亲杨光蕙毕业于桃源省立二师,在女小学当校长。父母在读书时学的都是音乐和美术,对黄永玉的未来发展留下了遗传基因。在黄永玉1924年8月出生后不久,他家就搬到凤凰县居住,从此黄永玉与他的表叔沈从文成了名副其实的乡党。
黄永玉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读小学时。有一天他正与几个伙伴疯跑,忽然有个伙伴告诉他,他家从北平来了客人。祖母告诉他这是他的二表叔沈从文。沈从文摸摸他的头,将他揽在怀里,很喜欢这个小表侄。少不更事的黄永玉听说这位表叔在北平当教授,写文章,并没有怎么在意,过一会儿,便跑去与小伙伴玩耍去了。
黄永玉从16岁开始以绘画与木刻为生,到处漂泊。在福建德化山区做小工时,老板见他头发太长了,给他一块钱让他去理发,可是他在书摊上见到一本表叔写的《昆明冬景》,便花了七角钱买了下来。他读着表叔写的书,对表叔的才华滋生了无限仰慕的感情。
1946年他才开始与表叔沈从文通信。这些信有谈艺术知识的,有谈艺术欣赏的,对黄永玉的未来发展大有补益。本来黄永玉名字中的“玉”是“裕”,是沈从文说他的名像个卖布的,建议他改为现在用的“玉”字的,意思是永远继承父亲黄玉书的艺术才华。沈从文曾在一封信中向黄永玉介绍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一是充满着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是摔倒了,不要停下来哀叹,要赶快爬起来往前走。三是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这样的教诲成了黄永玉的座右铭,也成了指导他前进的一盏明灯。
1950年沈从文动员在香港的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1953年黄永玉回到北京到中央美院任教。叔侄都住在北京,彼此的联系多,也经常走动。“文革”开始后,他们叔侄俩都成了审查对象。有一次在大街上他们邂逅了。沈从文怕连累表侄,装作没有看见,便走了过去。毕竟黄永玉年轻些,胆子大些,他借擦身而过的瞬间对表叔低声说:“要从容对付呀!”这句话表达了亲属间的惦念与安慰,对沈从文也是个很大的鼓励。
(75)情谊与巴金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张允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带着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巴金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马上给他们发了贺电,祝福他们“幸福无量”。不久,巴金来到北平时,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里。尽管沈从文新婚燕尔刚刚一个多月,但他们夫妇对巴金这个好朋友却是相敬如宾。他俩都在酝酿着新的作品,舍不得花时间闲聊,就分头搞起了创作。北方的秋天气候宜人,沈从文将书房让给巴金创作《雾·雨·电》中的插曲《雷》,而自己却在院子里的树阴下写自己的《边城》。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看望他们新婚夫妇,巴金才搬离沈家。
抗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沈从文的灵魂出现了迷乱。他“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其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为他的前途担忧,就通过朋友传话,劝导沈从文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遗憾的是沈从文没能够听从老朋友的劝告。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在3月28日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寻求解脱。幸好他的妻弟及时发现,挽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沈从文家门庭冷落,很少与朋友往来。
1949年7月,巴金应邀到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多次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到沈从文家拜访。同年9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协会议时,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沈从文最为消沉与寂寞的时候,巴金的友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巴金和沈从文都自身难保时,仍然惦念着对方。“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往来就更多了。可见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挫折考验的。
与胡适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称。1923年他刚刚闯北平时,的确是个“乡下人”,可是,自从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之后,他在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逐渐成为现代绅士派的自由主义文人。
本来,沈从文不会教书,可是在他与好友胡也频和丁玲到上海办刊物《红黑》时,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经营一年不仅没有盈利,反倒将本金也赔了进去。为了谋生和偿还债务,他们三人只有分头找工作赚钱。于是沈从文经徐志摩举荐,认识了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被聘为大学一年级现代文学课讲师。接到胡适的聘书后,沈从文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谈到自己不会教书,并表示,如果学生们不满意随时可以撤换。胡适对他极为重视,尽管第一堂课沈从文被“挂”在了课堂上,可是胡适并没有怪罪他。
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成了沈从文的知心朋友,事无巨细,沈从文都乐意与胡适请教和商议。当时,他花钱没有计划,经济拮据了,就写信给胡适要求预支工薪,还要求帮助他的妹妹暂缓交纳学费,胡适都给予满足。在教课时,有一个女学生引起了沈从文的注意。这个女生就是年仅18岁的张兆和。在沈从文与张兆和有了个别接触之后,他觉得口头表达不出他心底的感情,就给张兆和写了封表示爱意的信。张兆和没有回应,沈从文痛苦万分,便找到胡适,提出几个离开公学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他陷于爱情的漩涡,爱上一个女生。胡适劝他不要走,他会为他“做一切可做的事。”
不久,校园里沸沸扬扬地传说沈从文求爱不成想自杀。这个传言传到张兆和的耳朵里,她很害怕,便拿着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胡适仔细地听了张兆和的叙说之后,首先表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小说家。当胡适得知张兆和并不爱沈从文时,胡适希望她能与沈从文做个朋友,还劝说给沈从文写封婉转的回信。最后胡适答应劝劝沈从文。由于胡适的协调,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回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经过三年多的爱情拉练,沈从文终于赢得了张兆和的爱情。
1930年5月,胡适联合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胡适离开后,沈从文也觉得失去了靠山,同年秋天也辞职离开中国公学。此后的十几年间,胡适与沈从文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们的通信联系一直未断,直到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不久又去美国,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通信和会面了。
慈师1939年至1947年沈从文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西南联大的教室很简陋,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只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先到的男同学占据了扶手椅,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听课。沈从文看不过去,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地,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他们的心中就只能充满了感动。为让学生省点事,沈先生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找,作为老师,指明方向也就算尽职了。而沈从文却自己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是夹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学生们接过沈从文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