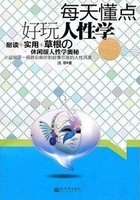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60)气节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墨,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1945年“一二·一”惨案以后,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表面上附庸风雅,居然送了一方玉石来,请闻一多刻印,限两天刻好,答应润例优厚。对此,闻一多不屑一顾,将玉石原样退回。特务对闻一多恨之入骨,公然把大街上商店中的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砸烂。
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的民主运动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安,他们派出大批特务四处活动,并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公然闯进几所大学,用枪弹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挥笔写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悬挂在“一二·一”四烈士的灵堂上。
国民党特务把他列为黑名单的第二名,有人劝他尽快离开昆明,都被他婉言谢绝。在李公朴治丧委员会举行的李先生殉难报告会上,李公朴夫人讲得泣不成声,被扶下讲台。原来没有准备发言的闻一多突然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婚事闻一多先生的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办的。早在1912年,14岁的闻一多刚考上清华大学时,父母就为他订下了娃娃亲。对象叫高孝贞,黄冈路口人,比闻一多小4岁,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和闻家还是姨表亲。闻一多考上清华大学后,高孝贞的父亲就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便主动来到闻家,提出要将女儿嫁给闻一多。闻一多的父母一想,如果闻、高两家能对亲,那就是大好事,既是门当户对,又是亲上加亲。
1922年初,就在闻一多赴美留学前夕,他接到父亲催他回家结婚的信。对于这门婚事闻一多很不满意。但是,闻一多是个大孝子,还是回到了家乡,答应与高孝贞结婚。不过他向父亲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不向长辈行跪拜礼;二是不拜祖宗;三是婚后让高孝贞入学读书。父亲本来认为儿子的这三条提得不合理,但为了这门亲事,也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婚后的高孝贞为人贤惠,也很能干,善解人意。因此,夫妻之间彼此也十分恩爱。不久,高孝贞女士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进校后由于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加之有闻一多的熏陶和感染,高孝贞也从一个生活伴侣,逐渐成为了闻一多先生事业上的有力支持者。
教化闻一多在“诗化教子”中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诗歌,而且通过对诗的评析,向孩子们进行了爱国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陶冶性情,培养情操。在给孩子们讲诗时,闻一多一般半靠在床头上,手握诗卷,逐字逐句逐段地讲解。有时引经据典地详细解释某一单字或单词,有时介绍历史背景,有时趣味盎然地讲解某个典故,或剖析诗文的意义。闻一多最重视历代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开新诗人,像对“初唐四杰”、张若虚、陈子昂、孟浩然等人的诗,都大讲特讲,赞扬他们为盛唐诗歌扫清道路、开辟新局面的不朽功绩,赞扬中国“人品重于诗品”的优良文学批评传统。
闻一多往往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对所要讲的诗进行评论,凭着对诗歌的特有理解,在讲清诗的含义后,他还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呃,真好呀!你们看,还能比这句写得更好吗?”分析作品时,他就像成了诗人的化身,在叙述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讲到精彩动人之处,连他自己也融化到诗情诗景里去了,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使得孩子们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受。闻立雕在闻一多百年诞辰时著文说:“这一年,听父亲讲诗讲文,收获极大,提高了古汉语的知识水平和欣赏能力;增长了对古代社会与历史的了解;陶冶了情操,特别是开始懂得人间既有真善美,也有黑暗与邪恶,启发和培育了我们对受苦受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与邪恶势力的憎恨。”
闻一多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品行。一天,闻立雕在家里玩得忘乎所以,把做作业的事丢在了脑后。闻一多问他怎么不做作业,他怕挨批评,就顺口撒了一个谎,说老师没留作业。但闻一多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是在撒谎,就非常果断而严厉地批评了他。难能可贵的是,重视“诗化教子”的闻一多,在家教中还能勇于向孩子道歉。有一次,他因一时气极而责罚了小女儿,事后主动道歉。此事使其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形象显得特别高大!
知己臧克家与闻一多的相识是在青岛,那是1930年的夏天。臧克家是青岛大学英文系的新生。开学之后,臧想转到中文系,就去国文系主任办公室找闻先生。当时有几个学生都想转,问到臧时,先生问:“你叫什么名字?”“臧瑗望”(臧是借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以《杂感》中“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的诗句见之于闻一多先生了。
此后,臧克家读了闻一多的《死水》,便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觉得如今才找到适合自己创作诗歌的途径。
对《死水》,臧克家几乎全能背诵,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对臧的诗,闻是第一个读者。一次暑假,臧克家把自己的《神女》寄给老师,寄回来时,闻一多在自己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打了红的双圈,让臧克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1932年夏天,学校里因为考试制度定得太严发生了学潮,同学们把责任全推到闻先生身上,有些人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处之。暑假之后,他便转到清华大学去了。他在给臧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以后,臧一直在战地上跑,偶尔在画报上看见闻先生的照片,胡须半尺长,成了清华有名的四大胡子之一。臧每隔一年半载就给先生写封信,以表怀念之情。后来,闻终于回了一信。臧自是十分惊喜。劈头第一句:“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
当报纸上刊出了教育部解聘闻一多的消息后,臧写了《擂鼓的诗人》,以示抗议。闻在回信中写道:“你在诗文里夸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雅好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谅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昆明街头的几家店铺和杂志社纷纷挂起“闻一多治印”的牌子。名教授治印,这在昆明是新鲜事,于是,慕名求印的接踵而来。闻一多本来课务很忙,这时时间更加紧张。深夜,孩子们睡了,他听着孩子们均匀的鼾声,奋力刻印。白天,朋友们来谈话,他往往也得手拿着牙章刻几个字。每逢这时刻,他常常风趣地说:“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
西南联大复员前夕,民盟云南支部组织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各种文件都不用组织的名义,而改用个人的化名。一天晚上,议定用“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用“刘宓之印”代表秘书处、用“祖范之印”代表组织部、用“杨亦萱印”代表宣传部。刻印的事,闻一多就主动担当起来了。第二天清晨,他拿了这四方印章交给楚图南。楚图南接到这精美的印章之后,“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睛,接过了四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动。”
名言书要读懂,先求不懂。
友间固不妨诚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也要避开标榜的嫌疑。
尽可能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哪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
尽可多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那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个人之于社会等于身体的细胞,要一个人身体健全,不用说必须每个细胞都健全。
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