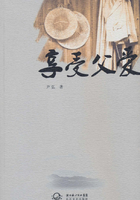师道1935年初,胡适南下接受香港大学颁赠的名誉博士学位,他向校方提议,港大中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主任应由中国学者担任,此人应毕业于英国大学,对中西文化有精深造诣,在学术界享有权威,而且还应是南方籍贯,谙闽粤方言。校方采纳了这项建议,经胡适介绍,许地山于1935年秋受聘香港大学,主持中国文学教学。
许地山出任中文系教授后,港大学风剧变,孕育出一股新的学术气象。许地山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待人接物总是抱着一片和蔼与真诚,永远保持热情,因而深得同仁的敬重与青年的爱戴。不少学生因许地山的到来获益良多,著名史学家金应熙在《悼许地山师》一文中追忆:“先生却是最恨敷衍了事的,他对每一课都认真预备。有几次我到中文学院上课,比预定上课时间早,已经看见先生在教室认真预备,翻抄上课时需用的参考书籍了。在上课的时间,有时偶遇一两个意义不明的词,先生也从来不肯放过,总要找到解释才休的。”
许地山以“五四”闯将的姿态与热情,致力改革中文系,他把当时的“中文部”正式改为“中国文学系”,开办文、史、哲、翻译等课程,随后又分设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合组成中文学院。他还着手革新课程,充实内容,积极倡导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倡导汉字简化,改革八股文,力倡白话文,并把中文学院招生的作文全部改用白话。1941年7月,针对钱穆的《新时代与新学术》,他在《大公报》发表了《国粹与国学》一文,反对抱残守缺,主张“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产生多少有用的知识与人物,而不是历史的久远与经典的充斥”。
苦研1915年,许地山考进燕京大学,曾在文学院和神学院求学。在此后五年间,他成天出进于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尤其是中外民俗学、宗教学图书,许地山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因为兼通梵文,他通过比较作研讨,发现其中不少乃自印度辗转流入,若干年后,许地山就此翻译了《孟加拉民族故事》;而在图书馆里,他更多的是研读各种佛经。1918年,写给新婚妻子的小品《愿》《香》等篇章,都分别用了佛经词语和典故。燕京大学图书馆深化了他对图书馆的需求,此后每到一处,无论居住长短,许地山大半时间都用到了跑图书馆上。
五四运动以后,大学停课,很多学生逛嬉于游乐场所,或无所事事,许地山却成天在图书馆流连忘返。燕京图书馆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就到其他图书馆去。可以说北京城里城外所有挂牌子的图书馆,他都跑遍了,他的同学日后回忆说:“北京的图书馆,没他没去过之处,一去就是一整天。他身上满是书香。”因为博览群书,知识面广,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也就出了名,人们认定他是一个一点也不痴的真正的“书痴”。
1923年,许地山与梁实秋、谢冰心等同赴美国留学,他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读宗教哲学。在大学仅一年,而大半时间却都在图书馆度过。到写作自传体小说——《读〈芝兰与茉莉〉》,也是借用了图书馆若干藏书,并在图书馆的413号检讨室里写成的。在此期间,许地山还查阅、摘录了图书馆收藏的欧美学者研究中国道学文化的著作和调查报告,准备写《中国道教史》。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推出的这部书的扉页上,许地山为感念当年图书馆提供的阅读便利,还特地写下“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等字样以纪之。
翌年9月,许地山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印度宗教比较学和民俗学。牛津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更为丰富,吸引着这个来自东方的学子深入宝山不愿返。他在牛津大学两年,日后回忆这段有益的图书馆生活,许地山颇有关山度若飞之感,还特地在自称为“牛津书虫”的文章里称:“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的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兰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菲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老舍后来追忆说:许地山只要在图书馆中坐下,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他到了图书馆,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伦敦虽大,许地山行迹所在却只是两个点,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皇家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老舍说,在伦敦要找许地山很容易,“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我在东方学院图书馆楼上发现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唤他,他不动。一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因为图书馆已到关门时间的缘故。找到了我,他不住地喊饿,是啊,他已饿了十个点钟了”。
1926年,时在巴黎留学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罗家伦,拟开创“中国近代史”课程,他写信给许地山,请求帮助搜集中英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文书、档案。许地山当即自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查阅这些尘灰满面的文字。他朝出夜归整整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整理、抄录。由于这些原始档案大多是缺头断尾,在抄录过程中,许地山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注释。他终于比较完整地搜集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交涉史料,寄交了罗家伦。
许地山在波德林图书馆搜集原始档案,也引发了自己对鸦片战争题材的兴趣。过去在国内见到的都是中国一方的文字,未及其他,易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而此正是治学大忌。因而许地山在波德林图书馆搜集档案结束后,余意未了,又赴英国其他图书馆寻找,果然获得更多的资料。当他回国前夕,竟抄录、整理了厚厚一本的英国鸦片战争档案文书。它就是192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达忠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
1927年,许地山离英归国。回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他的学识渊博,能开不少其他教师教不了的课,如《佛教文学》《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等。即便如此,他仍习惯于以大量时间在图书馆读书,按题搜集资料,其中很多选题是他人想象不到的,像搜集各种门神像等。有个时期他还热衷在图书馆寻找传统文化里被人们鄙视的扶箕迷信种种样式,后来竟然编了一册《中国扶箕文化研究》,罗列了100多种迷信样式,用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陋习。
许地山1935年升任教授后,学院为他设置研究室。这间挂有“面壁斋”匾额的研究室,除了一面墙挂匾,三面墙都被连接天花板的书架遮住了。其中有两只书架上,还摆着学者自海外图书馆抄录的梵文学习笔记和抄录欧洲中古时代僧侣所写的圣经以及其他稿本。当时,许地山想有条不紊地整理它们,以便完成八年前回国途经印度应泰戈尔建议,编出一部《梵文字典》的承诺。可是笔记整理完竣之后,他寻遍北平各大图书馆,发现藏梵文的中西书籍罕有,遑论涉及梵文的工具书了。由于资料的缺乏,这项有意义的研究随1935年许地山赴香港大学任教而中断了。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期间,仍醉心于出入图书馆抄书编书,大小学问都做。因为家里饲养了几只猫,他大感兴趣,就想到做猫的文字。他就此跑了多次图书馆,搜集中国和世界各地有关猫的神话、故事、人文与自然知识,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猫乘》,他说:“作者一向爱猫,故此不惮其烦地写了这一大篇给同爱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