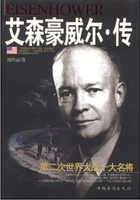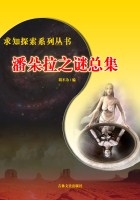传略许地山(1893—1941),原名许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生于台湾台南,甲午之战后全家迁居福建龙溪(漳州)。幼年随父在广东读书,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衰落,到漳州第二师范教书,1913年赴缅甸仰光中学任教,1916年回国。次年入燕京大学,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再入宗教学院,得神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次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习。他对宗教史有精深研究,也下工夫钻研过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掌握梵文、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甲骨文,是著名学者。
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瞿秋白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第一篇短篇小说《命命鸟》,发表于1921年1月《小说月报》,以虔诚的宗教感情塑造了一对青年男女因爱情受阻而厌世。希望转生“极乐国土”,以求解脱。小说以独特的宗教神秘色彩和艺术风格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应。收入第一本小说集《缀网劳蛛》中的早期作品大都表现对宗法礼教和封建习俗的不满,同时也流露出浓厚的宗教观念和虚无思想。著名的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也反映了他早期思想的“杂沓纷纭”。有主题明确内容深刻的佳作,也有宣扬佛教思想的篇章。
1935年赴香港大学任教,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学学会理事等职。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几年写的作品,主题和风格都有转变,结合现实日益紧密。1934年的小说《春桃》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泼辣而善良的形象。1940年的《铁鱼底腮》写了一个旧知识分子学无所用的苦闷心情及悲惨遭遇。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和他逝世后编辑出版的《杂感集》都显示出他的人生态度的积极变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他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教学任务又十分繁重,终因劳累过度,不幸因心脏病逝于香港。
才情许地山一生与世无争,热爱和平,性格温和、天真、乐观、幽默。当时他的形象是这样的:总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过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杉“,手带白玉戒指,留长长尖尖的指甲,蓄长发,留三撇胡,在当时被笑称颇似莎翁。经常满面笑容,据说在朋友眼里,几乎都总是咧着嘴巴笑嘻嘻。而对着即使是与其知识观念不相苟合而怒气冲冲相辩论的学生,也是极和蔼地说,没事哇,没事哇,你慢慢地谈。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任教时,一次,按约定时间去接购物的妻子,妻子因购物砍价而迟到,他幽默地谅解:“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我没有吃亏。”
“当他遇到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怎样,他总不驳回。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好友老舍如此回忆许地山。
郁达夫说,许地山“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这一种小孩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许地山在宗教研究中对佛学很投入,并表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如终年茹素,偶尔吃荤;虽然留学西洋多年,可他从不穿西服,夏天是麻布长衫、白通帽,冬天是棉袍大褂、黑呢帽。就这样,他因为一年四季爱穿黄对襟棉大衫,留长发蓄山羊胡须,天天练习像钟鼎文一样的梵文,师生们称之为“三怪才子”;又因其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同学们喊他做“许真人”。
许地山有许多惊人的才华,他不仅研究服装,还会自己做衣服;他善于培植花木、布置庭院,经他的手插于瓶中的花枝别具韵味;他搜集古钱,加以考证;他捕蝴蝶,制作标本;他还知音律,弹一手好琵琶;他带领他的孩子们养猴子、小狗和家禽,还为孩子们创制一种有历史内容的六国棋;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英文、德文、梵文等外国文字;能辨识金文、甲骨文,
沈从文评价许地山,说他能“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糅合在一处”。
许地山和老舍在伦敦时,有一次出去一整天才回来,进门便笑,还不住地用手摸着刚刚刮过的脸。老舍问他笑什么,他说,教理发匠挣去了两镑多!天啦,理一个发才八便士,再加刮脸也不过一先令,怎么会花去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他什么,他就答应什么。理发师碰到这么好说话的人,于是把所有项目全做一遍,不花去两镑多才怪呢。
许地山去世时,有人叹道:“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谈话伴侣,中年人失掉了热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开心的先生,孩子们失掉了淘气的老伯。”
炽情许地山和夫人林月森结婚很早,1920年,刚生下女儿不久的林月森在赴京途中病逝于上海。许地山和妻子感情很深,他把她安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常常一清早独自走到妻子坟前,放上一束鲜花,默默地站立一会,回味他们生前的往事与趣谈。对妻子的怀念成为他干燥的心灵气候里仅有的无声春雨。于是,便有了这首充满炽情的词——《心有事》:
“心有事,无计问天。/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我魂飘荡,有如出岫残烟。/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脱串。/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箭折,珠沉,隔作山溪泉。/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海涨就要沉没赤县;/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拼命去填/呀,精卫!你这样做,最经历万劫也不能遂愿。/不如咒海成冰,使它像铁一样坚。/那时节,我要和你相依恋,/各人才对立着,沉默无言。”
爱妻去世本来让许地山心如死灰。但若干年后,一个青春妩媚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令其死灰复燃。生活就是这般奇妙,失去的以为不会再来;它却不期然以另一副面貌出现。周俟松,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她在中学时读到许地山的作品,心生仰慕。在“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周俟松第一次见到许地山,又为其演讲所倾倒。
第二次见面,是在接待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欢迎会上,许地山忙前忙后,十分活跃。周俟松远远地看着他,目不转睛。不久,周俟松考入北京师大数学系,她有一天去与她家同在石附马大街的熊佛西家做客,意外地碰到许地山,他们说了很多话,像一对老朋友。许地山渊博的学问和生动的谈吐使周家的女学生再也按捺不住。
许地山见过几次周俟松后,也陷入情网,他鼓足勇气于1928年12月19日给周俟松写了第一封情书。“自识兰仪,心已默契。故每瞻玉度,则愉慰之情甚于饥疗渴止”,“是萦回于苦思甜梦间,未能解脱丝毫,既案上宝书亦为君掩尽矣”。相思连书都看不进去了,这对一介书生,该是何等的折磨。好在苦思必有甜梦。周俟松不顾父母反对,决意与许地山结婚。
翌年五一劳动节九时,许、周在北京“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前来祝贺的嘉宾有蔡元培、陈垣、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新房设在周家二进院,从洞房后窗可以看到后花园的八角木屋和野趣横生的丁香树、枣树,旖旎之至。周俟松在那天的日记上注了四个字:风和日朗。
婚后,这对新人恩爱有加。周俟松特别喜欢看故事,许地山写不了那么多,就专门为她翻译孟加拉和印度的民间故事。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夫唱妇随,红袖添香,享尽人间福祉。我们来读一段许地山那时翻译的德国民歌,庶几可以写照他的心情:
“夏夜底月初升,在沉寂的山顶;远处颤音低微,是夜莺的幽鸣。唱罢,快乐的夜莺!在银光里唱罢,这如梦的夏夜,我们不能听见别的声。西天一片云彩,黑暗像要降临。停住罢!别走近来遮片刻底爱光阴,停住罢!”
有一天,住在山东济南的老舍忽然收到许地山的电报,电文是:“×日×时到站接黑衫女。”老舍郑重其事地按时赶到车站,接到的所谓“黑衫女”竟是身着黑色旗袍的周俟松。她在一所学校任校长,前往济南出差。许地山的风趣让老舍笑得闭不上嘴,亦足见许地山当时的轻快与喜悦。
黑暗虽然没有降临,阴影却像宿命似地飘然而至。阴影来自于光环的消失和激情的退去。在周俟松眼里,许地山不知不觉由著名作家变成不修边幅、随意乱扔东西的邋遢鬼,变成重友轻家、应酬太多的伧夫俗客。而周俟松呢,慢慢地,红粉褪色,淑女成妖,先是唠叨,尔后是牢骚,都不见效,终于演化成河东狮吼。许地山可没有陈季常那样的耐性,他是演讲出身的,吵起架来也是出口成章,全然把闺房重地当作了北京街头。在夫妻生活中,对抗一旦产生了惯性,那任何细枝末节都可能触发一场“战争”。1933年秋,两人惊涛骇浪般大吵后,许地山不辞而别,远赴印度考察学习去了。
大半年过去,身在异乡的许地山发现自己无法忘掉周俟松,无法抛却他们之间那一段氤氲情义。他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那些个无猜无忌、耳鬓厮磨的日子里去,但矛盾和憎怨是明摆着的,它们像一座座山阻隔着这对夫妇。许地山知道,要搬掉这些山,必须靠他们自己;否则这些山就会无情地让他们恩断义绝。突然,他想到,为什么不在两个人之间立一个公约呢?那该叫什么公约呢?对,以爱情的名义,就叫“爱情公约”!
于是,他提笔给周俟松写了一封充满悔意和深情的信,并附上自己拟定的解决双方矛盾的“爱情公约”:
一、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
二、如意见不和,在大声说话以前,各自离开一会儿。
三、各自以诚相待。
四、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肉体和精神的愉快。
五、一方不快时,他方当使之忘却。
六、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
周俟松读了许地山的信和公约,泪如雨下。她检省自己的种种不是,想起对许地山无时不在的牵挂,她给许地山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早日回家。
许地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两人执手相见,恍如梦中,竟说不出话来。周俟松把许地山领到卧室,向他指了指墙上,许地山抬头看见那里高高挂着的,正是他们的“爱情公约”。夫妇俩抱头痛哭,从此他们生活中便永远没有了阴霾。
周俟松是一个坚强的女性。1941年,年仅49岁的许地山因劳累突然倒地身亡,8岁的女儿许燕吉号啕大哭。周俟松抹干眼泪,拍着女儿的背说:“孩子,不要怕,还有妈妈呢!”周俟松活了九十多岁,她默默地为丈夫编书、写文章,像一只春蚕,绵绵不绝地吐露着自己的不尽哀思与无边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