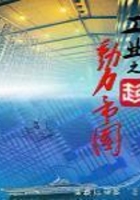宝玉用力推开茗烟,道:“我不管,妹妹才不会愿意嫁给王爷呢,一定是他们逼得。”扑上去,茗烟摇着宝玉,大声喊道:“二爷,你就醒了吧,这事早就是不可更改的了,就是你真的赶回去,也无能为力,抗旨不尊,那是掉脑袋的事,退一步来说,即使你能回去,说不定林姑娘已经出嫁了,你又能怎样,何况,你现在根本就回不去,你出去看看,李贵他们正在外面守着呢。”
颓废的一下坐在地上,宝玉顿觉得浑身无力,耳旁一个优雅的声音依稀响起:“果然是如宝似玉。”低低的唤了一声:“林妹妹。”宝玉顿觉得眼前发黑,一时便无知觉。
“宝玉。”黛玉一下从梦中惊醒过来,情不自禁的喊了出来,紫鹃迷迷糊糊的走过来,道:“姑娘,怎么了。”
摸了摸额头的冷汗,黛玉轻声道:“刚才做了个噩梦。”紫鹃道:“姑娘不要多想了,再歇会吧,天亮还早呢,何况还要出门。”
接过帕子拭了拭汗,黛玉道:“你去歇着吧,我一会儿再睡。”软软的倚在靠上,黛玉扯起被子围住身子,脑海里依然是梦中的情景:宽阔的河边,宝玉站在前面拼命的招手,可自己却一动也动不了,只得眼睁睁的看着宝玉被冲过来的河水卷走,耳旁依然是他声嘶竭力的喊声。
闭上眼,黛玉才发觉,自赐婚后,这是第一次梦到宝玉,醒时两人身处两地,想不到连梦里也是天各一方,抬起手想拭一拭流出的泪,却发觉帕子竟是干的。
一大早,黛玉陪着永昌长公主出城去牟尼院上香。早在三天前,慕箫已经奉旨去西北巡视,送走了慕箫,长公主心里总有些隐隐不安,知道牟尼院的香火很盛,于是便选了个日子,又道黛玉也快要出嫁了,一起来上上香,权当告慰故去的父母。
上过香后,又留下吃了一顿素斋,等长公主黛玉她们离开时,外面天色暗淡,清冷的风吹着山上的枝叶沙沙作响。
坐着轿子下了山,马车静静地候在路边,宽阔的大道上杳无人迹。
紫鹃刚扶着黛玉登上后面的那辆马车,却听不远处的林中传出一声轰隆的声音,前面拉车的马惊得一声长嘶,一下挣脱车夫,扬蹄向前跑去,身后传来众人的惊叫声。
车上的黛玉还没反应过来,马车就疾驰而去,耳边犹听得后面的尖叫声和呼呼的风声,身子不由己的一下跌进车里。
黛玉情急之下只得紧紧握住车里的横栏,闭上眼,任由车子放马而去,颠簸中,黛玉隐隐听到外面的喊声不断,没有去理会,有一瞬间,黛玉的心里竟有一种释然的感觉,或许这样也好,“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叫污淖陷渠沟。”
也不知过了多久,车子猛的一下停了下来,黛玉毫无防备,身子收势不住,一下向前扑了出去,一双手臂紧紧地迎了过来,把黛玉抱了个满怀。
回过神来,黛玉想要挣扎,却不料那人丝毫没有松手,健壮有力的臂膀似乎要将黛玉融进自己的身体里,怦怦的心跳急促而清晰,带着劫后余生的激动,令黛玉诧异的是,那圈过来的手臂竟带着不可遏制的颤抖。
松了口气,耳旁一个声音喃喃的道:“好在没事了,好在没事了。”
微皱起眉,黛玉听到自己冷漠的声音:“放开我。”那人丝毫不为所动,依然紧紧的拥着黛玉,气急败坏的道:“刚才为什么不应声,你不知道这样会没命的。”
冷冷一笑,黛玉道:“一个棋子的命对王爷又有什么呢。”反应过来,水溶咬牙切齿的道:“那也得我同意,告诉你,即使真的有个好歹,黄泉路上你也只能是我水溶的人,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回过头,水溶对身后的人道:“侍剑,去告诉皇姑,王妃没事,免得她担心,阿九,去把本王的披风拿来。”
周围一下静了下来,轻轻松了松禁锢的手臂,水溶附下头,看着劫后余生的黛玉,放松的喜悦如潮水般涌来,禁不住低低的调侃道:“即使真是棋子,那你记住,我是个爱棋如命的人。”
阿九小跑着过来,水溶接过披风,轻轻披在黛玉身上,修长的身躯遮住了黛玉回头的视线,低声道:“别看。”
透过风吹来的血腥,黛玉也情知拦下疾驰的马车恐怕也非易事,没有做声,黛玉只是轻轻舒了口气,抬眼向前看去。
这里地势相对空旷,远处是一片稀疏的林子,面前不远处,立着一排背身而立的侍卫,身旁的水溶道:“也是凑巧,今日我去城西大营巡视,回来的路上正碰到……”
舒了口气,水溶心有余悸的道:“多亏耽搁了一会儿才走,看来今日那个军士应该是有功无过,回头吩咐下去,连升两级。”
抬头冷静的看了水溶一眼,黛玉淡淡的讥讽道:“果真是权倾朝野的王爷,一句话,可以让人上天也可以让人入地,只是不知这满盘的棋子,王爷又能顾得了几个,到最后不过是被丢弃的命运罢了。”
想起宫中那次听到的兰贵人,上次南安王爷口中的前王妃,黛玉顿时觉得周身侵寒,一直寒到了心底。
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个面美如玉,心冷如霜的人,黛玉朝着远处跑来的紫鹃迎了上去,飒飒的风吹起身上披的水溶长长的披风,仿佛要随风飞去。
有一刹那,水溶目不转睛的盯着风中那个纤细的背影,生怕自己一眨眼,就不见了她的踪影,身后,方才急出的冷汗早已冰凉,手中,被缰绳勒出的血痕隐隐作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