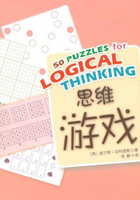商量不出一个结果。
最后,于苏州慢慢抬起头,说:“你们把我跟我爸一起处理吧,要锁一起锁,要关一起关,我愿意的。”
所有人都盯着他看。
于老棺沉痛地哭,乱喊,说不关苏州的事,不关苏州的事,不关苏州的事。
老苗跟他说,这或许不是件坏事,把苏州跟他一起带下山去,他顶多因包庇罪坐一段时间的监,很快就能自由的,也不至于呆在山上战战兢兢地活。
于是就这样决定。
把两个人反绑在一楼大厅的椅子上,轮留看守。
三个小时以后,楼明江再次做他的试验,把血清素喷洒到于巧巧的右脸上。
右脸的鼻翼、脸颊和唇角,也都现出紫黑颜色的反应,并且像刚才一样,很快消失不见。
楼明江说:“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毒粘在皮肤上以后,能在空气中保存最起码三个小时以上,具体是多久,不知道。”
天还没亮,局里的车到达村口,把于老棺父子以及于巧巧的尸体抬上车离开,悄然无息,没有惊动村民。
于老棺不可能再自由。
于苏州会因为隐瞒于老棺的犯罪事实而被关押一段时间。
于巧巧死了。
一夜之间,少掉三个凶手嫌疑人。
现在剩余村民的名单是:乔兰香,张红,于伟,于恩浩,戴明明,石莲娟,陈乔斌,于国栋,梁玉米,于天光,于菁菁。
其中于菁菁和于恩浩是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五岁。
我问常坤局里是不是真的已经定下陈家坞隔离监控的方案,他说上面还在商量,没有定下,昨天是为了安抚于苏州才说已经定下监控方案。
具体还得等上面的意思。他说。
楼明江说,昨天往尸体和于苏州身上喷洒的血清素非常敏感,任何有对人体有伤害的物质都能呈现反应,并且会因伤害程度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状况。
“昨天这种情况从来没见到过。”他说,“我想应该可以这样解释,有人把某种毒——可能是液体,也可能是粉末——涂抹在于苏州的袖子内侧,那个部位是手非常容易接触到的,只要手接触到,然后吃东西,就会把毒送入体内。而这种毒一进入血液就产生致命的破坏,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也就是说,它会适应人体结构,将自己转换成血液的某一组成成份,从而很现发现和判断。”
“世界上存在这种毒吗?”常坤问。
“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楼明江浅笑。
“那你觉得,这个村子里的那些农民,有谁可能把这么危险的东西藏在自己身边?”
“谁知道呢。这个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那什么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
“昨天晚上我做的,就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这种毒找出来,这也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常坤问楼明江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毒物,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化学物质还是动植物毒。
楼明江想了想,笑起来,说:“我没接触过这种东西,但我听一个教授讲起过一件事情,和这个好像那么点关系。说云南那边有个小村庄,村民无意挖掘出一处古墓,墓中八副石棺,棺中尸体用某种奇怪液体浸泡,不腐不臭,面色如同生者,尸体穿金戴银,尸身下还有古器皿作殉葬。村民贪财,疯抢,并且向当地政府隐瞒了古墓的事情。几天之后村中将近一半村民离奇死亡,怎么查都查不出死因。村民大骇,以为是他们的行为惹怒墓中亡灵,招致灾祸,便要求所有村民将棺中取出物件全部放回原处,并封棺叩拜。但有两个村民奸滑,不愿意将宝贝还回,就趁夜里潜入墓中,往石棺内浇气油,点火烧了八具尸体。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墓体坍塌,全部活埋。”
我没听明白。
他所讲的这个故事,跟陈家坞的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楼明江没再笑,而是往下说:“后来有警~察和一队考古学家驻村,我认识的那个教授的一个朋友就在那个考古队里,他们没能把坍塌的墓体重新掘开,但在驻村调查期间发现,所有死去的村民,都曾在那个墓中,将双手伸入石棺的液体中捞取殉葬品。石棺里的那些液体是关键。教授的那个朋友用我昨天晚上我用过的那种动物血清在死去村民的衣服上,头发上,皮肤上发现毒。他基本上能肯定致使村民死亡的毒就是石棺中的那些液体。同时他做了很多试验,发现,那种毒能在人或动物的皮肤上存留三天左右,在衣物和木制品上可以存留两到三个星期左右,但不会在任何金属上存留,而且非常容易在水以及其他洗涤剂中溶解。”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常坤问他。
“1996年。”
“后来呢?关于这件事情,有没有新的进展?”
“我不知道。警~察那边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考古队这边的情况我还有一点点听说,那次行动早就结束,但是之后,好像还有几位专家在研究这个全新的,富有挑战力的课题。关于那种液体是什么,毒性从哪里来,对于尸体的保存是不是有完美作用。等等等等。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很多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常坤还想问什么。
外面突然有人走进来。
穿堂风送进一阵中药的浓香。
然后一道影子投在门边的阳光里,瘦长。
是于天光。
他犹豫着跨过门槛。
然后犹豫着开口。
他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刚才,刚才,于伟去找我,说他感冒了,问我买点感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