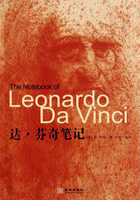拭了泪,黛玉方道:“按理,在这里也长了近十年,银钱又不过都是身外之物,我原是不该张口要这些嫁妆钱。可是,我林家的女儿,不是给人指手划脚说我吃用皆是贾府供奉,毁未来徐将军府中声名体面。我用的是林家的钱,并不曾沾贾府的一文半个,倘若外祖母心里体谅,原是我的福分,倘若不谅解,那也只能如此了。”
“老祖宗心里爱姐姐的,哪里有不体谅的份儿呢?”探春忙款言劝解,“这些年,我也是如今才知道姐姐竟是身携巨金而来,可恨竟是上头没说,家下的丫头婆子言三语四,让姐姐生了许多的闷气,多了许多的烦恼。”
想起外头说徐将军生死不知的事情,不免又安慰道:“姐姐只管放心罢,徐将军顶天立地,还没娶姐姐过门呢,哪里能舍得让自个儿出事?姐姐和徐将军吉人自有天相,总是会喜结良缘,早生贵子。”
说得黛玉越发红了脸,想起徐若凡就在内室,不觉嗔道:“偏生就是你牙尖嘴利,素日里的话,尽叫你说去了!”
探春陪着黛玉说笑了一番,倒也解了些黛玉的烦闷,黛玉心里又担忧着徐若凡受伤发热的事儿,因道:“我这几日弹琴倒是伤了手,奶娘的意思,如今又是秋深露重的,怕冷不防倒是着了凉,又受了寒发热就不好了。因此妹妹回去告诉凤姐姐一声儿,请大夫配些皮外伤受寒发热的药好预备着,也好减了些奶娘的担忧之心。”
探春忙笑道:“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王嬷嬷担忧着姐姐也是该的,我回去告诉凤姐姐就是。”
因此便约着宝钗出来,黛玉起身相送,不妨宝钗眼尖,瞧见墙角里放着红纱罩着的长刀,惊道:“这是什么东西?倒是长刀的模样!妹妹这里都是女人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凶器?”
黛玉毕竟是自幼男儿教养,倒也临危不乱,淡淡地道:“原是我房中的东西,外人一概不得说什么。就是猫儿狗儿,那也是潇湘馆里的,外人也得忌讳着些,自有我来处置,藏着长刀又如何?难不成竟是不曾放着的?”
探春听到黛玉如此说,亦是有些怔忡,倒是没有多嘴说什么。
王嬷嬷正好带着丫鬟们送上黛玉的早膳,听了这话,方款言笑道:“宝姑娘原是不知道的,书香清贵之家,家大业大,人又生得太干净了,唯恐撞见了什么花神,因此但凡我们这样的人家,总是房里悬挂着刀剑镇压邪气入侵。偏生这长刀又是太锋锐,唯恐悬不起来,所以我们姑娘暂且放在了角落里。”
听到王嬷嬷这么一番话娓娓道来,严丝合缝,没有一丝儿可让人挑刺儿之处,宝钗也不好说什么,只得含笑道:“这个规矩倒是新奇,原是没听过的,竟是我孤陋寡闻了,妹妹也别恼,姐姐也不是有心的。”
略说了两句,便与探春一同去了,只是路上又不免回头瞧了两眼。
细雨霏霏,掩去了两人的背影曼妙,黛玉方略略松了一口气。
王嬷嬷见黛玉呆坐在窗边,细细安慰了几句,方吩咐雪雁扶着黛玉进屋,又亲自将早膳送进卧室屏风外的桌子上,取出四色清淡小菜,另外是香油莼齑、干炒鸡丝、羊尾笋条、牛肉馅儿的包子,以及一大碗碧莹莹热腾腾的碧粳米粥。
黛玉眉头一皱,脸上有些不喜,淡淡地道:“这么点子东西够做什么的?吩咐厨房里的婆子,就说我手上伤着了,有些牛肉的东西吃不得,想喝极新鲜的鱼汤,让他们去弄极新鲜的墨鱼熬了汤送来,再吩咐她们整治些对伤口好的东西来。”
又想着徐若凡毕竟是个大男人,哪里如自己这般日日吃一点猫儿食似的?故黛玉又吩咐多预备些早膳来。
外头厨房里虽心里有些讶异,只当黛玉又耍小性子,嫌之前的饭菜不合胃口,虽不耐烦,也只得依言做好送过来。
黛玉跟前只留着王嬷嬷和雪雁春纤服侍,轻挽水袖,亲自盛了一碗香浓的鲜鱼汤,递给王嬷嬷扶出来已经坐下的徐若凡。
对她的细心和体贴,徐若凡心中自是感激不已,喝着香浓的鱼汤,香在嘴里,润在心中。
黛玉虽装作平静无波,可是毕竟是未曾出阁的女儿家,到底还是羞得了不得,只得闷闷喝了两口鱼汤,便放下碗不吃了。
徐若凡即使是发着烧,可是神色却是极其平静,似乎没有一丝不适,只是伸手替她张罗盛汤,问道:“怎么不多吃一些?你也受了伤,多吃些身子才会好,你这样的胃口,连小鸟都不如。”
一句话出,黛玉眼中竟是扑簌簌地落下泪来,柔肠百转,竟是打了一千个结,愈加抽抽噎噎哭个不住。
见到黛玉哭泣,徐若凡手忙脚乱地站起身,却不妨触动伤处,双眉微皱,却不露丝毫痛楚之色。
“好好的,怎么哭了?”大手也是忙忙地给黛玉擦拭脸蛋,只是用力不当,未免擦红了黛玉雪嫩的小脸。
徐若凡一时倒是忘记了男女授受不亲,黛玉也未想起来,只是心中那一股暖流竟是暖彻了心肺,半日才渐渐止了哭声,方抽抽噎噎地道:“自从六岁到这里,不吃饭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劝过我一回,也没有人在意我是不是吃饭。”
小时候,她不爱吃饭,总是父母哄着自己吃,没有一顿落下的。自从来了这里,饮食风俗大异,十顿饭中,她常常都是五顿不去吃,也从来没有人在意,只顾着吃自己的。哪里如徐若凡这般,见自己吃得少,还要劝着自己多吃的?这一生,在贾府中,从未有过如此温暖人心的话,怎能让她不伤心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