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沉腻于悲痛中哭得不能自己的时候,他会递过来一杯水,说,“哭了这么久,该补点水份了。”
当她半夜被恶梦惊醒的时候,他会慌乱不已的冲进她房间,看到她没事后,便说,“制作恐怖片让你去做特效,我想效果会更好。”
田田看看镜子,长发散乱披肩,苍白削瘦的脸毫无血色,空洞漆黑的大眼没有一点光彩,的确像一个幽灵。
田田不知不觉已走到马路,看着那股川流不息的车辆,不知怎么的,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样生活,难道她要依附严肃一辈子吗?
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曾经认定可以携手一生的人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等她清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了。
这些念头在脑海反复纠缠,就像虫豸吞噬着她。
田田一瘸一拐的走着,她已走了几个小时,却不能停,只要一停,她就会马上崩溃。
她强迫自己不去想,一直以来她都认为是别人负了她,结果是她害死了妈妈,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她自己。
田田心中痛如刀割。
身后不远处,严肃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步步地艰难地走着,到了最后她都一瘸一拐的了,还在强自支撑着不倒下去。
严肃不放心田田,每天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便开车回到别墅看看,今天回到家中,看到田田不在,便慌忙开车出来找,好在很快看到傍徨在马路边上的田田。
严肃是欣赏田田的这份决绝和坚强的。
田田自恢复以来,刚开始的号陶大哭,到现在没有再哭过,没有闹过,总是一个人默默的忍着。严肃也没有安慰她,她的伤口只有自己自己舔,这样她才能坚强起来。
也不知走了多久,天边已泛黑。
田田摇摇晃晃地上了天桥,笨拙地爬上望海台。
严肃亦步亦行跟在她后面,她丝毫没有察觉。
田田爬了上去就很安静地在上面坐着,两条腿晃晃荡荡垂在海面上,这实在不像自杀前的准备动作。
严肃眼睛一眨不眨的注视着她的每个动作,怕她一旦支撑不住掉下去,他能赶在第一时间挽救。
一时一分一秒的过去,田田就一直坐在那里沉思着,眼睛空洞的望着天边,时而喃喃自语。
“这蠢丫头要坐到几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寒风肆虐,严肃身上起了一层寒意,不禁担心着衣着单薄的田田。
田田虽然被冻得几乎麻木了,思路却慢慢地清晰了起来,这一路走来,穿梭的车流,波光粼粼的海面,想想自己的人生,已生无可恋。
从小,爷爷奶奶不喜欢她,父亲是个赌徒,后因打架伤人入狱。是妈妈忍辱负重把她当宝贝呵护着长大。她明白她是妈妈这一生的依靠与寄托。
可是她的婚姻不但在她心上狠狠的割了一刀,宝宝的夭折又在她受伤的心口上补上了千刀,母亲的自杀真正地将她的心粉身碎骨。
但是她不能死,她还有好多债好多人情要还。
妈妈为她,生前的家就被烧掉了,死后还没有一块像样的墓地,骨灰盒只能存放在格子间。她要挣钱,挣充足的钱为妈妈买一个环境幽美的家。
张淑兰阿姨为她妈妈垫付了很多医药费,还倾家底把她那残破不堪的家给修葺好,她必须要报答。
还有,还有严肃,欠他实在太多,田田根本无法算清。但是她会慢慢偿还,她不想欠他。
田田撑着僵硬的腿挣扎的站了起来,慢慢地,她抬头,却浑身陡然一震。眼前严肃如雕像一般站在她面前。
“清醒完了,就回去吧。”严肃开口冷淡的语气,似这寒夜。说完就大步流星的走在前面。
田田在后面疲倦地跟着他,却没觉察到前面严肃一片低低的叹息和意味深长地眼神。
车里,严肃从抽屉里拿出一瓶白兰地,倒了一杯递给田田,命令道“喝了它。”
田田揉搓着僵硬的手指摇摇头,却被严肃一手按住头发强行灌了进去了。严肃随即又给自己倒上一杯,一饮而尽。
“咳咳……”田田被灌得直咳嗦,哀怨得瞅了一眼严肃。五脏六腑却顿时温暖起来。
回到家,严肃率先下车,然后一把把欲下车的田田抓了下来。
“喂,你干嘛这么粗暴!”田田被拽得七荤八素,不满抗议。
“对付你,就不能太温柔。不然越发把自己当成林黛玉了。”严肃也不管田田是否跟得上他的步伐,一路托至别墅内。
严肃走进浴室,干净利索的放上一大缸热水,“去洗个澡吧”严肃说这话的时候,田田一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里不动不出声,目光散乱,不知道在看什么或是根本什么都没看。
其实从他把她从码头上接回来时,她就是这样,呼吸都很轻,如果不是偶尔转动的眼珠,如果不是这样面对面的坐着,她简直安静得好像不存在一样。
在心底叹了一声,严肃将目光移开不去看她,田田本来胖乎乎的身子,病好没几天已经单簿成了一张照片,单簿的风大一点就能将她带走。而她脸色除了苍白还是苍白,手腕纤细得好像几岁的孩童。
严肃将田田托至浴室,她的身体很轻,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我自己会洗。”终于她说了进屋的第一句话。
“你那身材也没啥可看的,我只是怕你晕倒在这里。”严肃面无表情的说。
她淡淡的说,“我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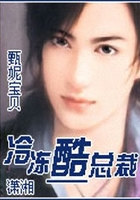

![都是吻惹的祸[完]](http://c.dushuhao.com/images/book/2020/03/31/10370668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