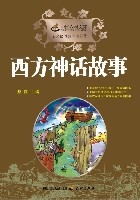二位已经耳聋眼花,以为只有废除了这些法令,罢免了这一派的官员,召回原来被罢免的人,恢复从前的老办法,社稷民生就能有救,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他们的办法不会超过这些了。
啊,这样做难道就能酬谢天子的重托,而不愧对皇天,坦然面对先祖的责问,告慰漂泊四海的孤独之人,使西北狡猾的敌寇也能折服,而敢说尽到了大臣的职责吗?我如果诚心诚意地修养君子正直的品德,邪恶的东西自然没有办法来窥视我;我如果诚心诚意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政事,那么一些非分之想就没有办法影响我;我如果真能谨慎地选择捍卫国家的将领,保卫我们的家园,那些邀功生事的自然就平息了;我如果真能革除中饱私囊的弊病,来充裕我的财富,从百姓中搜刮聚敛的计划也就自己消失了;我如果真能用纯净的风气来影响士子,从慎于进取的人中选拔贤才,为国家百年之后储备人才,那些盯着官位的奸佞之徒也就自己收敛了,而好人则能通过自我修养,洗礼磨炼自己显露出来。但没有人这样做,而是夜以继日,像寻找丢失的孩子一样,提拔一个人,就说他是熙宁、元丰时被罢官的;罢免一个人,就说他是熙宁、元丰时提升的;施行一种法令,就说这个法令是熙宁、元丰时废除的;废除一个法令,就说这个法令是熙宁、元丰时施行的。
然而,如果让元祐时的这几位处在仁宗、英宗的年代,他们将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件事也做不成,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过一辈子吗?没见到他们有什么道理,仅仅是负气而已。气一动就停不下来了,于是,吕公著、范纯仁在朝房不能协调,洛党、蜀党、朔党在官署闹出矛盾,一个人站在上面,更多的人在下面呼应,怎么能说元祐时仍然有皇上,宋朝仍然有国家呢?而绍圣(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时的那些奸人,驾驶着四匹马拉的大车,驰骋在升官的康庄大道上,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又学习他们的所作所为。
所以说,哲宗在位的十四年,没有一天不在为祸乱进行谋划,没有一天不处在危亡的境地,不是只绍圣是这样。那个时候,契丹的君臣,也处在昏聩、淫乱而不能自保的情况下;李元昊的子孙们,也只能偷安而不能再逞强了,如果不是这样,靖康年的灾祸,不会等到那个时候。而契丹衰落,西夏孱弱,就像是遇到了汉宣帝北击匈奴的大好时机,但是,全国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争论你我之间的短长,而不能振奋起来。啊!难道只是宋朝的存亡吗?无穷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站在今天的立场,回头再看哲宗时代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辞洋溢在史书中,用实际的行为要求他们,没有一个是有人心的。如果明白得失之间的道理,怎么能与愚昧的百姓一样,共同来庆贺呢?
王夫之的这篇文字中有“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和“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两句话,这是失于考证之处,因为,王安石执政时,不曾流放一个人,根据前面排列的名单,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即使在王安石辞职之后,八年间,也没有听说贬谪官员到岭南海岛的事。所以,元祐时流放蔡确于新洲,范祖禹说,这条路上生长的荆棘都已经有七十年了,可以作为证据。
章衮《王临川文集》序说:
元丰(公元1078—1085年)末年的时候,王安石早已辞去官职,不久,宋神宗与他相继去世,对王安石的议论随之也平息了,事情慢慢地安定下来。元祐(公元1086—1094年)时如果能坚守新法不加以改变,因循习惯之后,效果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谁说继承发扬没有好处呢?然而,非要追究过去的怨恨,一定要将熙宁、元丰时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先用使人头晕目眩的猛药进行救治,司马光又用使人头晕目眩的猛药制造混乱,于是,国家的政治屡次动摇,民心一再被人扰乱,回想当时说新法不可以废除的,应当不只是范纯仁、李清臣等人,只是因为书写历史的人排斥王安石,不想把当时的说法都保存下来。
不仅如此,哲宗非汉献帝、晋惠帝能比的,为什么杨畏的一句话,章惇就做了宰相,而章惇一做宰相,党人就全被驱逐了,新法也全部恢复了呢?悲哀呀!开始的时候是群臣共同结为一党来对抗皇上,最终是君子小人各自结党来求得胜利,纷争不断,互相决裂,耗费时日,耽误国家大事,直到新的皇帝登基了,仍然不能停止,自古以来,像闹成这个样子而不给国家带来祸患最终导致败亡的,有这样的道理吗?王安石当年对仁宗说,晋武帝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为子孙做长远打算,当时在位置上的官员,也都是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抛弃礼义,不要法度,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被夷狄沦陷了二百多年。王安石又说:“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急迫的了,错过这个时机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由此看来,靖康时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是早已预料到了。他苦心经营,不畏艰难,不逃避别人对他的议论和诽谤,每件事一定亲自去做,他就是这样,天未下雨时就想到事先要把门窗遮挡好。而古今那些议论他的人,却要把靖康时发生祸乱的责任归于王安石,这不是秦人斩首、车裂、灭族的习俗没有消亡吗?
陈汝锜、章衮都是平时崇拜王安石的人,他们的言论或许不免与我的言论有同样的毛病,即阿谀我们喜欢的人。像王夫之对王安石的诋毁,大概和那些俗儒没有什么区别,但他论述元祐时的政治也像陈汝锜、章衮一样,那种把宣仁太后比作尧舜,而把司马光、吕公著比作皋陶和夔的说法,都可以省略了。而且,元祐时的那些人可以议论的,还不止这些呢。宋朝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记载: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没有不推崇尊重他们的。绍圣(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时定下来的,只有三十二个人,到了蔡京执政,凡是和自己意见不合的都被写了进去,已经增加到二百零九人。然而祸根其实基于元祐时疾恶如仇太过分了。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安石亲党吕吉甫、章子厚以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以下十人,张榜贴在朝堂之上。范祖禹上疏说,应该惩治首恶,胁从不问。范忠宣叹息着对旁边的人说:“我们也将不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啊!”后来形势发生变化,章子厚建了元祐党,果然像范忠宣说的那样,大抵都是出于士大夫的互相报复,终于使国家遭受祸乱,真是悲哀呀!
章惇、蔡京制造党狱,至今稍有见识的人,都是深恶痛绝的。章惇、蔡京应该受到大家的厌恶是绝对没的说的,但怎么知道造下这个孽的肇始者不是章、蔡,而是天下后世所推崇尊敬的元祐诸位贤人呢?如果不是有《玉照新志》偶然记述了四十个人张榜在朝堂之上这件事,我们到今天也不会知道。党籍榜和党籍碑有什么区别吗?何况刻碑公布于天下,是崇宁(宋徽宗年号,公元1102—1106年)年间的事,他们在绍圣(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时,也不过张榜而已。由此看来,始作俑者其实是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这几个人,章惇、蔡京不过学他们的做法罢了,他们的罪过反而从来没有减轻过。党籍碑成了遭人万世唾骂的材料,党籍榜却从未有人提及,难道有幸运和不幸运的区别吗?不过是史家赋予他们的幸运与不幸运罢了。
蔡确已经被贬官,但台谏仍然议论不停,谏议大夫范祖禹也说蔡确的罪恶,天下不能相容。执政者要杀蔡确,范纯仁、王存二人认为不可,极力争取不杀他。文彦博要贬蔡确到岭峤,范纯仁听说了,对吕大防说:“这条路自从乾兴(宋真宗年号,公元1022年)以来,荆棘已经生长七十年了,我们听说了它,恐怕将来自己也免不了。”吕大防于是不再说了。过了六天,竟把他流放到了新洲。范纯仁又对太后说:“圣朝应该务求宽厚,不能凭借语言文字之间有些暧昧不明的话,就诛杀或流放大臣。今天的举动应该就是将来的法律,这件事千万不可有个开头啊。”太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蔡确于是死在了流放地。啊,这件事可以对比王安石在执政时是如何对待异己的。但王安石却蒙受苛刻严厉的名声,而元祐的各位贤人,至今还有评论者认为他们除恶不尽,这样来看,天下还有是非吗?
陈汝锜又说:“杨立中正当靖康遭遇祸乱之时(公元1127年),说到这场祸乱,虽然是蔡京一手造成的,其实是从王安石那时就开始酝酿了。这种说法一出来,各种支持它的材料也翩翩而至,把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时的变法作为靖康时祸败的根由,把王安石当作了鼓舞蔡京的开路先锋,这种诬陷太过分了。
如今事实俱在,凡是蔡京所喜欢做的,沉溺在虚无的生活之中,大兴土木,建造楼堂宫观,在下面大肆搜刮盘剥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在上面极尽奢靡享乐,荒淫无度之能事,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的事做了不止一件,哪一件是熙宁时做过的事?凡是蔡京结交的人,如内侍有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小人有朱冲、朱勔父子,执政者有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人,惹是生非的不是一个人,哪个人又是熙宁时的人呢?虽然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但他并没有因为蔡卞的缘故就受到王安石的提拔,在熙宁、元丰的时候当权。他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竟有人认为今天这个祸乱是王安石造成的?他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庙,是把王安石当作他欺君邀宠的工具了,多少掩盖一点他的野心。就像篡夺汉朝天下改为魏国的人,未尝不拿舜和禹禅让的事作为借口,制造所谓符命来糊弄小孩子于股掌之上;未尝不以周公摄政的故事作为解释,但曹丕篡汉怎么能说是三让登坛,是汉朝皇帝的谦让品德给自己带来了祸端,使得篡位者可以登上皇位呢,又怎么能教给后世如何使假皇帝变成真皇帝的谋略呢?”
这番话说得可谓痛快。我曾经说过,绍圣(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时章惇主持工作,他还是有意想要继承王安石的,还不至于嫁祸于宋朝。真正给宋朝带来祸乱的只有蔡京。但是,蔡京能够跻身于显要位置,是谁举荐提拔了他呢?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马光。司马光要废除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周围的官吏同僚都认为非常困难,蔡京五天就把事情搞定了。司马光欣赏他的才干,于是,委以重任。如果援引举荐连坐的法律,那么,司马光难道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司马光也是一个贤人,我不敢学习史家深文周纳、歪曲史实的伎俩,把蔡京祸乱宋朝的罪过,归于司马光,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些善于骂人的怪兽反而将这个罪名强加给与蔡京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安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