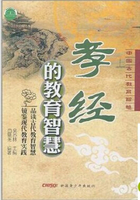实际上,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当时,为王安石说好话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陆九渊这样做,一方面他是江西人,与王安石是同乡,包括后来的挺王派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都是江西临川人。中国古代有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优良传统,北宋以降,无论王安石受到怎样的非议或诬谤,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像他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绝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他鸣不平。可以说,在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大都来自他的家乡。所以,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门为王安石所受到的冤屈辩诬正名。这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开了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的先河。
但朱熹反对王安石,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还有学理上的分歧。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是有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他的新学在北宋后期数十年间曾长期独尊于官学的地位,在当时,程颢、程颐兄弟的理学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很小的学派而已。但自从王安石及其新法在政治上被否定之后,他的新学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在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新学更被反对派指责为“得罪于孔孟”,“得罪于名教”。甚至,王安石的新学所受到的打击,比他的新法还要严重。新学被视为“异端邪说”,予以彻底封杀了。朱熹是批判王安石最卖力的,也是最有眼光的,他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离不开这个大的背景。
而他们的分歧则主要在于所谓义利之争,他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所谓“聚敛害民”;他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所谓“剥民兴利”。其实,这不仅是熙宁、元祐以来反对派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自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包括顾炎武这样的所谓进步思想家,也对所谓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表示反对,一再指责王安石“藏富于国”。王夫之更是强调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他在《宋论》中对王安石的批判,即贯穿了由义利之辨衍生出来的“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指导思想,从而认定王安石是小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人不能接受王安石的理由,仍然是他的趋利逐义。
但实际上,王安石不是不讲义,他只是反对空谈义理。他不认为,一个人仅仅道德修养很高尚,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就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后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那一套,更发展到寻章摘句,玩物丧志的方面去了,许多人为此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一点用处。在《王荆公》这本书中,梁启超有专章讲到王安石的学术,他概括为两个方面: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
也就是说,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术。王安石是个知行合一的人,他的道德情操,即使他的敌人、反对他的人,也没有不加以赞赏的。梁启超更将王安石视为千古一人,他大为感叹:“悠悠千年,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在他看来,王安石无人能比,“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他惊呼,如果在尧、舜、禹之后寻求一个完美之人,那么,只有一位王安石可以胜任。
说起来,后代那些肯定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人,恰恰都是从义利之辨入手,主张学以致用的。像清代的颜元和龚自珍,他们与王安石都有着十分相近的思想理路。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公然扯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旗,也很看不起注疏考据的学问,对于所谓“宋学”、“汉学”,他是“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他反对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的空虚,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所以,颜元“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经之事功立论”。宋儒之所轻,正是颜元所推重的。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意识,他认为王安石的被诬陷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宋朝的不幸。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怀抱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也十分推崇王安石,是王安石的粉丝,“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煌煌万言的一篇文章,手抄九遍,非粉丝不能办到。
到了梁启超的时代,中国人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知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不再迷信那些空谈义理的儒家经典,也不再担心讲经济、讲利益会被人指责了,他们面对着列强的欺辱、侵略,国家的衰微、腐败,以及经济的凋敝,军队的涣散,吏治的腐朽、糜烂,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可以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于是,王安石就被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后来的孙中山诸公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王安石的思想。
那时,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作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胡适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我常常在想,“天妒英才”这四个字,用在王安石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太杰出,太强悍了,太超前了,于是连老天都嫉妒,天夺其命。他变法不是为了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彻彻底底的赤子之心。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失败了,受谤将近一千年,直到百年前与梁启超相遇——梁启超是王安石的知己,他作《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是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安石得此知己,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最后,我想以一首《金缕曲》结束这篇序文:
寂寞千年久。
更谁能,
推心置腹,
呼朋唤友。
自古英才多奇志,
不信蝇营狗苟。
是与非,
惟天知否。
问道人心何所见,
却原来,只是跟风走。
真心话,
难出口。
任公奋作狮子吼。
想当年,
神州陆沉,
举国悲愁。
只取临川成一梦,
怎奈杯中残酒。
看群贤,
争说肥瘦。
毕竟文章惊海内,
且由他,覆雨翻云手。
知己在,
何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