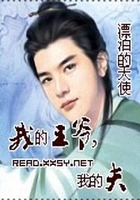要想正确判断人类目前的自然状态,就不得不首先对人类的起源进行考察,研究人类在形成初期的状态。这样做固然是很重要的,然而我却并不打算研究人类在连续不断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构造,也不想停留在只是简单地追问,人类如何从最初的状态逐步转变到如今的这种状态的。我并不打算研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长指甲最初不过是弯曲的爪子的说法是否正确;人是否曾经像熊一样全身长满毛发;或者人在最初是否用四肢爬行,目光向下且仅仅局限在一小块范围中,无法看到广阔的大自然,并且因此限制了思想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我只能够提出几乎全凭空想的模糊不清的假设。到目前为止,比较解剖学仍然没什么进展,因而观察家们也无法为任何可靠的推断提供有力的证据。因此,要是不存在可以利用的超自然的知识,也就无法注意到那些由于人类将四肢应用于新用途以及食用新食物所引发的身体内外构造的变化,那我就只能假设:同现在的人类一样,当时的人类一直都用双腿行走,并且也像我们现在一样使用双手,他们目光向前,因而看得到广阔的大自然,也看得到广袤无垠的天空。
在此种生命构造之中,如果剥离了其中超自然的天赋,以及其在漫长历史中获取的人为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只考虑人刚从自然中造出来的样子,就能够看到,人类作为动物,既不像某些动物那么强壮,也不像某些动物那么敏捷,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在所有的动物当中,人体的构造可以算是最完善的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只要能够找到橡果充饥,找到小溪能够解渴,还可以在一棵橡树下睡上一觉,那么其全部需要就都能够得到满足了。
要是大地还能像以前一样肥沃,森林还能像以前一样茂密,树木也不曾遭受刀斧的砍伐,那么自然界一定可以继续为所有的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以及住所。而人类,他们生存在各种动物之间,凭借其观察和学习的能力,从而获得了其他动物的生存本领,并因此具备了其他任何动物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任何动物都仅仅局限于一种本能,而人类在最初也许不具备任何本领,但学会了别的动物的生存能力。人可以吃各种食物,然而动物却只能吃其中的几种,所以人类比动物更容易找到食物来充饥。
因为人类自从幼年起就开始长期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中生活,他们不得不忍受疲劳,也没有可以御寒的衣服,没有可以防身的武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和食物,不得不和猛兽搏斗,并且为了逃避野兽的追击而不得不拼命地奔跑。人类因此而获得了强壮的体质,且几乎不会改变。人类的孩子一出生,就具备了从父母那里遗传的优良体质,并且在赋予这种体质的环境中得到了不断的磨炼,因而获得了人类所特有的生存能力。就像斯巴达的公民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斯巴达人仅仅留下天生强壮的孩子,加以培养,使其更加强壮有力,而杀掉其余体质较弱的孩子,自然对人类也是如此。这一点与现在的社会完全不同,在我们的国家,父母将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累赘,在孩子还没有出生前不管是否强壮都一律杀掉。
对原始人而言,其所能理解并掌握的唯一工具只有自己的身体。原始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用途,而我们的身体却由于缺乏锻炼什么能力都不具备。现代技术的存在让我们变得柔弱而笨拙,而原始人却不得不使自己变得强壮而敏捷。假如有斧头,他们是否还有力气用手折断树枝呢?假如有投石器,他们是否还能将石块飞快地扔出去?假如有梯子,他们是否还能敏捷地爬上一棵树?假如有马,他们是否还能跑得这么快呢?如果文明人有足够的时间使用机器,毫无疑问他必然能够打败原始人;然而,假如让他们赤身裸体地站在一起,没有任何武器,你会惊异于文明人和原始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你将能够看到,一个能够随时全力以赴、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变故,甚至始终具备一切力量和技巧的人,占据的无比优势!
从霍布斯的观点来看,人天生勇猛并且争强好胜,喜欢打斗。但是另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正如康贝尔兰德和普芬道夫的观点,原始人几乎是所有动物当中最为温顺胆小的,他们始终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甚至会被最微弱的声音或者细小的动作吓到,落荒而逃。每当原始人遇到陌生事物时,这种情形就可能会发生,我也毫不怀疑,他会被任何一种新奇事物吓到,因为他无法判断出在他眼前的事物是否对他有利,他也无法将可能遇到的危险同自己的能力作出正确的对比。但是在自然状态中,这种情形并不经常出现,那时,所有事物都以一种单纯的方式进行,在大地上不会有突然的或者持续不断的动荡发生,通常这种动荡是人们在一起生活时,人们的欲望碰撞以及胡作非为所引起的。原始人在各种动物之间散居,他们不断同野兽争斗,因而能够将野兽同自己的能力迅速作出对比。
一旦他发现自己在智巧上胜过野兽的程度远远高于野兽在力量上胜过自己的程度,他就能够明白自己再也无须害怕野兽了。当你看到一只熊或一只狼和一个强壮、敏捷、勇敢的(所有原始人都这样)又使用石块或者棍子的原始人搏斗时,你会发现至少双方都存在危险。这样,在经过一番试探后,这些并不喜欢相互攻击的野兽知道这些原始人同它们一样的凶猛,便不会再攻击人类。但是如果某些野兽在力量上胜过人的程度远远超过人在智巧方面胜过它们的程度,那么,原始人就同其他弱小动物一样处于相似的境地。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能够继续生存。何况原始人还具备另一个优势:他和别的动物跑得一样快,并可以在任何树上找到安全的避难场所。当其面对野兽时,就能够自由选择是进行搏斗还是逃跑。此外,并非所有动物都能够天然地攻击人类,除非其迫于自卫或者是饥饿难耐时才会那样。动物也不会天生就反感人类,这种反感似乎表明某种动物注定将要成为另一种动物的食物一样。
毫无疑问,黑人和原始人就是因此而不害怕在树林里遇到野兽。生活在委内瑞拉的加拉伊波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绝对安全,并且不存在任何的不方便。就如弗朗索瓦·柯勒阿所言,那种人只带着弓和箭就足以在树林中自由行走,从未听说他们之中有人被野兽吃掉。
但是,人类有更加可怕的敌人,并且不存在任何的防御办法,即年幼、衰老以及各种疾病所导致的天然虚弱。人类弱点的不幸证据正在于此,每种动物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前两种,最后一种则主要是存在于那些社会状态之中的人里。说到年幼,很明显,人类的母亲能够随身带着自己的孩子,比起那些忙碌地往来于觅食与喂养孩子之间的动物母亲,她们显然更容易养育孩子。但是,假使母亲不幸死亡,那么孩子随之而去的可能性就会很大;然而任何动物都存在这种危险,幼崽在足以养活自己之前,总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依赖自己的母亲。人类的幼年时期比动物的幼年时期更长,其寿命也相应的更长,所以任何动物在这一点上都是大同小异的。尽管动物在幼年时期与幼崽数目上仍然存在别的规律,但这与我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干。老年时期的人类活动减少,分泌物也随之减少,对食物的需求也会随觅食能力的减弱而减少。尽管原始人不可能得风湿、痛风这种疾病,然而衰老却成为人所面对的痛苦中最无法缓解的一种痛苦。继而他们会悄然死去,没有人会注意,甚至连他自己都不会意识到。
对疾病这一话题,我并不愿意重复多数健康人提出的反对医学的肤浅谬论。可是我想问,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医学最不发达的地方的人们要比医学最为发达的地方的人们的寿命更短?假使我们人类自身所导致的疾病比医学所能治疗的疾病更多的话,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人类的生活方式变得极度不平衡,有一些人过于安逸,而另一些人却过度疲劳。纵情的欢愉损害了我们的感觉器官,过于精致的食物使我们摄入过多的热量,开始变得消化不良;与之相对的,穷人们吃的食物都有损于他们的健康,并常常不足以果腹,这让他们一旦有机会便会暴饮暴食,以至于因此伤害脾胃。
如上所述,再加上熬夜、不节制、各种情欲的放纵、精神衰竭、身体疲劳,以及各种无以计数的痛苦和焦虑掺杂在一起,让人类很难享有片刻的安宁。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大多数疾病是由我们自身造成的,而如果我们想摆脱这些疾病,就不得不转而坚持自然所赋予我们的最为单纯、简朴和清静的生活。假使自然注定让人类健康,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思考就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状态,一个正在思考的人毫无疑问是一种痛苦的动物。在我们想到原始人的优良体质的时候——那些至少还不曾被烈酒毁坏的身体,一旦想到他们除了衰老和受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的不适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段疾病增多的历史。最起码在柏拉图看来是这样。柏拉图根据波达利尔和马卡翁在特洛伊城被围困时曾经使用并且推荐的药方推断,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药物会导致一些疾病。赛尔斯也曾经说过,希波克拉底发明的节食疗法同样适用于当代的人。
原始人很少会生病,因此并不需要医疗,当然也更不需要医生,在这一点上,原始人同动物差不多。从猎人那里就可以得知这一点,当他们在打猎时,是否见到过受伤的动物。他们肯定经常看到受过重伤的动物的伤口能够自动结痂,或者是动物折断了骨头和四肢也不需要任何的外科手术,经过一段时间后伤口会自愈,它们仅仅需要过正常的生活,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护理或者疗养;它们不需要去忍受手术的痛苦,不存在药物的毒害,也不会受到禁食的折磨,其伤口照样能够愈合得很好。总而言之,无论医学对人来说是何等地有用,原始人在生病时只需要依靠自然,除了疾病以外并没有可担心的事,其生存状态令人向往。
因而不可以将原始人与我们常见到的人混为一谈。大自然用一种偏爱之心在照管着所有的动物,而且他似乎极其珍视此种权利:不管是马、猫、牛,还是驴,在野外生存的它们普遍都比那些圈养的要高大得多,而且也更加有活力、有朝气,更加强壮和勇敢。这些动物一旦被人们驯养,它们就丧失了大半优点,就好像我们对它们所有的关怀、养育,对它们都只是一种损害。当然人类也是如此,一旦他具有了社会性,成为一个奴隶,那么他就会变得虚弱、胆小,并且奴性十足。他们委靡安逸的生活方式使其力量和勇气被完全地消磨掉。原始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别,甚至比野生动物与驯养动物的差别还要大。因为,尽管自然并没有区别对待人与动物,但是人却通过使自己沉溺于比驯养的动物更加安逸的生活中,而更加堕落。
因此,原始人赤身裸体并且没有住所,不具有我们所认为必需的任何奢侈品,然而并不因此而不幸,这些也并不会对其生存造成任何的威胁。假使他们身上没有毛发覆盖,那是由于他们生活在温暖的气候中,无须此类保护。但是假使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国度,那么,他们很快便学会把捕获的动物的皮毛披到自己的身上;假使他们可以只靠两条腿走路,那么他们就会用双手来保护自己和获取食物。即使他们的孩子们走得很慢,很难学会走路,他们的母亲也可以轻易地携带他们。因而他们具有其他动物并不具有的优势,因为动物在遭受追击时,动物母亲不得不抛弃其幼崽或是放慢脚步与其一起跑。总而言之,除非我们认为存在一种偶然的巧合(将在后文提到)——虽然不太可能,否则我们很容易认为,第一个为自己制作衣服、建造住所的人是在制造自己根本不需要的累赘。因为没有这些,他同样可以生活,他不会在成年后却无法忍受自己自小就一直过的生活。
就像其他不大思考的动物一样,孤独、闲散而且还时刻伴随着危险的原始人必然喜欢睡觉,只要不思考,他便一直这样睡着。他不得不睡得很警醒,因为保护自己是他主要,甚至可以算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他不得不经常锻炼攻击和防卫的能力,或是用于捕获猎物,或是防止自己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与此相反的是,原始人的那些用于享受安逸和情欲的器官自然极度不发达,也不相容于任何精致的东西;然而听觉、视觉和嗅觉却发展得非常灵敏、细致。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动物的状态,然而根据旅行家所说,这也是多数原始人的状态。因此,好望角的霍屯督人用肉眼即可看见远处海上的船,然而荷兰人却需借助望远镜才能够看到;美洲的原始人能像最优秀的猎狗般用嗅觉去追踪西班牙人;另外,原始人即使不穿衣服也不觉得难受,他们还可以吃大量的辣椒,能像喝水一样喝下最烈的欧洲白酒。
直到目前为止,上述内容只是谈到了原始人的生理方面,之后我将谈原始人的精神和智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