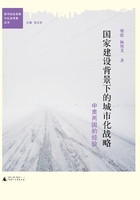以上所说的是其人民达到适于代议制政府的属地的情况,然而,还有另外一些并没有达到这种状态的属地,倘若想掌握它们的话,就必须由支配国家去统治,或者由支配国为此目的,委派合适的人去统治。倘若它是在该附属人民的现有文明状态下最便于他们向进步的更高阶段过渡的统治方法的话,那么,与其他任何方式一样,这种统治方式就是合法的。如前所述,在一些社会状况下,为使人民适应较高文明所特别欠缺的方面,强有力的专制政治本身就是对他们加以训练的一种最好的统治方式。也有一些社会,单纯的专制政治确实没有什么有益的效果,因为专制政治所起的教育作用早已经发挥过了,但是,这个社会的人民本身却不存在自发的进步动力,此时,进步的几乎唯一的希望便都依赖于拥有一个好的专制君主了。
在本地的专制政治下,能拥有一个好的专制君主是一件稍纵即逝并且极为罕见的偶然的事情,然而,当该地人民在一个更加文明的国家的统治下的时候,那么,该国应当可以继续不断地提供这种好的专制君主。统治国家应该可以为其臣民持续不断地做专制君主所能做的全部事情,这样提供的专制君主因为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国家便可以避免野蛮的专制政治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因为他们的才能便可以期望他们具有先进国家的所有经验。这便是自由的人民对野蛮人民以及半野蛮人民的理想统治。我们不必指望这种理想必然实现,然而,除非是做到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这种理想,否则的话,统治者便犯有对一个国家所能负有的最崇高的道德委托失职的罪行。倘若统治者不以这种理想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便是自私的篡夺者,便是与世世代代以来基于自己的贪婪和野心把人类大众的命运当做儿戏的人们,犯有同等的罪。
落后人民直接隶属于较先进的人民或者处于较先进人民的完全的政治支配之下,这已然是一种通常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将会迅速成为普遍的情况,所以,从目前来看,很少有什么问题比怎样组织这种统治更加重要,就是怎样使这种统治成为对从属人民来说好的统治而非坏的统治,怎样提供给他们可能达到的最好的政府以及最有利于未来持久发展的条件。然而,使政府适合于这一目的的方式,决不像能够自治的人民的好政府所需具备的条件那样被人们充分了解,甚至可以说,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在那些肤浅的观察家看来,事情好像是非常容易的,倘若印度(比方说)不适于治理自己,那么,在他们看来,所要做的就是要有一个大臣去统治它,而和所有其他英国大臣一样,这个大臣必须对英国议会负责。然而,不幸的是,虽然这是试图统治一个属国的最简单的方式,但却几乎是最坏的一种方式。这种想法恰恰表明其拥护者完全不理解好政府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在对一个国家人民负责的情况下统治那个国家,与对另一国人民负责的情况下统治一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就前一种情况来说,其特点是自由胜于专制,然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其特点则是实行专制,唯一的选择是不同专制政治的选择。是否两千万人的专制一定会优于少数人甚至于一个人的专制,这是不肯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其臣民不闻、不见,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人们所实行的专制很有可能比对其臣民有一些了解的人们所实行的专制更坏。通常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因为权威的直接代理人是以一个实际上并不在场的主子进行统治,而且是以一个有着无数更为迫切利益要照顾的主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便会统治得更好。主子可以责成这些代理人负严格的责任,可以临之以重刑,不过,处罚是否恰当,则往往令人怀疑。
即便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并不存在思想和习惯方面的极端不一致,由外国人来统治一个国家总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也是很不完善的。外国人不会和本国人民有同感,他们不能按照一件事情在他们自己心里的情况,或者按照这件事情影响他们自己感情的情况,以判断这件事情将如何影响那些从属人民的感情,判断这件事情将如何浮现在这些人民的心中。这个国家的那些具有一般实际能力的本地人似乎本能地便可以知道的事情,他们却必须通过学习和经验慢慢地,而且终究是不完全地学会。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对之进行立法的习惯、法律以及社会关系,并不是他们从幼年时期开始就熟悉的东西,而是全然陌生的。关于这些详尽的知识,他们必须依靠本地人的介绍,但困难就在于他们不知道应该去信赖谁。
当地的人民猜疑他们、害怕他们,甚至于憎恶他们,除为了本身的利害,当地人很少来找他们,因此他们便轻易认为,那些对他们卑躬屈节的人是可以信赖的。他们的危险在于看不起本地人,而本地人的危险则在于不相信外国人所做的那些事情可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这些都是那些真心希望统治好一个国家的外国统治者必须克服的一部分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始终会是一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的工作,而且要求主要行政官员具有极高的能力,其部属必须有较高的水平。要想把这样的政府组织好,必须保证该项劳动的进行,必须发展该项能力,而且还要把这种能力的最高典范置于最信任的位置上。这样一个权威,他从没有从事过这种劳动,完全不具有这种能力,甚至多半不清楚这种劳动或能力在任何特殊程度上是必要的,那么对其负责就不能被认为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有效方法。
一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治理自己的国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件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情,但是由一国人民来治理另外一国人民,则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也不能存在的事情。因为,被治理的一国会被另一国人民当做免费的养兔场或养鱼塘,一个为他们国家居民的利益而努力经营的人畜农场,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但是如果被统治者的利益是一个统治政府的本来业务的话,那么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本国人民直接去照料,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委派一些比较优秀的人去照料。而对这些被派去照料的人来说,他们履行该项职责的指导标准不能依据他们本国的意见,那些意见也不能是他们履行这些职责的方式的合格的裁判者。不妨假设一下,假使英国人对他们本国的事务也像他们对待印度人的事务那样一无所知、漠不关心,那么他们将怎么统治自己的国家。其实,这个比较并没有完全恰当地阐释清楚这件事情,因为,一国人民对国家政治一无所知、漠不关心,也许只是因为对政府的默从和听之任之。而在印度的情形,像英国人这样在政治上积极的人民在习惯的默从之中却常常进行几乎总是不适当的干涉。
印度人到底是繁荣还是没落,是进步还是退步,决定这些的真正原因往往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本身的视野。他们缺少用来怀疑这些原因存在所必要的知识了,更不用说那些判断这些原因所起的作用的知识,那些知识就更少了。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可以被管理得很好;也可以说,这个国家不管管理得再怎样不好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诱使他们去干涉和控制他们代表的行动的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强迫当地人接受英国人的观念,例如,通过改革宗教的措施或者有意无意地触犯当地人民宗教感情的各种行为。目前,这种在统治国家中的舆论的错误指导,从普遍存在于英国的公立学校中,依据学生或者他们的父母的意愿讲授《圣经》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有启发性的例子(这些例子除了能证明正义和公平,以及期待于真正确信的人们身上的那种公正无私以外,没有其他的意思)。根据欧洲人的观点,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能显出公平,而且不会因为宗教自由而遭到反对的了。但如果从亚洲人的观点来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