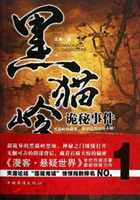或许没有必要多加说明,这条教义只适用于能力已经成熟的人类。我们没有说这条教义也适用于幼童,或适用于尚在法定成年男女以下的青年。对于尚需要他人照管的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行动也需要加以防御,正好像对外来的伤害也需要加以防御一样。根据同样的理由,对于那种种族自身尚可被视为未届成年的社会当中的一种落后状态,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边而不加以讨论。在自发的进步过程中,早期的困难是这样严重,以至于在克服困难的手段方面竟难以容许有所选择;因此,如果遇到一个富有改善精神的统治者,他就有理由使用任何便宜的方略达成一个非此不能达成的目的。
只要目的是使他们有所改善,而且所用的手段又属于正当,那么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就是一个合法的形式。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没有达到能够借对等的和自由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都是无所适用的。还没到那样的时候,如果人们有幸能找到一个阿克巴(Akbar)或者一个查理曼(Charlemagne)之类的大帝存在,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就只有选择服从。但是,一旦到了人类获得可以借说服或劝告来引他们去自行改善这种能力的时候(这个时期,所有的国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达到,这里也必须提到我们自己),强制的办法,无论是以直接的形式还是因为产生反对的声音而加以痛惩的形式,都不能再成为目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而被许可使用的手段,因而只有以保障他人安全为理由才能算是正当的行为。
在这篇论文中,应当说明,只要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所引申出来且有利于我的论据的各点,我都没有加以引用。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的确最后总是把它归到功利上去;但是,这里所说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做前进的存在而以他的永久利益为依据。我要特别地强调,这样一些利益是享有威权来使个人自动屈服于外来控制的,当然只是在每人涉及作他人利益的那部分行动上。如果有人做出了一个有害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一个一看就知道要对他进行处罚的事件,对此可以用法律来惩办,或者当法律惩罚不能妥善适用时,也可以用普遍的谴责来处理。还有强迫人们去做更多对他人有益的行动,也算是正当的:比如说到一个法庭上去作证;在一场共同的自卫斗争之中,或者是在为他所受其保护的整个社会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联合工作之中,担负他的一份公平的任务;又比如说参加某些有益的活动,比如出力去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挺身保护一个遭遇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等等。总之,只要明显是一个人在义务上应当做的事而他没有做时,那么就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
要知道一个人不仅会用他的行动对他人造成不利,也会因为他的不行动而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这都是正当的。当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施行强制,需要比在前一种情况下更加慎重。一个人做了危害他人的事,就必须为这件事负责,这是规则;对比他不去防止祸害,而要他必须为此负责,那可能就是例外了。尽管是例外,在许多足够重大和足够明显的事情上却足以证明此举是正当的。
一个人在涉及除他之外的一切事情上,对于关系到与他有利害的那些人在法理上都是应当负责的,并且假如需要的话,对于作为他们的保护者的社会也应当是负责的。也经常有些好的理由可以使他不用对此负责;但那些理由必须是出自特殊的权宜之计:不外乎是因为情事本身就属于这一类,如果由社会依据它的权力的任何方法来对他加以控制,倒不如让他自己考虑该怎样裁处,那样整个看来似乎会办得更好;或者是因为假如试图加以控制,将会产生其他祸害,要比所防止的祸害还大。应当指出,既有这样一些理由免除了事先的课责,这时主事者本人就应使自己的良心站在空着的裁判席,从而保护他人的那些没有外来力量保护的利益;因为这事情不容许他在同胞的裁判面前有所交代,所以要更加严格地裁判自己。
但对于社会来说,也有这样一类有别于个人之处的行动,只有(如果还有的话)一种间接的利害。这类行动的范围包括一个人生活和行为中仅仅会影响到自己的全部,或者说如果也会影响到他人的话,那也得有他们自愿的、没有因为被蒙骗的同意和参与。必须讲明,我在这里说仅仅影响到本人,意思是说这种影响是最初的,是直接的,否则,只要是影响到本人的都会通过本人而影响到他人,这也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要是可根据这个可能的事情因而反对,也势必是需要加以考虑的。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这个领域包括:第一,意识的内在境地,要求是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要求是感想和思想的自由;要求是不论在实践的还是在思考的、道德的、科学的或神学的等所有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
讲到刊发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因为它属于个人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行为,看起来像是属于另一原则管辖之下的;但是由于它和思想自由本身几乎同样重要,其所依据的理由也大部分相同,所以在实践中和思想自由是分不开的。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志趣和趣味的自由;要求能够顺应自己的性格来自由地制订自己的生活计划;要求有自由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因此而导致的后果。这种自由,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伤害到我们的同胞,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背谬、愚蠢或错误的,都不应该遭到他们的阻碍。第三,随着每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种限度之内,个人之间还有相互联合的自由;这也就是说,人们在不伤害到他人的时候有自由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都是成年人,而又不是出自受骗或被迫就可以。
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如果上述这些自由整体说来在那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上述这些自由在那里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没有限制的,那就不算是完全的自由。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就是在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人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时,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每个人不论是身体的健康,还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都是他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如果人类彼此容忍并各自按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那比强迫每个人都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得到的收获要多。
虽然这条教义绝对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并且在一部分人看来还有些不言自明的意味,但是它却一直与现在存有的意见和实践的一般趋势相反,它比其他的任何教义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曾经尽其全力试图(照其所见)强迫人们适应它对人的优越性和对社会优越性的观念。古代的共和国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公共权威去制约私人行为的每一部分,而对此,古代哲学家也表示赞同;他们的根据是国家对每一公民的全部智力和体力的训练都是有着深切关怀的。被强敌包围着的一些小的共和国,经常有被外来攻击或内部骚乱推翻的危险,即使在一个短的时间里,如果精力和自制稍微有所松懈,也容易造成致命的损害,因而就不允许它们等待自由发生健康的永久的效果——也就在这样一些小的共和国里,这种想法曾经是可以被认可的。
在近代世界中,政治群体的力量比较大,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俗界的和灵界的权威分开了(这就把对于人们良心的指导权交给了另外一个不控制人们世俗事务的手里),这些情况阻止了法律对于私人生活细节的那些大量的干涉。可是道德压迫的一些机器又被更有力地挥动起来,去反对在仅关本人的事情上与统治意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比在社会性的事情上反对得还要厉害。以在参加形成道德情绪中最为有力的宗教来说,它就几乎不被教吏团的野心控制着——它企求控制人类行为的每一部门——即被清教主义的精神控制着。就是反对某些旧时宗教最为有力的近代革新者,在主张精神统治的权利方面也并不落后于一些教会或教派。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孔德(Comte),他的社会思想体系,就像他在《论现实的政治》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对个人的专制(尽管用道德的工具多于用法律的工具),但竟然超过了古代哲学家中最严格的纪律主义者在其政治理想中曾经考虑过的任何东西。
把思想家个人的特殊学说排除在外,世界上还广泛地存在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既用舆论力量,也用立法力量,把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不适当地加以延伸。既然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趋向于加强社会的权力从而减弱个人的权力,可见这个侵蚀就不是那种趋于自动消失的灾祸,相反是会增长得越来越可怕的。无论作为统治者还是公民同胞,人类都倾向于把自己的意向和意见当做行为准则来强加于他人,这是有着人类本性中难免带有的某些最好和最坏的情绪的有力支持的,以至于几乎从来无法加以约束,除非是因为缺乏权力;除非能筑起一条道德信念的坚强堤障来反对这种祸害,否则权力不是在降减,而是在不断地增加:这样,在世界现存形势之下,我们就只能看到它在增长了。
为了便于罗列论述,本书不打算一下子就进入一般的论题,而在开头部分只限于这个论题的一个分支,在这一个分支上所列举的原则,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某一点上被流行意见所认可的。这一分支是思想自由,还有与它同源的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这些自由,虽然已经在一切宣称宗教宽容和自由制度的国度里成为了政治道德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所倚靠的哲学上和实践中的依据,恐怕在一般人心中还没有形成概念。甚至有些舆论,领导者也未必像可以期待的那样已经清楚地彻底认识了。那些依据,一旦经过正确的理解,就不只适用于这总题的一个部分,而且可以有宽广得多的应用;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一部分的彻底考虑,是对于其余部分的最好的导言。当然,我在这里所要讲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并不新颖。所以,倘若说关于这个三个世纪以来已经被时常讨论的题目,我还敢再作一番讨论的话,那么我只有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