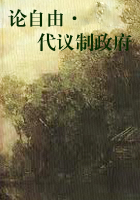在民主共和国,人们有巴结大多数的倾向,从而导致这个倾向立即渗入各个阶级。这是可以用来谴责民主共和国的主要方面之一。
对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这种谴责很有道理。在这里,多数的统治如此专制和不可抗拒,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必须放弃某些公民权利,甚至要放弃做人的本色。
在进入美国政界的那一大群人中,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具有豪爽的性格和刚正不阿的精神了,而豪爽与刚正不阿是昔日美国人曾引以为荣的特质,任何时候都会将其看做伟大人物的突出特点。乍看上去,仿佛现在所有美国人的思想都是出于同一个模子,以至于他们可以分毫不差地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不错,外国人有时会遇到一些离经叛道的美国人,他们会慨叹法律的种种弊端、激愤于民主的任性多变。这些人往往会谈到那些败坏了国民性的缺点,并指出可以纠正的方法。但实际上,除了你以外,而你这个他们选择的不会向别人述说,他们倾诉隐秘想法的对象,只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过客。他们愿意把真心话告诉你,但这对你并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到了公共场所,便不这样讲了。
如果将来有一天,上述这些被我转述的话被美国人读到,我猜想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读者们将高声谴责我;第二,其中大多数人将在内心里原谅我。
在美国我曾经听到人们谈论祖国,也在人民中间见到真正的爱国主义,却无法在国家的领导者身上寻找到这种表现。专制主义对其所治人民的败坏影响为什么远远超过对其执行者的?用类推方法不难解释其中原因。在专制君主国,国王往往品德高尚,但朝臣多为卑鄙无耻之徒。当然,美国的当选官员不会称他们的主人即选民为“大人”或“陛下”,这好像与君主国的朝臣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不断称赞其主人天生明情达理,却从不争论他们的主人到底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美德。因为他们确信主人具有一切美德,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一定会有。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送给主人,供其宠爱而纳为嫔妃。但他们同样出卖了自己,因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观点。
在美国,道德家们和哲学家们,虽然不必用寓言的形式来掩盖观点,但当他们壮着胆子讲述令人不快的真理之前,总是加上一段:“我们知道,听我们讲话的人民品德高尚,不存在使自己有失主人身份的缺点。假如听我们讲话的人士,其品德和学识并非好得可以比别人更值得享有自由的话,我们就不说这些了。”
在路易十四面前献媚的人,都不能奉承得比这种引子还好。
就我来说,我确信在任何性质的政府中,下贱的献媚者一定会趋炎附势。而且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人们自我侮辱,那就是防止任何人拥有无限权威,即不赋予任何人可以诱使他人堕落的最高权力。
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来自多数的无限权威
导致民主共和政体破灭的是政府滥用权力,而非它们无能——美国的共和政府比欧洲的君主政府更集权和更强大——由此产生的危险——麦迪逊和杰斐逊对此的看法
政府通常由于无能或者暴政而垮台。在前种情况下,属于权力自行离开政府;在后种情况下,则是权力被人夺走。
许多人在看到民主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时,就以为是因为这些政府软弱无能。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党之间燃起战火,政府就会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但我并不认为,一个民主政权天生就会缺乏人力和物力;恰恰相反,我相信一个民主政府之所以垮台,基本上是由于滥用人力和物力。无政府状态总是由于暴政或管理不当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政府无能。
我们不能把稳定与力量,或把一件事情的伟大性与其持久性混为一谈。在民主共和国,因为指导社会的权力[5]会经常易手和改变方向,所以它并不稳定。但是,在权力易手和改变方向时,它的力量也几乎同样是不可抗拒的。
在我看来,和欧洲专制君主国政府一样,美国的共和制政府也是集权的,它的力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不认为它会因为软弱无力而垮台[6]。
假使有一天自由在美国毁灭,那也一定是多数的无限权威所导致的。因为这种权威将会使少数忍无可忍,从而诉诸武力。那时将出现无政府状态,但引起这种状态的则是专制。
麦迪逊总统就发表过类似看法(见《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万人文库版第266页及以下各页)。
他说:“对共和政体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不仅要保卫社会不受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防止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遭受另一部分人的不公正对待。……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会的目的。人们曾经一直追求,并将全力以赴地永远追求这一目的,直到成功为止,或是直到在追求中丧失自由而被迫停止。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较强的派系学会利用这种社会情况随时联合起来压迫较弱的派系,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自然而然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使软弱的人失去可以凭恃的抵抗强者的暴力的任何保障。在这种状态下,原来较强的人也会因为不满社会动荡的现状,而愿意服从于一个既能保护弱者又能保护自己的政府;在出现这种愿望之后,同样的动机又促使较强的派系和较弱的派系同意组织一个能够保护一切强的和弱的派系的政府。不必怀疑,如果罗得岛州脱离联邦而独立,那么该州以人民名义在极其有限的土地内进行统治的权力,必将因多数的暴政而证明它完全脱离人民,而且它是由那个需要这种暴政的多数迫不及待地弄出来的。”
杰斐逊也说:“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并非我担心的唯一问题,或许还不是我担心的主要问题。立法机构的暴政才是真正的最可怕的危险,而且在今后许多年仍会如此。行政权虽然也会出现暴政,但要在很久以后。”[7]
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引用杰斐逊的话,而不是其他人的,因为我认为他是迄今为止宣传民主的最坚强的使徒。
注释
[1]在考察联邦宪法时,我们已经看到联邦的立法者曾反对过这种力量。联邦政府在工作中比州政府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直接取决于立法者的努力。但联邦政府只主管对外事务,各州的政府才是在实际上管理美国社会的。
[2]只是马萨诸塞州从1780年至今公布的立法文件,就已装订成三大卷。还应当指出,我说的这部文件汇编是在1823年经过修订而辑成的,其中已剔除大量旧的或已经失效的法令。要知道,居民不如法国一个省多的马萨诸塞州,在全美国还算是法律最稳定的州,但它也为立法工作不断地投入大量的人力。
[3]任何人都不会主张一个民族可以滥用它的武力去反对另一个民族。然而,一个大国中的政党,却可变成一国中的小国。如果承认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实行暴政,那怎么能不承认一个政党也可以对付另一个政党呢?
[4]在1812年战争时期,巴尔的摩发生了一个多数专制引起的暴力事件。在这个时期,巴尔的摩人非常支持这场战争。当地的一家报纸对居民热烈支持战争的行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人民因此自动集合起来,捣毁了报社,袭击报社人员的住宅。有人还想召集民兵,但没有成功。最后,官员为了保护生命受到愤怒的公众威胁的无辜者,只能把他们当做罪犯投入监狱。这项预防措施并未生效。人民在夜里又集合起来,当地的行政官员去召集民兵来驱散人群,也没有成功。监狱大门被砸开,一名记者当场被杀,人民还要处死报社的其他人员,但经陪审团审理后,这些人被判无罪。有一天,我对宾夕法尼亚的一位居民说:“请您告诉我,为什么在一个由教友会教徒建立的因宽宏大量而出名的州里,已经获得解放的黑人依然不能享有公民权呢?他们照章纳税,让他们同样参加选举岂不是很公正吗?”他回答说:“请不要这样侮辱我们,你去看一看我们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是多么公正和宽宏大量。”“这样说来,在你们这里,黑人是享有选举权的了?”“当然。”“那么,今天早晨我在选民的会议上为什么没有见到一个黑人呢?”这位美国人说:“这不是法律的错误。黑人确实有权参加选举,但他们总是故意不来出席。”“他们也太谦虚了。”“啊!不是他们拒绝出席,而是他们害怕到这里会受虐待。在我们这里,有时法律因为失去多数的支持而失效。要知道,多数对黑人最有偏见,各级行政官员也没办法,无力保证黑人行使立法者赋予他们的权利。”“怎么!享有立法特权的多数也想享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
[5]权力可能集中于一个议会之手。这时的它虽然很强大,但不稳定。如果权力集中于一个人之手,那它可能会不太强大,但非常稳定。
[6]我认为不必提醒读者注意,我在此处和在本章其他各处说到的多数的专制,不仅指联邦政府,而且也指各州的政府。
[7]《1799年3月15日杰斐逊致麦迪逊的信》。(参看《杰斐逊文集》第7卷第312页,华盛顿,1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