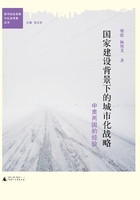在上一章里,我考察了在民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身份的平等是怎样改变了公民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我想再进一步论述,深入到家庭的内部去研究。在这方面,我的目的不是寻找新的真理,而是试图阐明已知的事实和我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成员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新的关系,父子之间昔日存在的差距已经缩小,长辈的权威即使没有全部消失,至少也已经大大减弱了。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美国,但它更加引人注目。
在美国,从来就不存在罗马人和贵族阶级就“家庭”这个词的含义所理解的那种家庭。美国人只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才具有传统的家庭意识。在孩子的童年时期,父亲实行家庭专政,子女不得抗拒。由于子女的年幼无知,使这种专政成为必要,借着维护子女们利益的理由以及父亲无可争辩的优势,又使这种专政显得合情合理。
但是在美国,子女成年之后,那种必须服从父母的关系便逐渐松弛。他们先是在思想上自主,不久便在行动上自主。严格地说,美国人是没有青年时期的,少年时代一结束,他们便自己闯天下,开始踏上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果认为这是一场家庭内部斗争的结果,做儿子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违反道德的办法获得了父亲拒绝给予他的自由,那将是十分错误的。促使做儿子的要求自己独立的那些习惯与原则,也使得做父亲的不得不承认儿子享有独立是他不可抗拒的权利。
因此,前者绝不会有那种一般情况下人们在摆脱压制他们的权势之后还将长期怀恨在心的愤懑感情,而后者也决不会产生那种在失去权势之后通常会伴随着的痛苦和气愤的遗憾感觉。也就是说,做父亲的早已明白他的权威总有一天会期满,这个期限一旦到来,他便自愿放权;而做儿子的事先也已知道,他独立的日子必将到来,可以毫无悬念地获得自由,这就像一份财产必归他所有,谁也不想来抢似的。[1]
尝试阐述一下家庭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与我们眼前即将完成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密切相关的,也许大有用处。
有一些重大的社会原则,要么被一个国家到处推行,要么不准在各地存在。
在有着森严等级的贵族制国家里,上层人物从来不向其统治下的全体臣民直接发出呼吁或求援,因为人们彼此都受一定的关系约束,所以上层人物只要发号施令就可以了,其余的人保证追随。这种情况也见于家庭以及由一个人领导的一切社会团体。在贵族制国家里,社会实际上只承认父亲的存在,他是不可怀疑的一家之长,做子女的只能通过父亲与社会间接地发生关系。社会管束父亲,父亲管束其子女。因此,做父亲的不仅具有管教子女的权力,而且也被赋予了向子女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父亲既是家庭的创造者,又是家庭生计的维持者,而且也是家庭里的行政长官。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触及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并且以同样的法律直接地治理每一个人,不需要有父亲那样的中间人存在。在法律上,做父亲的不过是一个比子女年长和有钱的公民而已。
当绝大多数人的身份极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永久性的时候,关于首长的观念就在人们的幻想中成长起来;这时,即使法律并未规定这个首长的特权,习惯和舆论也会让他自然地享有。反之,当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不再永远有高低之分的时候,关于首长的一般观念就将渐渐地淡薄和模糊;这时,即使立法者硬依自己的意志强行把一个人安排在首长的位置上,叫他对他的下属发号施令,那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民情在使这两个人彼此日益相近,并逐渐走向同一水平。
因此,即使我们从未见到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立法机构曾将独享的特权授予家长,我们也不能不确信贵族制国家的家长的权力比民主国家的更受尊重、更为广泛,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首长在贵族制国家的地位总比在民主国家的高,下属则与之相反,即前者低于后者。
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缅怀过去而不是重视现在时,他们更多的是考虑祖先的想法而不是研究自己的想法时,做父亲的便成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天然的和必然的桥梁,成为联结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套环。因此,在贵族制度下,做父亲的不仅是家庭的行政首脑,而且是家庭里传统的继承人和传代人,是习惯的解释者和民情的仲裁人。他说话时,家庭的成员都要洗耳恭听;所有成员对待他时只能毕恭毕敬,并且要始终诚惶诚恐地爱他。
当社会逐渐走向民主,人们开始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作为基本原则,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和合理的,只把传统的信念作为参考而不视为规范的时候,父亲的见解对子女的影响力,正如他享有的合法权力一样,将会大大降低。
民主制度导致的分家,最显著的后果或许正是父子关系的改变。
当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并不富裕时,他将和儿子长期同住在一起,共同参加劳动。习惯和需要的相似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且不得不时刻相互交谈。因此,在这样的父子之间不能不建立起一种不拘形式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做父亲的权威减小绝对性,并且很少讲究尊敬的表面形式。
然而,在民主国家里,这些并不富裕的阶级,正是一个能够使思想产生力量和使民情发生转变的阶级。这个阶级使它的意见和意志到处占据统治地位,甚至最想抗拒它的领导的人,最后也任由自己去仿效它的做法。我就曾见到一些激烈反对民主的人,他们容忍自己的子女用“你”而不用“您”来称呼他们。
因此,随着贵族阶级失去权势,父母昔日的那种严肃的、约定俗成的、合法的权威也消失了,在家庭之内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
总而言之,我不知道整个社会是不是由于这种变化而受到了什么损失,但我确信个人却由此得到了好处。我认为,随着民情和法制逐渐民主化,父子关系会更加亲密而温和,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讲究规矩和仰仗权威;他们之间的信任和眷爱往往是坚定的。看来,父子的天然联系更紧密了,但他们的社会联系却变得松弛了。
在一个民主的家庭中,做父亲的除了表示老人对子女的爱抚以及向他们传授经验之外,并没有任何权力。他的命令或许无人遵从,但他的忠告往往会发生作用。虽然子女们对他可能不是那样毕恭毕敬,但至少会对他表示信任。子女同他交谈不讲究通常的礼节,而是随时随地可以同他谈话,或者向他请教。在这里,家长和长官的身份消失了,但父亲的身份依然存在。
为了判明两种社会情况在这一点上的不同,只需看看贵族时代留下来的那些家书就够了。传统的书信,文体经常是端庄的、死板的和生硬的,而且文字冰冷得使人感觉不到一丁点的热乎气儿。
反之,在民主国家里,儿子写给父亲的信,字里行间总有某些随便、亲密和依恋的表现,一看就知道家庭里建立了新的关系。
这样的变革也在悄然改革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贵族的家庭里,也像在贵族社会中一样,每个人的地位是早已规定好了的。不单是父亲在家庭里自成一级,享有广泛的特权,就是子女之间,他们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子女的年龄和性别,永远决定着他们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并使其享有一定的特权。民主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于把这些壁垒大部分废除或减少了。
在贵族家庭里,长子继承大部分的家产和几乎全部的权利,所以他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家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兄弟们的主人。他尊贵有权,而兄弟们则卑下平庸,依附于他。但是,如果认为在贵族制国家里,长子的特权只会给他自己带来好处,那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话会引起兄弟们对他的忌妒和怀恨。
故此,长子一般都竭力帮助他的兄弟们发财致富,并获得应有的权势,因为一个家族的显赫与否必然反映在它的代表的身上。同样,做弟弟的也会设法协助长兄开拓一切事业,因为族长的显赫和权势使其能更好地扶掖家族的各支。
因此,通常贵族家庭的成员彼此之间联系得极为密切,他们的利益互相关联,他们的想法也比较一致,但是他们的内心很少互通。
民主制度也使弟兄间互依互靠,但其依靠的方式却与贵族的有所不同。
根据民主的法制要求,一家的子女身份是完全平等的,也是自主的。没有任何东西强制他们必须彼此接近,也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他们定要互相疏远。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血统,又在一个家庭里成长,并受到同样的关怀,可以说没有任何特权使他们彼此不同和把他们分成等级,所以他们之间自幼就容易产生亲密无间的手足情感。成年之后,新形成的关系也不会引起他们破裂不和,因为兄弟的情义使他们时刻接近,而不会反目。
因此,在民主制度下,使兄弟们互相接近的不是利害关系,而是对往事的共同追忆,以及思想和爱好的自由共鸣。民主制度虽然要使他们分家析产,但不能使他们的心灵分离。
这种民主的民情,魅力极其强大,以致那些拥护贵族制度的人也不再愿意遵守贵族制度了,并在体验这样的民情若干时日之后,决意放弃贵族家庭的那种毕恭毕敬、刻板冷漠的规矩。只要他们能够舍弃自身原来的社会情况和法制,他们随时都可以接受民主制度下的家庭习惯。但是,这项工作还牵涉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能忍受民主的社会情况和法制,就无法享用民主的家庭习惯。
我对于父子之爱和手足之情所作的论述,从人性本身自发产生的一切情感来说,也应当是合情合理的。
当一种思想或感情是由人所处的某种特殊情况产生出来的时候,一旦那种情况发生变化,它们便随即消逝。因此,虽然法律可以把两个公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当这项法律被废除后,他们便彼此分离了。再没有什么比封建社会把主仆联系起来的那种民情更具有紧密的联结作用了。但如今,这两种人已各奔东西,互不相识了。之前使他们结成主仆关系的畏惧、感激、敬爱的感情已经荡然无存,以致一点点痕迹也没有了。
但是,人类的天生感情却不会这样。即使法律试图以某种方式驾驭这种感情,也很少能够成功;法律在想增进这种感情时,往往也很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感情仅依靠本身的力量就能永远强大。
民主制度几乎使所有旧的社会习惯失效或消失,并鼓励人们去接受和适应新的社会习惯,从而使大部分旧社会习惯所产生的感情消失。但是,民主制度对于剩下的习惯只是做了一点改进,而且往往是赋予它们以原来没有的活力和温和性。
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本章和以前各章所表述的思想。这句话是:民主制度一方面松弛了社会联系,但另一方面又紧密了天然联系;它在使亲族更加接近的同时,却也使公民彼此疏远了。
注释
[1]但是,美国人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像我们法国人所做的那样,做父亲的死后便被剥夺其处理遗产的权利,从而丧失其权力的主要成分之一。在美国,遗嘱的设立效力是无限的。和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一样,在这方面也不难看到,美国的政治立法比法国的要民主得多,而法国的民事立法则又比美国的无限民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法国的民事立法是由一个人一手操弄的,他认为在不直接或间接反对他的权力的一切事情上满足同时代人的民主激情,这是符合他的利益的。只要人民不企图利用他们通行的某些原则去干预国政,他愿意让人民利用这些原则去打理财产和治理家庭。而在民主的激流开始冲击民法时,他也有把握用政治法令得到保护。这种做法既巧妙又自私,但是,这样的妥协办法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长此以往,政治社会总要成为市民社会的表现和形象,而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国家里,再没有比民事立法更具有政治色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