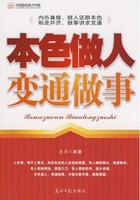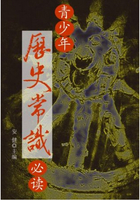汽车后座上的手
刘晓莹译
当人们傍晚远离喧嚣的街道,驱车回到舒服惬意的郊区家里时,白天的一切忙碌与辛酸都会被抛在脑后,付诸云烟。然而第二天早起,绿树成荫的入城街道上,数以百万的车辆排成了二十里的长队,我夹在中间,今日的焦躁代替了昨夜的安享,如果你不是这队伍中的一员,你当然体会不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可就在我自相矛盾的时候,麻烦也正在悄悄降临。
那是一个工作日的早上,我开车从辛斯街驶上肯翰姆大街,头一里路的交通畅行无阻,然后我拐弯进入克兰道尔街,一个紧急刹车使我幸免于与前面的绿色佳比牌汽车相撞。我抬头看了看前面的三条车道,目光所及,都挤得满满的,水泄不通。
我正好被夹在中间车道,不能前行,更不能后退或转弯。我只好干坐在那里,盯住前面的绿色汽车,适时跟进,尽管他五分钟可能才会前移一点点。
无聊却又不能放松警惕的候车间隙,我注意到左边车道开来一辆茶色的旅行车。那天是暮春时候的一个寒冷天,但是,我仍打开车窗,把胳膊伸在外面,我与那辆旅行车近得几乎可以互相擦拭。
我依旧干坐着,但每隔一会儿我都会不自觉地瞟一眼那辆旅行车。司机是个女人,戴着一顶宽边帽子,帽沿被她压得很低。偶尔,她的头向我的方向稍稍移动,然后再不安地转回去,好像想用余光看我,又不想被我发现。
她前面的汽车向前行驶了一两米,她改变引擎的速度,迅速跟进,然后,前面的汽车停住了,她又猛地踩刹车。
旅行车向前移动,它的后窗和我并行,所以,现在我正好看见它的后车座。后座上有东西用毛毯裹着,由于猛烈而又频繁地刹车,使得毯子滑下一点儿,我看见有东西从毛毯的一角伸出来。
我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移开视线,可疲乏的脑筋提醒我,让我再看仔细。于是我再次移回视线,我第一次看的没有错。
那是一只人手,中间的两根指头间有红渍,看起来像是血。再看看裹在毛毯下面的形状……我毛骨悚然,那是个人!
我试着想做点儿什么事。可我的汽车前后左右都被包围着,我企图挥手,去引起旅行车驾驶员的注意,但没有效果。
最后,我开始按喇叭,同时用另一只手惊恐地指着旅行车的后座。我前面那辆绿色汽车的驾驶员不屑地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多希望他此刻能够下车来叫我不要按,但是,车堵成这样,他恐怕连车门都打不开。
这时,旅行车那一行的汽车开始向前移动,旅行车开到我前面,渐渐加速。当它后面那辆汽车要遮住我的视线时,我迅速地瞥了一眼牌照,同时从衬衫上抽出一支笔,在衬衫袖口上写下了车牌号,然后,我坐在那里瑟瑟发抖,直到我后面的司机按喇叭提醒我。
车队缓缓地行驶了两里路,我边走边找那辆旅行车。路边有一座灰色的砖楼,那就是警察局。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车开过警察局前面的小停车场。我跳下车,进了楼。
“有什么事吗?”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警察问我。
“我……我要报案。”我傻兮兮地说。
“哦?”他站起来,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来一份表格:“先生,你撞人了?”
“不,不是我。你知道,是我旁边车子里的一只手,那是一辆旅行车,还有……”
“先生,你先冷静一下,你是不是喝酒了?”
“没有。”我说。
“那是不是街上有人受伤,需要帮忙?”
“不,不是,你知道,是一只手……”
“好吧,咱们先从你的名字说起怎么样?”
“我叫詹姆士。”
“詹姆士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请坐下来从头开始说吧。”他示意我坐到桌边的一把椅子上。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我说完以后,那警察用手摸摸下巴说:“唔,你提供的证据没有什么说服力,你确信你看见的是一只手吗?我是说,那辆车后面的车窗可能有点脏……”
“我确定那是一只手,没错!”我大叫道,“手上还有血!”
“别激动。”他说。
他在浪费时间,我告诉他,他应该立刻去追那辆旅行车。
“詹姆士先生,看看外面。”他指着窗外拥挤的大街说,“就算那辆车还在街上,我又能怎么做?我们的汽车不能飞,这点你是知道的。”
“设个路卡不行吗?”
“不行,设了路卡以后,十五分钟内我们就会使半个郊区塞满汽车。有了。”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然后开始低声在电话中交谈。
二十分钟后,办公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粗壮的人。“这位是汉克斯警官,他是市局的。”刚才那警察介绍说。
汉克斯警官倒坐在一把椅子上,说:“我已经一连值了十六个小时的班,疲惫的很,想早点儿回家休息。你最好简明扼要地说。”
“是关于一只手的事。”我尽量说得简单,“我在街上看见一辆旅行车,车的后座上有一只手。”
“一只手!”汉克斯警官温和地耸耸肩膀,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不是吗?说下去吧,告诉我那只鬼打架的手吧。”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故事。我期望汉克斯警官至少会有点儿紧张,但正好相反,他看上去显得非常不耐烦。
我让他看我写在袖口上的车牌号,他边打哈欠边抄下了号码。
最后,当我说完的时候,他说:“你真的期望我相信你讲的这个荒谬的故事?也许车窗玻璃反光,也许毯子下有像手那样的东西。再说,凶手也不会在车后座塞个毛毯裹着的尸体,挤在大道上的车队里走。宽宽心吧,詹姆士先生,我们俩都回家去,忘记这件事吧!”
“不!”我生气了,“告诉你,我明明看到一只手,你是警察,应该采取些行动吧!”
汉克斯警官挖苦地说:“好的,先生,我立刻办。但是,我不着急,我得先睡一觉。你先回家去,假如我发现什么,我会和你联络的。不过,假如我找到那辆汽车,人家根本没有那回事的话。我可要……我可要……”
我离开警察局,开车驶上大街。在下一个路口的拐角我朝相反方向发动了引擎,回了家。我给老板打电话,请了一天假。这之后的三个小时里,我寸步不离地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汉克斯警官的消息。
下午两点十五分,有人敲门,我开了门,看见汉克斯警官站在门前,他和气地说:“詹姆士先生,我查过那个车牌号了,跟你说的一样,那是一辆茶色的旅行车,车主是约翰逊太太,她住在奥顿镇。”
“奥顿镇距这里只有两里远。”我说。
“我也找到了你所谓的‘尸体’,詹姆士先生。”
“你逮捕她了吗?”
“逮捕?人家并没有犯罪,我怎么逮捕?詹姆士先生,你得和我坐车去约翰逊太太家一看究竟。”
“我不懂,为什么我要和你去,假如……”
“你一定得去,假如你不去的话,我也要抓着你的脖子,把你塞进车里。我要你去看看,我追了五个小时追到的是什么。然后,我再想想看要以什么理由拘留你。”
在去往奥顿镇的路上,我无聊地数着途中的电线杆,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好做。汉克斯警官只是眯着眼看着前方,看都不看我一眼,沉重地喘着粗气。
到了奥顿镇,汉克斯警官把车开进镇中心,停在一条街道旁,用食指指着前边的一道门说:“你所谓的‘凶手’就住在那里。”
这栋小楼的门上镶着不透明玻璃,玻璃上还漆着两个字:装潢。
汉克斯警官敲了敲门,门立刻就开了。
开门的是一位穿着沾有油漆罩衫的女人,我定睛看了看,正是那天早上看到的旅行车女司机。
“约翰逊太太,这位就是詹姆士先生。”汉克斯警官介绍道。
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微笑着转头跟警官说:“这位就是你告诉我的那个人吗?就是那个在街上看到我那辆旅行车的人?”
“正是他。”警官回答说,“你可否让他看看那……唔……那人体?”
“假如那样可以使他安心的话,我非常乐意。两位,这边请。”
她向后面挂有布帘的内室走去。我们跟在她身后,布帘后面的那个大房间是一个散乱的工作室,乍一看,有点儿像是中世纪的行刑室,或者电影里的杀人现场。赤裸裸的人体、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奇形怪状地抛置在地板四周和工作台上。在一个角落里,手臂和脚堆在一起,而另一张桌子上堆放着人头。
我小心地伸手去摸当中的一个人头,手指所及的地方干燥、坚硬,那是石膏人体模型。
约翰逊太太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汉克斯警官从兜儿里拿出香烟,点燃。我其实也想抽,想向他要一支,但是,我看到他的眼神,就不敢张口了。
约翰逊太太带着一只石膏制的时装人体模型走过来,那模型的脸上挂着傻笑。
“詹姆士先生,这是西蒙。”她说,“我相信你今天早上在我车上看到的人就是他。我和我先生的工作是给小裁缝店布置橱窗,我们向他们提供人体模型。西蒙是人体模型之一,两天前我们刚把它全身重新油漆过,今天早上我准备带它到一家店铺去。我们不能把没有穿衣服的模特放在车厢后面,否则的话,会有更多和你同一个念头的人。但是,我们家里没有多余的塑料套了,所以就用了条毯子裹住它。车子时开时停,毯子滑下来,就露出一只手。”
“可是,约翰逊太太,”我说,“假如你带着西蒙去别的店里,那为什么它现在仍然在你这儿?”
“哦,这很简单,为它刷油漆的时候,油漆流了下来,我们怎么能把刷坏了的模特摆进橱窗呢?这点还是在我把它搬进店铺的时候注意到的。瞧。”
她指指模型的右手,不错,有一道红油漆从手肘处开始沿手臂流下,流到右手的两个指缝中间。
“这就是你看到的‘血’。”
如果地上有洞,我宁愿钻进去,也不想再看到汉克斯警官的眼神。
“看到了吧?”他讥讽地对我说,“我们是现在走,还是先和屋角的那些石膏像跳一支舞?”
我还能说什么?一个时装人体模型使我劳驾了一位疲乏的警探,还错误地指控了一个无辜的人,我感到汉克斯警官简直恨死我了。
回到我的家,汉克斯警官骂了我足足十分钟,那些词儿他都没有在约翰逊太太面前用过。
警官走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一口干下,然后倒在沙发里,用警官骂我的话又把自己骂了一遍。
也许是威士忌喝得太急,也许是一整天绷紧的身体终于松驰下来,我倒下来不一会儿就睡得跟死人一样。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渐渐醒来,我不是那种可以一骨碌爬起来跳下床就干活的人,我需要慢慢清醒。
我望向窗外,天已经黑了。我想到汉克斯警官的脸,便紧紧闭上眼睛,试图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
然而我的脑袋却不听我的,它把画面切换到早上那条大街上。我又从旅行车的车窗里看到了一只手,但它不是手,只是一块石膏,那是约翰逊太太的人体模型的一部分,只是……
突然,我清醒过来,原来汉克斯警官和我都错了,约翰逊太太欺骗了我们。
大街上的那幕景象又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不停地幻想人体模型在毯子下面的模样,而不是真人。
红色油漆是在西蒙的右手上,可我看到的那只从毯子下面伸出来的手是左手!
我坐在沙发里,双手因为紧张而颤抖着,我该给汉克斯警官打电话吗?即便我给他打过去,他也不会相信我,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半小时以后,我仍然拿不定主意。
这时,有人敲门。我忐忑不安地走到门边,把门打开。
是约翰逊太太!
她仍然穿着早上那件难看而古怪的大衣,但是,她手上拿的东西可不古怪。
那是一把点四五的手枪,它正瞄准我的腹部。
我的头一句话并不聪明,但我这一天正是不聪明的一天。
“是……另外一只手,对不对,约翰逊太太?” 我说。
“我还在想你要多久才会领悟过来。”她说着走进起居室,牢牢地关上身后的门,“汉克斯警官第一次到店里来,告诉我你所看到的景象,我便急急忙忙找了个模型搪塞他,由于太过匆忙,我想不出从毯子下面溜出来的是哪一只手,我以为是右手,结果我猜错了,但一小时前我反应过来了。”
“你知道我可能想到同样的事情。”
“是呀,这只是时间问题。”她说,“我从电话簿上找到你的住址。现在我们一道坐车出去,詹姆士先生,我先带你见见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开推土机的工人,不过,只要价钱合适,他什么都愿意做。那之后,你就可以去见约翰逊了。”
“约翰逊?就是毯子下面的那个人?”
“是的,约翰逊——我的丈夫,他卑鄙、虚伪、自私……”她的嘴角露出一个邪恶的微笑,“可是他现在去了。”
“去了?去了哪里?”
“明天的这个时候,约翰逊的墓碑将会是一幢崭新的豪华公寓,”她回答,“他们下个星期就要打地基了。”
我的手心沁满了汗,我害怕、我惶恐,可如果需要我跪在一个女人面前请求饶恕,我是宁死也不肯的。
“现在我也要去那里,对吗?”我企图稳住自己颤抖的声音,“可是,你不怕汉克斯警官对我的失踪产生怀疑吗?”
“他愿意怎样怀疑就怎样怀疑吧。”她回答说,“他不会有任何证据。我们该走了吧,詹姆士先生?”
突然,前门传来一阵很响的敲门声,好像外面的人急着要进来。
约翰逊太太惊慌地看看四周,我想抢下她的手枪,但是距离太远了。
她不安地左右回顾,然后把枪放回大衣口袋,但手却一直攥着。
“不管是谁,”她声音中带有恐吓的意味,“你都休想动歪脑筋,否则,我会立刻把你们俩一起打死。”
我把门开了条缝。不论是谁在外面,我都需要得到他的帮助。
门打开来,居然是汉克斯警官。他冲进屋里,猛烈地用手推我,我踉跄着往后退,碰在对面墙上。
约翰逊太太站在门边,表情惊讶,枪仍然藏在她的大衣口袋里。
“你这个下流东西!”汉克斯警官冲我咆哮着,“你这个混蛋,你知不知道我回局里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提供了假线索,组长严厉地斥责我没有判断能力,这将会大大影响我的晋升,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他说着,又把我推向另一道墙,我四肢着地倒在厨房的门边。
“你诬陷无辜的人。”警官继续骂道,转过头去看约翰逊太太,她看来和我一样的迷惑。
我现在哪有时间担心汉克斯警官的难题,我有我自己更大的麻烦。
“我很高兴你也在这里,约翰逊太太。”他大声说,“我正想和你联络,你可以起诉这个家伙,要求他赔偿你的声誉受损费用。”
他说着踢了我的后背一脚,同时把我往后一推,我摇摇晃晃地穿过门,头撞在橱柜角上,最后倒在冰箱附近。
我愤怒地盯着汉克斯警官。生气是一回事,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他从枪套里掏出手枪,两个人都用枪对着我,看来今天我是必死无疑了。
但是汉克斯警官却迅速地从起居室闪过来,并示意我趴下,同时喊道:“丢下枪,约翰逊太太!现在他安全了,你没有脱逃的机会了!”
一声巨响淹没了警官的话音,约翰逊太太开枪了,子弹打在厨房墙上,石灰掉落下来。
她连续不停地扣动扳机,汉克斯警官逮准时机站起来,用另一只手臂托着枪,小心地瞄准。他发了一枪。
起居室里顿时传来一阵尖锐、丑恶的叫声,汉克斯警官迅速跑到门边,我跟在后面,步子慢了些,但仍看到警官迅速地捡起约翰逊太太身边的枪。
她躺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大衣前襟有一滩血迹。
“你最好打电话叫救护车,她可能还活着。”汉克斯警官说。
约翰逊太太被送到医院,医生确认说她的状态可以出庭接受审判。
“抱歉我进来的时候那样粗暴地对你,”当事情平静下来后,警官说,“当我看见约翰逊太太的旅行车停在你家门外的时候,我便向窗子里头瞧了瞧,我看见她正用枪指着你,我只好用那种方法把你弄出房间。”
“没有道歉的必要。”我说,“是你救了我,警官。可是你怎么会回到我这儿呢?我以为下班后,你就不管这个案子了。”
“那都是因为我太太的关系。”他回答。
“你太太?”
“是的。我回家以后,被你气得无法睡觉,就坐下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太太。她很不以为然,当了太久的警官太太,很多事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她看看我,很生气地说:‘你大衣袖子上沾了什么东西?我昨天才刚给你洗完!’像一般女人一样,她不管我是多么疲倦,只是不高兴看到我衣服上有污渍。”
“我不明白。”
“那时候我也没有明白。我看看袖子,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什么?”
“红油漆。我就回想,我唯一能沾到红油漆的地方,就是约翰逊太太店里的那个人体模型。假如是的话,她那个模型就不会像她所说的,是两天前油漆的。那一定是在我去查看的几分钟前新上的油漆。我在前门等候的时候,她曾进过工作室一次,还很小心的不让我碰那个人体模型的手臂。或许是再我离开的时候,袖子碰到了它。如果油漆真的是从西蒙手臂上沾来的话,那么,那模型是就是她伪造的——那意味着她说的都是谎话。想到这些,我赶紧跳上汽车,去她店里一探究竟,可她不在。因为你家离得不远,我就决定来这里,再和你谈谈。到了这儿,我就看见她的旅行车在外面,接下来的你都知道了。”
汉克斯警官深深地坐进一把椅子里,好像谈话使他耗尽了所有力气,但是还有一件事我想问。
“尸体呢?她丈夫的尸体?”我问,“她说他在正要造的一幢公寓下面。你怎么去找埋尸体的地方?”
“建筑调查员……明天……我会给建筑调查员打电话……”
“对了,他有各项建筑的记录。”我钦佩地看着汉克斯警官,“我就没想到这一点。”
“所以嘛,”他声音低沉地说,“我是警探,我的工作就是来办事的,而你,你不过是……一个……一个……”
天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不把最后一个字说完就倒在椅子上呼呼大睡。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