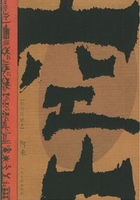战争中的故事
“列克星敦号”的沉没
珊瑚海的水是热的。“列克星敦号”的自动水温表上是摄氏三十二度,比血液的温度只低几度。而且,这里可以称得上鲨鱼横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凶恶鲨鱼在礁石间游弋,尾随着穿越珊瑚海的船只。
“列克星敦号”的了望哨警惕的眼睛日夜不停地搜索着附近的海面,每一片翻滚的白浪都可以怀疑是潜艇潜望镜的航迹。在最后决战前的几天里,他们看到了几千条鲨鱼,所以,谁都担心,要是真有一天要弃舰,那些鲨鱼将是一大祸害。
“如果我们在这个海里游泳,非叫鲨鱼吃掉不可。”舱面人员闲着没事聚在飞行甲板上聊天(海军叫“吹牛皮”)的时候总是这么肯定地说。
但是,当这个时候真的来到的时候,当“列克星敦号”弃舰的时候,几千人却没见到一条鲨鱼。不论是在飞行甲板上还是救护舰只的了望哨敏锐的眼睛连一个鱼鳍或露出的闪动的鱼尾,都没见到。
这有几种解释。有些人认为,这纯粹是命运,一个女人的命运,就像经常这样叫“列克星敦号”一样。然而,更多的分析是把完全没出现鲨鱼归结为它们被巨大船体内连续不断的剧烈爆炸吓跑了。在最后几分钟里,四万六千吨的船体几次被炸得东摇西晃,爆炸力在水中传得很远。冲击波在液体中传导距离很远,水下的剧烈爆炸能炸死方圆几百米的鱼类。空气是可压缩的,因此爆炸力很快就消失了,而水是不可压缩的,能将爆炸的冲击波传得很远。所以,我们把“海底深处的居民”不露面归结为这一原因。
当炸弹在军舰中部爆炸后谢尔曼舰长和副舰长从麻制的绳子上震下来时,他俩都摔到清澈温暖的海水里了。俩人吐了一气海水,就游向搜索水里最后几个人的那艘摩托艇。他俩被粗鲁地拽上了摩托艇,舰长还戴着那顶镶金边的一号帽子。
几周后,他已经从圣迭哥被调到华盛顿,晋为海军少将。回忆起这一情景时,他说:
“小伙子们揪着我的一只胳膊和臀部的裤子把我提起来,从船梆把我脸冲下扔到摩托艇上。”
“要把一个人从海里拽上来,这是唯一的办法。”
“不错,是这样。”他笑着慢吞吞地说。“但是,我看把一位舰长弄到艇上,他们应该用更体面的办法。”
现在是18点30分。热带的夜晚来得很早,天几乎黑了。夕阳落入大海,救护工作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这条摩托艇上坐满了精疲力尽的游泳的人,有的人吃了冰激凌又灌了一肚子海水,病的很厉害。摩托艇上的人都上舰了。除了我和乔治·马卡姆海军少尉外,其他人都爬上了巡洋舰甲板上放下来的登舰网。这时,又发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是“列克星敦号”最厉害的一次爆炸,鱼雷雷头里总共大约八到十吨的强棉炸药终于爆炸了。
“全体隐蔽。”传来了舱面军官的喊声。
乔治和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可怜的老“列克星敦号”,看到碎片、飞机、钢板、木板、大大小小的破片夹杂在白色的浓烟烈火中,冲上天空。我们紧紧躲在那艘巡洋舰的钢板后面,碎片溅落在周围几百米的海面上。
这个时候,未被摧毁的老“列克星敦号”也没有沉没,但火势更大了。飞行甲板现在从头至尾完全被撕开了。显然,这最后一次爆炸把燃油舱和汽油舱都炸开了大口子,烈火冲上一、二百米高空,最顶上是一团浓烈的黑烟。
在茫茫暮色中这个情景真是蔚为壮观,但也深深地刺痛了所有看到这个情景的人们的心。
上舰之后,我到了巡洋舰的洗衣房把全身上下弄干了。在那儿我遇到了一位友好的陆战队员。他负责洗衣房的工作,在他的建议下,借给我一套衬衣和裤子,我那烧坏了的破衣服放在那儿洗净烤干了。那双心爱的皮鞋是我采访不列颠战役时从伦敦买的,也放进了烘干箱里,不到一个小时就取回了,浸泡后一点没坏。
在我等着换干衣服的时候,从衣兜里掏出了几扎散页的笔记和一个黑色小笔记本,放到洗衣房的烘干箱里烘干后,每一页都保存下来了,并且高兴的看到我那龙飞风舞的字迹尽管弄脏了,但还能认出来。这是我救出的唯一的东西。我的手表、钱、衣物、打字机和那筒贵重的牙膏(六个星期后,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区还想买一筒,因为我没带旧牙膏皮,没卖给我)和我喜爱的名牌刮脸刀都毁掉了。
我来到甲板上。夜幕降临了,可能是个繁星密布的夜晚,但我们无法辨认,“列克星敦号”的冲天大火把天空的微光全都掩住了。在耀眼的火光中这艘大舰的每一处轮廓和残骸都看得一清二楚,相比之下周围的热带夜空象天鹅绒一样更加深不可测。两艘驱逐舰围着燃烧的船体绕来绕去,保障水里不丢下一个人。
19点15分,“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弗莱彻海军少将发来信号,命令舰队重新集结,然后转移。我们在这里停留起码有三个小时了,在敌人潜艇出没的这片海域里,这样做是自找麻烦。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了,但是军舰缓缓地移动着,好象不愿离开它们勇敢的伙伴“列克星敦号”。
我们没有把“列克星敦号”扔下不管,留下了一艘驱逐舰,绕着内部熊熊燃烧而现在变成樱桃红色的船体行驶。显然,它在沉没之前还能烧几个小时。在黑夜中它多么像一个信号标志啊!日本潜艇或侦察机在一百海里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都能看到,毫不费力地就能在海图或航空地图上把我们的位置准确标出来。
所以,弗莱彻将军下令击沉它。
单独留下的那艘驱逐舰(“菲尔普斯号”驱逐舰)执行了这个任务。舰员们在一千五百米之外,朝“列克星敦号”右舷发射了四条鱼雷。爆炸声几乎全被冲燎云宵的烈火的声音湮没了。鱼雷的爆炸没有使“列克星敦号”迅及沉没。
它几乎是四平八稳地慢慢沉了好几个钟头。鱼雷穿透了最后一层防护钢板,使它摇晃起来。
巨大的火舌夹杂着烟汽腾向上空,白热化的钢板遇水弯曲变形,发出尖利的嘶嘶声。舰内又发生了一阵阵新的爆炸,隆隆响成一团,这一定是巨大的压力把舱壁冲垮和汽油蒸汽爆炸了。现在,“列克星敦号”的下沉速度开始加快了。
但是,它还保持着平稳状态,不论舰首或舰尾都没有往下扎。海浪逐渐将它淹没了。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军官看着这最后一幕,自言自语地说:“它沉了,它没有翻。它是昂着头下去的。亲爱的老‘列克星敦号’,一位坚持到底的女人!”
这样,我们才下去吃饭,人总是要吃饭的。我一走进军官会议室,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声和友好的取笑声。我停了一下,左右望了望,我的天呀,周围全是我在“列克星敦号”上那几个星期一同进餐的熟悉的面孔。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列克星敦号”,只不过这间屋子的样子不同罢了。我意识到“列克星敦号”还活着,活在操纵它的那些舰员的心里。他们将把事业继续下去。
整个军官会议室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友好的,晒得黑黑的和没有刮过胡子的面孔。他们被请到丰盛的餐桌旁,每个人都吃饱了,作为巡洋舰官兵们的客人,都很轻松。
这艘巡洋舰的舰员很好客,他们物资并不充裕,但是倾囊相助。
全舰上下每一个人都打开了衣橱和行李袋,献出了军服、内衣、汗衫、蓝布工作服、鞋和最好的是床铺。成箱成盒的香烟和雪茄在我们中间传递。可口可乐和冰激凌也硬塞给我们,对于长期出海,与陆地隔绝的舰员来说,这些小东西就算不少了。在这艘舰上,我们的钱根本没人要。
晚饭后我同该舰的军需主任闲谈时,他问我有没有地方睡觉。他比我想的周到,因为我还没考虑这事呢。他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我说:“好吧,你在我的住舱睡吧。我一两天不能上床睡了,我得去安排舰上的事情。”
他把床铺指给我,然后拿出一本《舰艇条令》,查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些“权利”。在“军舰遇难者”一节里找到了一段,其中讲到要给我们这八百人中的每一个人提供衣服、卧具、毛巾、牙刷、牙膏、肥皂和刮脸刀。他马上命令军需人员忙着去把所有用得上的贮藏室全都打开。
按照名单对巡洋舰的每个舰员一一作了安排,就是说,他们要接待“列克星敦号”的同僚。比如,巡洋舰的舰长把谢尔曼海军上校接进了自己的住舱,巡洋舰副舰长接待塞利格曼海军中校,巡洋舰机电长把住舱让给了海因·容克斯海军中校,依此类推,所有的人都这样作了安排。“列克星敦号”的炮手使巡洋舰上的炮手增加了一倍。巡洋舰的机舱人员住进了机舱,把住舱腾给“列克星敦号”的机舱人员,锅炉舱人员也是如此。我们的陆战队员跟巡洋舰上的陆战队在一起,而信号兵则和他们的在一起。连菲奇海军少将和他的参谋在巡洋舰上也有地方住。巡洋舰上也有将军舱,但舰上没有将军,现在我们的将军和参谋住上了。
飞行员的情况稍有不同。巡洋舰有八名飞行员,而我们各飞行中队上来了几十人。巡洋舰飞行员们还是尽量往自己住舱里安排,剩下的人哪里有地方就安排到哪里,也就是说,走廊和过道里也撂上了小床,有的地方就把床垫放到甲板上。
巡洋舰舰员有一项安排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们都是一人一张床,现在自愿俩人占一张床铺,腾出一个铺位让给“列克星敦号”的舰员。他们轮流休息,一个人休息,另一个人值更。
我走到士兵餐室甲板,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两个士兵朋友。有几十人坐在那里聊天,满意地吸着香烟。我问大伙:“你们在舰上感觉如何?都有床位吗?”
“还有什么说的,很好。他们这么盛情款待,几乎把全舰都让给我们了。”
那天晚上,巡洋舰的乐队凑到一块为我们的吉特巴舞蹈家、低音爵士乐爱好者和即兴爵士乐专家演奏了充满生气的乐曲。
负责编辑这艘巡洋舰的小报的那个海军上尉说,要是我们肯为他提供素材,他想出一期有关“列克星敦号”的专刊,我们开了个会,指定几个“列克星敦号”上的人撰写这艘航空母舰的报道。最后,出了一期八页的专刊。
第一页上是一个来自康科德的民兵的画像,这是“列克星敦号”的桂冠,因为它称为“民兵舰”。这个人物形象站在“列克星敦号”的图案上。下面是一句古老的名言:“大海之光永照君。”
第二页登了韦尔登·汉密尔顿海军少校的一首短诗:
我们看到了她光荣的一生,
使每个目睹她壮烈殉国的人,
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
想起她就浑身力量倍增。
(选自《“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
作者:斯坦利·约翰斯顿[美国])
奥尔特海军中校最后的话
在列克星敦号的水手们同飞行甲板底下深处的可怕景象进行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斗时,约克城号也中弹了,密码室已被一颗炸弹炸得粉碎,雷达失去了效用,俯冲轰炸机攻击队队长奥尔特海军中校和他的报务员在攻击翔鹤号后返航时飞机受损,并发现自己处于飞行员的最危险的境地—在苍茫大海的上空迷失了方向,而油位指针在零度上面晃动。奥尔特可以用无线电呼叫到约克城号--
约克城号:最近的陆地在两百英里开外。
奥尔特:我们永远到不了那里。
约克城号:靠你自己了。祝你顺利。
奥尔特:请向列克星敦号转达。我们把一颗一千磅的炸弹丢到一艘军舰上了。我们两人都报告了两、三次。敌人战斗机飞来了。我改向北飞行。请告诉我你们是否收听到我的话。
约克城号:收听到了。靠你自己了。我将转达你的话。祝你顺利。
奥尔特:好,再见。我们的一颗一千磅的炸弹击中了一艘军舰!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听到比尔·奥尔特中校的声音。
名人论战
珊瑚海战役结束后,尼米兹称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深远意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