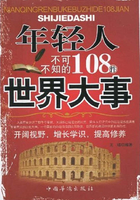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2003年2月16日,93岁的张兆和躺在病床上,有人拿着那个为她写过“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这样美丽的文字,与她共度了55年生命的男人的照片给她看。
“你认识他吗?”
她说:“好像见过。”然后她又说:“我肯定认识。”
但那时,她已说不出他的名字。
就在那个春天,她阖然长逝。
1906年2月,留日学生姚洪业、孙镜清回到中国。他们四处奔走,募集经费,筹办了“中国公学”。
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曾任董事。
1929年9月,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沈从文由徐志摩介绍,受聘到中国公学,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
像沈从文这样一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只有一张小学文凭,从军队退伍之后,只身闯荡上海,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会被聘为大学的讲师,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胡适,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他看中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沈从文的才华。
1929年9月,是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但写好了教案,还提前置备了新衣裳。为了不迟到,他还特意花了8块钱包了一辆黄包车去学校,而此次讲课的报酬,只有6块钱!
由于当时的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当天慕名来听课的学生早已挤满了教室。
一走进教室,看着下面坐得满满当当的人,沈从文吓了一跳,本来准备好的开场白,突然卡壳了。2分钟过去了,他没能开口;5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此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在讲台前面,有
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女生,名叫张兆和,见沈从文如此狼狈,她也不敢抬头看他。漫长的10分钟静静地过去了,沈从文终于抬起头来说道: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要哭了。学生们笑了,张兆和也笑了,他们用善意和宽容的笑声,打消了他的惊惶。
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英语系读书,沈从文在国文系教学,因为沈从文的名声很大,张兆和经常来旁听。
张兆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张冀牖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挚友,并在当地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当时的苏州城,流传着“苏州城四朵奇葩”之说,说的就是张家的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这四位多才多艺的名门闺秀。
张兆和当年18岁,皮肤有点黑,活泼俏丽,被仰慕和追求她的男生称为“黑牡丹”。兆和顽皮地把一封封求爱信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
张家四姐妹,前左起:允和、元和;后左起:充和、兆和。
留存起来,一个都不理睬。
但是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却愣住了。
这封信,竟然是她的老师沈从文写的。
为了向张兆和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不善言辞的沈从文拿起了笔。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情书这种古老的传情方式,在校园内盛行。从1929年12月开始,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几百封情书。
几乎每天都要写好几封信:
“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服侍我,却愿意自己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你不会像帝皇,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呐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
“我不仅爱你的灵魂,也爱你的肉体。”
情书写好以后,沈从文让一个好友代为传递。这位好友出于好奇,每次在送达情书之前,都要先拜读一下。“这个情书才叫真正的情书,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情书。”这位好友由衷地说。
每天收到几封情书的张兆和也十分焦急,一方面,她是倾慕沈从文的,不然,她不会作为一个英语系的学生,经常到中文系去听沈从文的课,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学生啊,老师对学生的这种追求该怎么接受呢?更何况,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还那么大。
在沈从文执著的追求下,张兆和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到校长胡适,于是有一天,她拿着情书去了胡适的家。张兆和说:你看!他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给我算什么样子?她想不到的是,原以为校长会为自己主持正义,谁知道他根本不站在自己这边。胡适竟然这么回答他:沈从文没有结婚,他向你追求那是正当的事情,你同意不同意当然你有你的自由。
这个话,张兆和听了已经是出乎她意料之外,没想到胡适还接着说:你的父亲跟我是同乡,我也认得他,你要不要我去跟你的父亲讲一讲?张兆和气得不得了,拿了信就走。
但其实呢,她心里,已经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了。与胡适会面之后的几天里,张兆和又收到了沈从文的情书。这一封信,竟长达6页。
正是这封长信,深深地影响了张兆和,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
1932年7月,张兆和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沈从文决定亲自来苏州看望张兆和,并向张家提亲。盛夏的中午,没有一丝风,阳光晃眼,街上极少行人。沈从文在烈日下匆匆赶路,他来到苏州九如巷的张家大院门前,敲开了张家的大门。门房拉开门,看着这位陌生的人。他说,他想见张家的三小姐。看门人说:“三小姐不在家。”
听到张兆和不在,站在阳光下的沈从文有些失望。这时,张家二小姐允和从门口路过,她一眼就认出来,这位年轻人是当时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沈从文。张家二小姐上前说:沈先生,请进屋来坐,三妹到图书馆看书去了。沈从文不知所措,过了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我走吧。然后,他留下了自己的旅馆地址,转身走了。
沈从文回到旅馆,正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到了两声轻轻的叩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正是他苦苦等待的张兆和。
沈从文在苏州停留了一周,每天一早就来到张家,直到深夜才离开。在这期间,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长达3年的情书追求有了一个美满的结果。但是生性腼腆的沈从文却没有当面向张兆和的父亲提亲。7天后,沈从文返回青岛,才写信给二姐张允和,让她去征询父亲对这桩婚事的意见。张兆和的父亲思想开明,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不会强加干涉。在得到父亲的明确意见后,张允和来到邮局,给沈从文发了一份电报。那封电报的内容,就一个字:“允”。允,就是张允和的允,一个意思是表示父亲允许了,另外一个意思呢,是她的名字。一个字的电报发出去了,张允和却觉得不放心,她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就给沈从文发去了另一份电报:“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他们没有正规的仪式,新房也十分简陋寒酸。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创作了著名的《边城》,小说里“黑而俏丽”的翠翠,就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
有一年,沈从文回湘西探望生病的母亲,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给他回了信,这些信里,他叫她“三三”,而她叫他“二哥”,后来汇集出版了,书名叫《湘行书简》。
在《湘行书简》里,他们用简单的语言写着绵绵的思念:
张兆和:“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都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3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张兆和留在北京照顾孩子。
面对现实困窘的生活,再美的诗也会褪下颜色。
分离的日子,他仍然和她通着信,这时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
由于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善于理财的人,没有什么积蓄,分居两地,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于是,她开始在信里说沈从文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沈从文这时候开始对张兆和的感情,充满了疑虑与猜疑,因为张兆和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北京去和他团聚,但是她并没有。他由此怀疑张兆和不爱他。
沈从文似乎一直很自卑,而张兆和,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好像一直都没有真正地理解过他。在沈从文声名大作时,张兆和经常看他的文章,不经他同意就动笔修改他的语法,一度让沈从文不敢让她看自己的文章。沈从文深爱着她,但是他一直感到沉重的压力,“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
沈从文患上了忧郁症,他去清华园疗养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张兆和没有去陪他,也没有去探望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