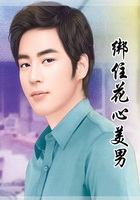“你神经病。”我狠狠把书包朝他扔过去,就想造成漫画里头直接把人拍死的效果,可惜这招在现实世界管不了多大事儿。以他和书包的比例,最后的结果也就是他能一把牢牢抓住这破玩意。
“你们俩真好玩儿,跟说相声似的。”
你才说相声呢,一点不好笑!我气鼓鼓的后来一直没说话。
“生气啦?你别理小昭,她就是随便说着玩的。”李景赫拉着我手,就跟没事儿似的。
我没理他,就顾着往前走。这张风喝冷的也不知道王旭要把我们带哪儿去。
“程筱,我想吃冰棍儿。”那混蛋突然松开手蹲在我面前,眨巴眨巴两只大眼睛瞧着我。
“大冬天的吃什么冰棍。王旭他们都快走没影了。”
“你别管他。我实在想吃。”
“想吃不会自己买啊?!”我可受不了这对大眼睛,一眨巴就眨巴了我十多年。
“我没带钱。”他伸手拽住我裤脚,扁了一扁嘴。
看他像往常一样耍活宝,我又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也不知道先前我柔弱的“小赫儿”怎么就长成了现在这副英挺的样子。
“筱筱,我想吃冰棍。我没带钱。”他蹲在地上使劲揪我裤腿。
“亏你还说得理直气壮。快点给我站起来!你这样像什么样子!还有,你别叫我筱筱,这算什么名啊?”其实说了也白说。
“我不!”瞧吧,“我这是很可爱的样子,你那是很可爱的名字。你不觉得特可爱吗?”这家伙居然还吐出了舌头,蹲在地上蹦蹦跳跳。丢人!你又不是吉娃娃。
我只想趁周围的人群还没形成大范围的侧目之前赶紧离开,掏出兜里的钱就给了那混蛋,他才总算是站直身子飞奔向马路对面去了。不一会又举着两根冰棍儿回来了。
“你瞧,我买了最好吃的小豆冰棍儿,那个阿姨可好了,还饶了我一根儿哪!你是不是特崇拜我!”他一边说着,一边麻利地撕开包装一棍塞进嘴里,一根塞进我手里。
“我崇拜你个姥姥!”
对于各类包装我都比较头疼,好像永远也掌握不了去掉那层薄薄隔膜的技巧,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成心,反正每次这种协助工作都是李景赫完成,其实要是他狠狠心就是不管我估计我也就能自己弄了,但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或许李景赫他像小时候一样没变过。
那我变了吗?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我们没有一天不在一起,我知道李景赫一天天长高超过了我,知道他眼泪一年比一年流得少,知道他打架一回比一回厉害,他是真正的变了。可我自己呢?我自己现在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儿了呢?
张嘴咬了一口冰棍儿,镇得我脑仁疼,倒霉的东西,怎么就非得吃冰棍啊?我张着两只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行,愣了愣瞅着小赫儿把冰棍从我手上拿走。
“你别老闹别扭了行吗?”
“怎么啦。”
“那什么……”李景赫咬了一口冰棍,也被冰得龇牙咧嘴,过半天才问出口,“刚才让王旭一闹我有一点懵。其实我真特想知道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啊?”我一下愣了,连声音都带着点发抖,我打赌心跳肯定上一百五了,不信你摸我脉,不过估计那会儿我也没脉了。
“喜欢吗?你说实话。”
“你不是问过了吗?”
“什么?到底喜不喜欢哪?”
“程筱,你说呀。想急死我是怎么着啊?”李景赫紧追不舍,非要痛打落水狗,“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你烦不烦?”我憋了半天终于张开嘴了,“李景赫,但凡我要是有一丁点不待见你,早抽你大嘴巴子了。你脑袋让门夹了?”
扔下这句话,我就觉得脸上发烫,也不管他怎么着,迈开大步“腾腾腾”就往前走,心想着他总得赶上,可过了老半天也听不见动静,他不是让车撞了吧?我慢慢回过头去想瞧瞧他,就这回头的一秒我已经在脑子里头塑造了无数种可能,惊心触目型的、天崩地裂型的、甚至还有琼瑶苦情系列的。可没等把头回过去就听见他扯着破锣嗓子高声地唱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
小昭姑娘和王旭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满目汗颜地瞅着我。
“你们干吗啊?不是我让他唱的啊。”
小昭姑娘倒是什么事儿没有,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们还说你俩哪儿去了呢。一听声儿就找着了。以后能让他当路标。瞧瞧,要带你们去的地儿可不就是这儿吗。”
我一抬头,这是什么地方啊?五星级大饭店?忒豪华了。上这种地儿干吗来啊,又不是多阔。
“请我们吃饭这有点忒隆重了吧?其实随便找个金钱豹什么的垫吧垫吧就成了。”李景赫有时候想得也太美了。
“不是那儿,得往里走。”
我们穿过这座大酒店,后面是一片高级住宅区。要说有钱人就是不一样,这是一栋栋的连体别墅,从上到下透着金光,连窗户上头镶着的玻璃都明显比我们家厚一层。停车场上一辆日本车都没有,宝马奔驰是最次的,还有不少是全球限量发行,明晃晃一片,差点儿让我们得雪盲症。北京城有钱人还真是不少。
“闹了半天就是参观富人区啊?咱们走吧,怪没劲的。”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李景赫从小时候就充分地显示出了对有钱人的仇恨。按现在的说法,这种人就叫“仇富”!我估计这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走什么呀,这是萧阳家。”
啊?你涮着我玩儿呢吧?
我一直以为我和有钱人的关系就是观众和演员的关系,那些人在电视电影里头勾心斗角,我就坐在沙发上磕着瓜子喝着茶水,乐颠儿乐颠儿地瞧着,时不时替他们捏一把汗。我以为有钱人就跟超级无敌海上小霸王杰克斯派洛船长只能在电影院里见得着一样。你别笑话我没见识,自一小我就住在大杂院里头,见着的人不是张大婶就是李大妈,一个两进趟的四合院住着十几家人,平均分分一人合不到五平米,谁想到我身边就能出现这么一有钱人呢?
这家里是真有钱啊,那房子大的,比我们原来住的大杂院还占地方,而且还是双层的,要算上阁楼那就是三层,光是客厅就有我们家整个屋子那么大,还用木地板搭了个日本式的玄关,这是玄关吗?有我们家客厅那么大。我们一帮人就站在这个超级夸张的大玄关,一个一个张着嘴,傻愣愣地就跟农村老伯进北京,走到了西直门就开始数楼一样的土老冒。
“你们家住了多少人啊?”我说这话确实有点傻,怪不得旁边的三人拿眼睛直瞪我,恨不得立马拿透明胶布把我从头到尾裹个严严实实,末了再挖个坑埋了。
幸亏这家里头住的是萧阳,我犯什么傻她也不笑话。就是微微一笑,不愠不火地慢条斯理开口。
“没什么人。”
“真够可以的。你们是不是一天换一屋啊?要不就是按着春夏秋冬排顺序?”
还说我呢,李景赫你问出这种话不是更傻。
“行了,你们别闹了。快点进来吧。”
那我们是不是得脱了鞋再换身新衣服才能进去啊?
我周围的这帮人可真是盖不吝,脱了鞋随便一扔就往屋里跑,就跟三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没什么区别。王旭还算好的,顶多就是挨个屋子溜达溜达。小昭姑娘和李景赫就有点太过分了,摸着那些精雕细刻的红木家具,坐在沙发上使劲儿地一颠一颠,嘴里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也幸好没有别人看着,不然准以为他们俩是还没从幼儿园毕业的小孩儿。我本来不想说,可实在太丢人了。
“你别担心,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是神仙吗?还是我表现得太明显了?
“多傻缺啊。也就是你还能忍得了。”
“我说,你问了李景赫了吗?”
“问了。”我红着脸连头也不敢抬。
“知道他喜欢的是谁了?”
“嗯。”
“你这傻瓜,别的人都看出来了,就你还看不出来。”
“那你都不告诉我!”我这就叫恼羞成怒。
萧阳宽容地笑笑,她真是挺不容易的,整天被我们这群还没发育的半大小孩儿围在中间,忙左忙右,整个就是一个幼儿园阿姨。一开始我看见的时候觉得她只不过就是一个娇滴滴的普通小妞儿,得被别人捧着护着揣在兜里还得拿手捂着开口,一点凉风都不能让她招着。我们还觉得是我们保护了她,一直固执地以为是我们把她从苦难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我们把自己当成了把睡美人从长满荆棘的城堡中解救出来的骑士卫队!可谁知道我们才是被哄着的小孩儿,她瘦小的肩膀用我们想象不出来的坚毅扛起了摇摇欲坠的世界,包括我们给她带来的苦难,她独自一人站在冰冷的水里,忍受着刺骨的寒冷所带来的疼痛,拼尽全力保住了我们最最珍贵的一切!直到那个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我们那种自以为是的帮助伤害了她。
只是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
李景赫跟小昭姑娘满屋子绕着跑,情况跟小学生的追跑打闹差不多,这座豪华的大屋子一瞬间就变成了超级幼儿园。
王旭绕了这豪宅整整一圈,挨个屋子看,然后坐在中央的真皮沙发上慢慢抽烟。他已经好一阵没去学校了。
“其实他不去上学我能理解,我以前有一阵儿觉得学校是比阎王殿还可怕的地方,天天早晨必须得鼓足勇气才敢上学,可没准儿走在半路上就掉头上别的地方玩去了。有一天更严重,走到我们家大门口却说什么都没办法伸出手去开门,等我妈晚上下了班回来我还站在门口发呆呢。”
“超级优等生也有这时候啊?”
“嗯,那时候我上小学,长得又瘦又矮,还带着个镶着黑框的大眼镜,说话也不太清楚,有点大舌头。学校里的同学都叫我‘鸭子’。我的书老是丢,要不就是被画得一块儿一块儿的黑。其实我知道是他们干的,可是我跟谁都没说。”
“那你就这么忍着呀?要是我早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了。”
“不忍着又能怎么样呢?我也打不过他们。而且我爸要是知道我跟别人打架,肯定得把我再锁几天。其实有什么事儿忍一忍就都过去了。我爸说我得当最听话的小孩儿。”
“你就听他的?”
“我以前一直觉得必须都听他的。可是现在,我觉得也得听听自己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总不能老听别人的话活着不是。”
现在只要一回想起来她这句话,我心里老是针扎一样的疼,那个本来可以不受任何伤害的漂亮女孩儿,就在我们几个幼稚的骄傲中,从天堂上掉下来,折断了翅膀一股脑掉了下来,扎进垃圾场旁边的煤末子堆里头,弄得灰头土脸。可当时,我们还觉得洋洋得意。依着我妈的话,真他妈没人性!
现在再回过头来想想那个时候的我们,实在是幼稚得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