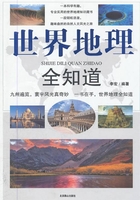每年北京城都会有这么一天,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城好像空了一般,从窗户看出去大街上一片空荡荡,坐公交车的时候不是终点站和起始站却有了座位,甚至多到不用给后上来的老弱病残孕乘客让座,街面上的商店关张了多一半,若是有风吹过,只看得见几张废纸在地上打着旋儿。
这时候就是要过年了。外地人都回家了。
每年这时候学校也就放假了,期末考试成绩没多少人在乎,真正在意的是我们的家长,整天念叨着快上高三了,可得好好努力,一落下就跟不上了。其实只要考得不是太差,大过年的也没什么人计较,我们这些人混在不好不差的正中间,就连王旭这不怎么上课的主儿,也考得不赖。一帮子人就这么的成了闲人,整天绕着满北京城转悠。就是萧阳出不来,她爸就盼着她好好学习,将来上个北大清华什么的,请了个家教天天在家给她补课,比上学还累得慌。听说每个假期都一样,怪不得她瘦成那样。
三十儿晚上北京城里头就见不着人了,天一擦黑儿,就全回家猫起来了,就算有几个人也都是在大街上偷着放炮的,这是北京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后的一年,1993年北京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的规定》。这个法规规定: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区。远离市区的农村及其他远郊区、县则暂不列为禁放区域,由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这规定实在让人窝火,据说是因为每年放爆竹炸伤炸死的人忒多,这是政府为了安全考虑。头几年我还觉得真安静呀,整天琢磨这是在过年吗?真安全呀,能在三十儿晚上放心大胆地走胡同串小巷了。禁就禁吧,放了十几年正好懒得放了。过了几年后心中又有种新的感觉:凭什么禁放烟花,这不是自找没劲吗?要是逢年过节都听不见点响动,那还叫什么过年啊?再说了,我们这帮小破孩儿打会走就拿着爆竹捻玩刺花,十几年了不也照样没事儿吗?还想着小时候年年过春节,大晚上一堆小孩儿攒在胡同口儿,盯着谁家放个炮仗,等响声刚一下去,就“呼拉”围上来,在剩下的炮仗堆里头扒拉,找着还没放过的就立马揣到兜里,干这种事儿王旭最猛,年年都不花一分钱可兜里揣着的炮仗比谁都多。
可那种情景好几年没见过了。今年也是一样,眼瞅着就三十儿晚上了,都没听见有一点儿动静。我们几个商量着,要再这么憋下去,非得找一天坐上车直奔郊区,甭管他昌平还是门头沟,溜溜放上一天炮仗。
现在中国的冬天就是每个人都在往回家的路上赶,北方的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身在异乡的人就起了相思病,甭管是赌气出走的还是被迫远走的,都开始惦记着家里的人好不好。再下几场雪,就该拎起来大包小包地坐火车乘飞机了。
也就只有一个人还没有回家。
“王旭,快过年了。”小昭姑娘拍着他肩膀挺豪气。
“怎么啦?”王旭这小子眼皮抬都没抬,就跟压根儿不关他事儿一样。
“你不回家?”
“前两天回去过了。老爷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房子都快空了。”
“没跟街坊打听打听?”
“没见着。也不知道是不是死外边儿了。”
一提起他家里的这些事儿,我们就全都手足无措。一个个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就是亲爱的小昭姑娘还能有点儿办法。
“咱们再去瞧瞧吧。”
“有病啊,干吗去啊?”
“总得知道他在哪,好歹也是你爸。”
“你是居委会大妈啊?怎没带着小红箍入了小脚侦缉队啊?”
“你就兹当我是行了吧。”
一群人浩浩荡荡,直奔王旭家而去。
刚到胡同口,他家东院的王大妈就远远儿的跑过来啦。您可加小心啊,就您那两只小尖脚再摔个马趴,真别说,小尖脚捣得还挺快,眼皮没眨的工夫就到了跟前啦。
“王家小子回来啦?哎,也真是苦了你了,要不赶明儿你吃饭什么的就都归我管吧。”
“没事儿,您别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这街里街坊地住着,帮一把还不都是应该的吗。”
“真不用,您甭操心了啊。我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那哪儿行啊,就你一个人了,怪可怜的。”
“真没事儿,还有我爸哪,他过两天就回来。”
“你这孩子,你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
“您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啊?”
“敢情你真是不知道啊?咳,这孩子!你爸进去啦。”
“啊?!”
嘴巴张得老大,本来灵活自如的手指仿佛抽筋一般,稳稳夹着的烟从指间掉落,跌落在地的尘埃,再往起弹了一弹,终于湮灭在飞扬的尘埃,吐尽了最后一口白色的烟雾。
“怎么进去的?”
“你瞧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天来了好几辆警车,“呜哇呜哇”的,下来一帮警察就把你爸带走了,找你也没找着。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反正听说是什么贩毒。”
贩毒?我们全都懵了,那时候毒品这东西我们也就是从电视上头瞧见过,何况政府的禁毒宣传攻势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强烈,贩毒?我还以为只有拍电视剧才能见得着呢。一时之间,大家伙全愣了,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旭沉默地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上下抖动,眼泪从手指缝间一滴一滴地渗出来,滴落到蓝色牛仔裤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一片片圆形水印。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王八蛋!”
“得了,怎么说也是你爸。”伶牙俐齿的小赫儿,能说出来的也不过就是这几句。
“他不是!我他妈恨他!他挣不了多少钱我无所谓,整天喝酒我无所谓,哪怕他打我、骂我我都无所谓。可是他怎么能这样?贩毒,真他妈混蛋!他不是我爸,我不认他!”
“王旭……”认识王旭这么些年,见过他仰天大笑、见过他喋喋不休、见过他沉默寡言、见过他暴跳如雷、就是从来没见过他掉眼泪。
因为李景赫的缘故,我从小就对“眼泪”这玩意儿缺少免疫力,看见别人掉眼泪就搂不住火儿,蹿起来就敢揍人一顿,可现在看着王旭掉眼泪,鼻子也就酸了,别说发火了,就连话都说不出来。李景赫温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终于忍不住悄悄掉了眼泪。跟王旭比起来,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太幸福,恨不得把自己周围这点热乎气儿都拿个塑料袋装起来,捆巴捆巴弄一堆儿,全灌到他嘴里去。
但又明摆着无能为力。
这是2002年的春天,全国人民都在忙着庆祝新一年的到来,可今天我们这位一直背着吉他追着梦想往前疯跑的王旭同学,独自一人坐在“嗷嗷”咆哮的西北风中间,红了眼眶落了泪。
最后王旭还是跟小昭姑娘和双胞胎兄弟回了新街口,李景赫把我送回家,一路上我俩蔫头耷脑的没说什么话。
“你俩今儿是怎么了?蔫巴出溜的。”一进屋就让我妈看出来不对劲儿。
“妈,王旭他爸进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听说就前几天的事儿,我们谁都不知道。”
“你们这帮混蛋。没一个有人性的!这大过年的他一人怎办啊?”
“嗯……”我鼻子一酸,眼圈又红了。小赫儿一直没出声,话说到这儿才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把他叫咱们家来。也不少这一双筷子。”
别瞧我爸平时不爱说话,可那要是真发了话,一句是一句的,谁也打不了驳回。
结果三十儿晚上,我们家就成了大饭店。
本来说的是叫王旭过来,谁知道趁着热闹呼啦啦来了一大堆人,极光的四个人,再加上李景赫他们一家子,给我妈乐得合不拢嘴儿,忙得自己脚不沾地儿也就罢了,嘴里还不带打磕巴儿地指使我。抓瓜子、倒茶水,真把我当小催巴使唤,我趁着她没注意,撂挑子不干了。悄悄跟李景赫发牢骚。
“不是说就叫王旭来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小赫儿也不着急,笑眯眯掰着手指头给我数,小昭姑娘是孤儿,不来就得在孤儿院过,“那她得多孤独啊,你舍得看见一个漂亮小姑娘掉眼泪吗?”石平石安爹是警察,正赶上今晚上值勤,妈在外国谈生意回不来,也跟孤儿差不多。不来这儿这帮人去哪儿啊?
他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别的啊?
“得,就算他们必须得来,可你干吗来了,还拖家带口的。”
“凑热闹啊,这么大热闹我还能不来凑凑,那这辈子可就亏了!”
“不好好在家过年,瞎往这儿凑什么热闹啊?”
“你爹妈跟我说这儿就是我家一样啊。你妈让我妈来帮忙的。帮了半天忙总不能一脚就踢开吧?程筱,你忒狠了,卸了磨杀驴!”
“难为你承认你是头驴。”
他瞪大了眼睛瞅着我,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当时就心里一惊,惨了,这回把他惹急了,我什么时候斗得过他啊,这么一来,我就请等着受死吧。
突然他的一只手就重重地拍了我肩膀。我吓得一闭眼,心想着完蛋了。虽说人活这一辈子横竖是个死,可就因为这么一句话死了,实在是有点太不值当了。
“你可以啊,还学会幽默了。真不容易。”
我真是小看了李景赫,这时候他都能笑出来,还明显挺开心的,笑得捂着肚子缩成一团,眼泪都出来了。我有那么好笑吗?
怪不得过年都要大家团聚,哪怕是千里迢迢也得赶回家,“落雪也不怕落雨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风雪落下,”一定要回家,只要见到家“如何大风雪也不怕”。我看着这一大屋子人,嘻嘻哈哈,吵吵闹闹,有人抱怨着谁沾了面的手摸到自己新洗的衣服上,却被别人笑话捏出来的饺子实在难看,这么乱七八糟的时候,心里头竟然涌上来一点儿感动。就像是被热乎气儿包裹起来的窗玻璃,泛上一层水汽。
北京过年有个传统,每年的三十儿晚上到了整十二点就能听见钟鼓楼的钟声,所有人都在这个时刻安静下来,大气不喘,就这么静静聆听着浑厚悠扬的铜钟声穿越大街小巷,满四九城地飞跑。今年也是一样,临近半夜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一股脑地跑到阳台上推开窗户,也不管外边西北风刮得脸生疼,一个个眼睛里闪着亮光,仔细地寻找从钟鼓楼上飘过来的钟声,在结束的同时发出“哦——”的一声大叫。
这时候大家都说不能忘了没法凑到一起的萧阳,紧接着一个电话就追过去了。她在那头开心地“呵呵”直乐,说是要让我们赔罪,就约好了第二天去逛庙会。
正月初一早晨起来,一个个眼睛都红得跟兔子似的。昨晚上折腾了一宿,打牌聊天的,我爸平时不到十点就躺下了,可那天晚上也愣是睁着眼睛熬到早晨。我妈说这才叫过年,不然怎么就有那么句老话说“三十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的呀。她倒真挺想得开。就因为王旭昨天红着眼眶说了句谢谢,她这一晚上嘴没合上过,忒美了。
按照昨天说好的,萧阳早就在我家门口儿等上了。我们这一群人吃过了饺子就慌手忙脚地往厂甸儿赶,每年最大的庙会就是这儿。其实厂甸就是宣武区南新华街路东边的一条小胡同。元朝时候政府在这设了烧琉璃瓦的一座窑,所以就有了个名儿叫琉璃厂厂甸。在北京,一般的庙会都是用庙宇的名称命名,厂甸这儿光庙就有三座,火神庙、吕祖祠和土地祠,这三座庙是明朝时候建造的,火神庙现在叫宣武区文化馆,吕祖祠在厂甸七号,土地祠已经拆了,现在应该是宣武实验幼儿园。这三座庙宇离得挺近,而且都在农历正月,佛事兴盛,上香的人和小商小贩摆的摊儿连在了一起,这么着就成了厂甸庙会。小昭姑娘高兴得不得了,非说长这么大这是头一回,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哪儿说得清啊,光记着小时候一家子一起逛庙会,骑在我爸的脖子上,用北京话说那叫“呵儿喽”着。肩膀上扛着一大串糖葫芦,这是厂甸最有名的了。全是用山里红,也就是山楂,穿成串儿,大的能有五六尺长。有讲究的拿黍米做的饴糖从上到下刷上一层,整个就变成了白色的,顶子上还插着各种颜色的小纸旗子,就叫厂甸一景儿。
听我一说,小昭姑娘激动得直蹦高儿,坐到公共汽车上头也安分不下来,一个劲儿地叫司机师傅快点儿开,我说大小姐,这不是出租车好吗?一年就这么一回能赶上座,还不能老实待会儿。
这帮人一个劲儿地埋怨我,怪我不该招她,可我哪儿知道她这样儿啊?简直就是一活猴儿。
等我们到了那儿才知道什么叫人多,抬头一看哪儿哪儿都是一片黑压压的人脑袋。哎呦,看得我头直晕。逛庙会的过程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就算是七个人手拉着手也还是不停地被冲散,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像是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可是大家还是兴致高昂,抖起来嗡嗡作响的单双空竹,迎风挥舞就嘎嘎击鼓的大小风车,抽在地上滴溜乱转的陀螺,以及五六尺长的大糖葫芦,再加上各种生肖玩意儿,每一件都吸引足了我们的注意,店铺和摊商前边摆着的书画珍玩、册页扇面、京味小吃、干鲜特产、空竹陀螺、风车风筝、针头线脑、杂物百货,我们每一家都停下来,每种小吃都尝一口,遇见实在好吃的,就几个人抢着吃。溅得浑身不是油星儿就是调料,那也没不高兴,照样乐呵呵地到处跑。小昭姑娘扛着几尺长的大个糖葫芦,一个劲儿地觉得自己跟这儿有莫名奇妙的缘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忧愁。”你别逗了,还是大家一块儿开开心心地玩儿吧。那一天整个厂甸的上空都能听见我们嘻嘻哈哈的吵闹声。
2002年的春节就这么浩浩荡荡地过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这么激动人心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