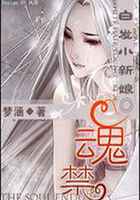不过,她还是想去看看他。若他真结了新欢,她自不阻了他的道。
她只当没活过这一回便是。毕竟,当年他确是真心了的。
“哎。”惊羽虽是宽慰了自己,却忍不住叹了口气。
到底是母女连心,小包子立刻察觉到了自家娘亲的不虞,又是个心思机巧的,立刻道:“娘亲莫恼,爹爹实是想极了娘亲。只是这次不知受了什么魔怔。”顿了顿,又把怒气集中到了柳水仙身上,银牙一咬,“都是柳叔叔的错,尽添乱!”
惊羽不禁被她小大人的口气一下子逗乐了,先前的愁绪倒是淡了一些。
“啊——”这时,却听一声尖叫划破长空,直有冲破云霄直上九天的架势,两旁树上的麻雀儿顿时鸟兽散般“呼啦”一下飞了。
惊羽只觉一阵耳鸣,皱眉,捂住小包子的耳朵,啐道:“闭嘴!”
战爱闲彷佛终于惊醒了般,白着脸抖着手指指着惊羽半天说不出话来。
小包子鄙夷得瞧他一眼,教训道:“战战,你的礼仪白学了,怎么可以用指头指着别人?”最后得出结论,“真粗鄙!”
惊羽额头上滴下汗珠一枚:唔,她这个女儿才五岁吧,她怎么愈发觉得像是二十五甚至更甚?
瞧她那鄙夷的小眼神,怒其不争的语气,不知道的还会以为是哪家母亲在教育儿子呢。
战爱闲也不管她,“嗖”得一下就蹿到惊羽跟前,双手抱着惊羽的胳膊就直摇晃,颤抖着声音道:“媳妇,你诈尸啦?太好了!这可是个赚钱的新门路啊!咱们合计合计,看参观费定在多少合适?可不能少咯,这千百年来,诈尸的鬼怪可是头一回见呢。小爷也不贪,这赚的银子咱们四六分如何?当然,我六你四。”
惊羽一个踉跄,险些跌了。望着战少年一脸的热切,她不禁黑线连连。就说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估计这位强人,居然他刚刚是一直在计算这事呢!那脸色苍白的,身体颤抖的,也是因了有新钱进账,兴奋的吧!
对比下战少年的疯癫,再看看自己成熟稳重的小女,惊羽圆满了:跟这位比起来,小包子是多么得正常呀。
。
有了北临小公主这块金字招牌,惊羽进皇城自是方便了许多,更是没有需要通传。车队也一并留在了外头。
惊羽叫随行众人去行馆等她。毕竟现在情形有变,她也只不过就是进去探探虚实罢了,没必要这般隆重。若是以南明公主身份去了,最后反倒尴尬。
南明众人虽是心内惊疑,自家公主居然在北临皇宫有熟人,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情。但这到底是主子的事,也不作妄言。
进到皇宫内苑,惊羽又是一阵感慨,上次来这地方的时候,独孤玄许下“江山聘”的承诺,她亦在那时,交付了她的一颗真心,此刻却是人事全非。
这般美好的誓约,那人现在是说与谁听?
来来往往的宫人俱是不阻拦几人,更是早早辟开了路,福身恭请几人,眼都不敢抬一下,倒是对小包子这个小公主极是尊重的。
惊羽欣慰得点点头,至少小包子在皇宫里受到的待遇是不差的。
但是,此时惊羽只猜到了结局,并没有猜到过程。当她知道为何自家女儿小小年纪便能掌控后宫时,心脏病差点被吓出来,这自是后话。
却说愈往里走,惊羽的脸色愈诡异。
终于,她忍不住发问:“最近妇人间流行白装么?”这来往过去好几拨的贵人了,俱是白衣的装束。是不是她没有经历的这五年,潮流发生了变化?她记得当年宫里贵人们总是爱花枝招展得攀比的。这一身的素白什么意思?后宫制服么?
“学你呗!”战少年撇撇嘴,显是极其不屑,“都说端敬皇后嗜白衣,这宫里头的人啊,哪个不是争破了头的想要往上爬的,自然处处要学你咯。”
对这些女人,战爱闲完全提不起兴趣。倒是眼睛直溜溜盯着惊羽瞧。对于这位死而复生的“媳妇”,他却是极为欢喜的。虽说鬼怪之说向来无稽,普通人见到归魂的惊羽,说不得就要纵火烧妖了。但战少年又岂是常人?自是一会儿便完全消化了这个事实。
倒是惊羽乍闻“端敬皇后”四字沉默了下。一路行来,她自是打听了自己不在的这五年间,独孤玄的事迹。自然知道,这端敬皇后便是指的自己。这“端敬”二字,便是独孤玄灭了东启跟西昭后,赐给巫家三女的字。
世人皆道北临这位主上人虽然暴戾了点,但到底痴情。自端敬皇后去后,这后位竟一直空悬……
正想着,惊羽几人恰巧经过演武场。惊羽不经心一瞥,表情顿时扭曲了。
她指着场中,艰难道:“独孤玄这是要组织个女子举重队么?”
只见偌大的场地上,各式着白衣的美人,成行列队,马步一扎,竭力想要提起各自面前的巨石,香汗淋漓,忙得不亦乐乎。
那一个个,纤细娇弱的、唇红齿白的,一瞧便是从小享尽荣华富贵的千金小姐,手里从来是拿书执笔,向来是附庸风雅的人物,何时做过这等粗重的活计。
于是,场中那一个个歪歪斜斜、颤颤抖抖的马步,怎么看怎么诡异。
惊羽机械得抽了抽嘴角:“独孤玄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怪癖?这是培养穆桂英挂帅呢还是耍杂技呢?”
战爱闲咂摸下嘴巴:“怪癖?你家相公就没正常过。”
惊羽转头,默默腹诽:就你这样的,还好意思说别人不正常。
“谁来给我解释下。”
战少年来了兴致,捻起兰花指,拉长了声调唱起了戏来:“此事说来话长,媳妇且听俺细细道来。”
惊羽面无表情得打断了他:“小包子,你告诉娘亲,好不好?”
战少年大受打击,蹲到阴暗处默默画圈圈内牛。
小包子摸摸他头顶,表示诚挚的安慰与真切的幸灾乐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