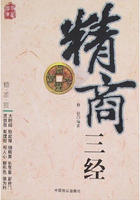那花田距绚彩山庄本是甚远,凌若心也来回走过许多次,却第一次觉得原来花田距绚彩山庄这么近,一个时辰的路程不知不觉便走完了。
只是还没靠近花田,便远远的闻到一股焦味,凌若心心里闪过一丝不良的预感,忙策马向花田奔去,一走近花田,不禁吓了一大跳,原本种植的好好的天心兰,此时已被人尽数烧死。整片田地一片焦黑,绚灿的花朵早已没了形状,碧绿的叶子有的焦黄有的已成了灰烬。
清菡一见这种情况,惊道:“这里就是花田?”
凌若心点了点头,她接着又问道:“可是怎么会这样?”
会这样的原因太简单了,那就是有人故意放火,凌若心咬了咬牙,手也握成了拳!如深潭般的眸子里杀机一片!咬牙切齿道:“秦风扬,你太卑鄙无耻了!”
清菡一见凌若心的模样,微微叹了口气,她也很生气,这种手段实在是太卑劣!只是看到凌若心那么生气,她却又觉得她生气也于事无补,于是在旁劝道:“花田已经被毁,现在生气一点用都没有了,绚彩山庄可还有在其它的地方种有天心兰?”
凌若心见她一脸沉静的样子,心里微微有些称奇,这小丫头每日里看起来暴燥无比,到关键的时候却又如此冷静,让他不由得又多了几分欣赏。他重重的叹了一口气道:“天心兰对生长的环境要求极高,只适合生长在雾气较重而湿润的地方,更需要极用心的打理,否则极难存活。而整个凤引国懂得养天心兰的人,也就只有绚彩山庄。绚彩山庄适合种养天心兰的地方,也只有这里。”
清菡听得他的话,不由得有些沮丧,举目望去,整片花田雾气蒙蒙。心里又不禁将秦风扬狠骂了一通,只是现在再怎么骂也骂不活天心兰。她想了想又问道:“如果没有人工种植的,在野外可有地方能生长?”所有的东西在被人种养之前,必定是野生的,如果找到野生的天心兰,也一样可以制成流光溢彩。
凌若心听得她的话,眼睛一亮,但转瞬又暗了下去。他悠悠的道:“我曾经听娘讲过凤引城外还有一个地方生长天心兰,只是那里危险无比。而且天心兰十年才开一次花,还不知道有没有开花的开心兰。”
清菡听见他的话,微微升起了些怒意,她骂道:“狗屁秦风扬,下次若再栽在我的手上,就不止脱光他的衣裳,还要把他的脸画花,再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凌若心听到清菡的话,不禁吓了一大跳,问道:“他曾栽倒在你的手上?你还脱光了他的衣裳?”心里微微又升起了怒气,她的胆子也太大了些吧!在她的心里还有没有男女之防啊?心里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却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她只怕是做的出来。他就曾被她看光光!
清菡忙掩了掩嘴,知道自己说漏嘴了,脸上微微有些窘,大大的眼睛眨了眨道:“其实也没有脱光他的衣裳,只是把他的衣裳划破了罢了。”也不是划破,是划得稀巴烂。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解释,却觉得这种事情还是不想他误会。
她不解释还好,越是解释凌若心越是冒火,他完全可以想像的出她嘴里的划破是什么意思,语气瞬间转冷道:“一个女孩子,却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整日里跟个疯丫头似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清菡最是讨厌他这样说她,当下跃上马背,恨恨的道:“是啊,当女人我是没办法和你比,可是你为什么不去跟那些男人比了,不要忘了,你自己原本是什么东西!”
凌若心的脸瞬间黑了,怒道:“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东西不东西?”她以前也说过他很多次他娘娘腔之类的话语,只是在今天听来,这样的话就显得格外的刺耳。
清菡冷哼一声,双腿一夹马肚,知道他今日心情不好,也懒得理他,骑着马扬长而去。凌若心看着她离去,叹了一口气,便也跟着追了上去,只是晨雾极大,等他策马追的时候,已不见清菡的踪影了。
清菡独自策马狂奔,在心里把凌若心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完了凌若心又骂秦风扬,这些男人真没一个是好东西。他居然嫌她丢人,她还没嫌跟在他的身边窝囊了,若不是因为担心爹的安全,她才不要答应帮他,而他不但不领情,还敢凶她,欺负她,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秦风扬的手段也真是狠厉,一大片的花田居然就被他烧成那副模样,那么漂亮的花,他也下得了手,真是辣手摧花!
骂着骂着才发现一个问题,她迷路了,早上来的时候她跟在他的身后,也没有仔细记路,此时雾气又重,根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她不由得看了看在雾中显得有些朦胧的太阳,浅浅的黄色就像一个大饼,对了就像大饼,不是她俗气,而是她的肚子饿了,一早上爬起来都没吃东西。她叹了一口气,反正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不如就往前走,找些吃的,等雾气散了,她再找人问回绚彩山庄的路。
谁知越往前走,道路越是崎岖,雾气倒是消散了不少,清菡见前面隐隐露出屋檐,心里一喜,不管怎样,先去弄点吃的再说。
那是一个很俱规模的别院,看起来整洁而素雅,她心里微微有些吃惊,这寻隐城里还到处都是财主,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还有人修这么好的别院。她在门外叫了几声,柴门打开时,却是一个素衣女子,那女子一身白衣,浑身纤尘不染,虽不是极美,但眉目间满是温柔,嘴角含着一抹若有若无的淡笑。那女子的模样让她不由得想起了凌若心,他也喜欢穿白色的衣裳,也喜欢笑。若是以前,她定然会好好的夸夸那个女子,只是自从认识凌若心之后,便知道这世间美的事物都是带刺的,越是美的人越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