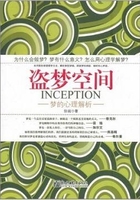范老桅把渔船开进大海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卷毛大浪时常把已经载重了的船打得横了过来,如果不及时调整船头,判断出下几次大浪的方向,渔船就会树叶一般,倾覆在大海里,范老桅只能在大浪的缝隙,寻找机会直入大海。范老桅驾着渔船,在岸边的浪峰上徘徊了好一阵,突然间离弦的箭一般,猛地窜进大海里,随后,就被黑暗包围了,只剩下那盏若隐若现的渔灯。
缆绳默默地牵扯着卷扬机,把范老桅的移动传导上来,让人们感受到范老桅的进程。缆绳每一次剧烈的颤抖,都像是拨在人们的心弦上,让人们的心颤颤地疼,让无节制的心脏狂乱地跳。人们看不到范老桅,可剧烈颤抖的缆绳分明地告诉大家,那是一场怎样的搏斗啊,风和浪揪人下地狱的恶鬼一样,纠缠不休地扯着范老桅。好在颤抖之后,缆绳又被牵引出去,对讲机里重新传回范老桅粗砺而又坚定的声音。大家松了一口气,范老桅又斗过了一阵恶浪。
又听不到范老桅的声音了,缆绳在呼啸的暴风雨中,发出鬼哭狼嚎的尖锐叫声,让人们的心冷飕飕地打颤。
没有高超的驾驶技巧,谁敢在大风大浪之中载重行驶,虽说载重了的船不会再让螺旋桨空转,也不会让尾舵悬出海面,可稍有不慎,海水就会灌进来,渔船就会面临着沉没,范老桅必须斜切着浪锋,迂回着往前航行。他不怕渔船穿峰入谷地上下颠簸,多高的浪都不会让他眼晕目眩脚底无根,他怕的是渔船的左右摇摆。范老桅小心翼翼地驾着船,他时而关闭时而大亮着渔灯,他是在给对面的渔船发出安慰的信号。渐渐地,范老桅接近了那盏微弱的灯光,接近了那艘遇难的渔船。
那艘无能为力漂泊的遇难渔船就飘浮在范老桅的眼前了,可两只船的相聚却格外的艰难,好不容易接触上了,却又被涌过来的大浪无情地打散,再次相聚再一次被打散,就这样分分合合了好多次。
暴雨之中,海里的能见度极差,又有巨浪不分轻重地胡乱拍打,范老桅每次接近对方的渔船就格外的小心,靠紧了怕把船撞沉,救人不成反倒害了人,靠慢了又被大浪轻易地分开了。范老桅在海上漂泊了大半生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艰难的两船相靠。
一个闪电从天空劈下一片苍白的光芒,范老桅看到,对面的渔船上,人们一个个像只小猴子,死死地抱着船上的某一部位,任凭大浪对渔船的摇晃。范老桅的渔船靠近时,他们即使是伸出搭勾去勾船弦,也都是用一只手软弱无力地去勾,另一只胳膊依然嵌在渔船上不可动摇地搂着。显而易见,没有范老桅的帮助,他们很难从那艘渔船上爬过来。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送给了舍身取义的范老桅,有那么一刻,两条渔船突然间被大浪冲成了平行在一起的位置。范老桅钻出了驾驶舱,双腿紧紧盘在船上,双手持着搭钩勾到了对方的船舷,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缆绳,活生生地把两条船靠成了一体。那条船上饱经风浪之苦的人们番然醒悟,拼着最后的力气,爬上了范老桅这艘还算安稳的船,就连身材魁梧的冯大岸,被人连拉带拽地弄上范老桅的船,也软成了一滩泥。范老桅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两条船之间巨大的分力了,当逃离苦海的渔民全部爬上他的渔船后,他终于松开了双手。那艘渔船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几经沉浮,斜歪着膀子趔趔趄趄地漂浮走了,埋没在滔天的大浪里。
准备回航的时候,范老桅犯难了。行船不怕顶头浪,追在船屁股后边的顺头大浪是最让行船的人吃不消的,何况他这还是一艘载重的船呢。抛出船舱里的石头,船的螺旋桨和船舵就会划空,救人的船反倒成了遇难的船。范老桅只能面对着大浪倒行逆施地退着走了,这么行船虽然能够看住巨浪对渔船无穷无尽的冲击,却无法去看身后的航向,避开身后的危险。好在范老桅已经向岸上发回了信号,牵扯着自己这艘船的缆绳开始被卷扬机往回搅了。
回航比迎风斗浪的前行艰难得不知多了多少倍,一个个巨浪恶虎扑食般前赴后继,逆来顺受的渔船不可能再用尖锐的船尖破开大浪,却是一次次地忍受着大浪劈头盖脸地往船上灌水。被他营救上来的这些人,是拼着最后的力气爬到他这艘船上来的,他们剩下的力气只能是牢牢地抱在渔船上,不可能帮助他从船舱里往外淘水。尽管渔船的后面有卷扬机的帮助,尽管离岸已经不远了,可生还的路却还是那么漫长。离岸越近,卷毛浪越加凶狠,浪头高得好像从天而降。渔船已经无法逃避地遭受到海水的倾灌,驾船靠岸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沉船也成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范老桅只剩下最后的办法了,那就是放弃自己的这条船,靠曳纲缆绳把大家扯到岸上。他钻出驾驶舱,手指脚趾抠进了船缝,壁虎一般向船头爬去,趁着浪尖把船头高高翘起的一霎那,向着深深的浪谷抛下了铁锚。接着,范老桅爬回驾驶舱,忍受着大浪对整个船体的冲刷,开动机器倒退一段距离,又像壁虎一样爬到船尾,拼力地抛下了另一个锚,他是在用两个铁锚将船固定在海里。
这是与大海最后的拼博,两部对讲机在雨水和海浪的浸泡下已经不起作用了,范老桅用手电光向岸上发出了另一种信号,就像岸上商定的那样,他让岸上把曳纲缆绳变成传输带,不要牵拉渔船了,他要把所有的人都捆到缆绳,传回岸上。这是他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惟一的办法了,守在船上只能是等死。
获救上来的那些人渐渐地明白了范老桅的良苦用心,缓慢地爬过来,齐聚在他的身旁。范老桅逐个把他们拉到驾驶舱的顶上,再像捆猪一样,把他们的双手双脚牢牢地绑在缆绳上,让缆绳把他们传输回去。
送走了最后一个幸存的渔民,一向身壮如牛的范老桅也瘫软了下来,双手也麻木得不像是自己的了,他连把自己捆到缆绳上的力气都没有,脑袋也是木木的。
歇息了一会了,范老桅猛醒过来,把别人送出了险境,可自己呢,还在极端危险之中。他挣扎着爬起来,拼着最后的力气把自己拴在了缆绳上。就在范老桅即将离开船体的时候,大浪便把渔船高高地掀起又狠狠地摔下,顷刻之间渔船便沉没下去。范老桅的腿就是在那个时刻被砸伤了,他不能像别人那样时而是浪里时而是空中拖上岸去,曳纲缆绳随着渔船沉入了海水里,他是完全从海里被拖上岸的。上岸的时候,他已经一丝不挂了,像一条拖上来的死鱼了。人们都以为范老桅已经淹死了,怎么抢救也没用了,悲伤和失落潮水一样涌向人们的心中时,他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范老桅在海底足可以憋上一袋烟,海水淹不死鱼,就淹不死范老桅。
范老桅呆立在暴雨中,淋了一会儿,便抹了把脸上的水,趔趔趄趄地往前走,边走边说,我要睡觉。没走几步,他就跌倒了。
在那震撼人心的海难中,所有被范老桅救上来的人都像是一条条被钓上来的大鱼,浑身上下的衣服早已被大浪撕扯开了,全都是赤条条地上了岸。那一夜,所有还生的人和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都应了“赤条条而来”这句老话。
范老桅在冯乐礁的船舱里仅睡了半个时辰,突然间就被噩梦惊醒,高呼着海里还有人,就一瘸一拐地下了船,守在一艘冲锋舟旁,瞪大眼睛瞅着海里,只待风浪减弱些,再度入海救人。
8
那一次海难,范大锚命运多桀,是名副其实的九死一生,远不似冯大岸那样有惊无险。大雨骤然而至的时候,辽东湾里没有呈现出常见的那种风雨交加,范大锚和船主都麻痹大意了,他们依然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只顾一味地拔着布满对虾的网,根本没有弃网回航的打算。直至起了风,并且风越来越强烈地刮起来,他们才后悔了自己的贪婪。
范大锚不愧为渔村最优秀渔民的儿子,也没让老爹的本事白传给他,船在行驶了十几海里之后,就漂摇得不行了,风浪大得快让船舵和螺旋桨失去了作用。范大锚临危不乱地抢占了船长的位置,没有像后来那些被大浪倾覆的渔船一样惊慌失措地往岸边上赶,而是让渔船上所有的人各就各位,自己把住舵盘,让渔船斜切着大浪行驶了一段路程,向最危险的海域——环城礁靠去。暴风骤雨已经打碎了大海里所有的规律,环城礁外危险的暗流已经分崩离析了,最危险的地方反倒成了避难的地方,环城礁多少能分解一些狂涛巨浪对渔船的侵害。
渐渐地,范大锚把船头调成了顶风逆浪背对海岸的方向,他让船上的人们把船头和船尾铁锚抛下去,把渔船固定在斜逆着大浪的大海里,他要让渔船成为长在海里的树,两根抓在海底岩石上的铁锚是船的根。范大锚解释着说,风吹走浮萍易如反掌,吹走生了根的小树却难上加难,如今浪已经高得把舵尾和螺旋桨都抛出海面了,行船是最危险的事情,只能靠在海里生根熬出一条生路了。
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范大锚观点的正确,那些期盼着能早些逃出暴风雨的打击而仓惶逃往岸边的渔船,实际上是做着一种欲速则不达的努力。狂风兜着这些渔船的屁股,轻而易举地将船掀过去,转眼间渔船就倾倒了,人卷在巨浪中软弱得没有一丝挣扎的能力。只有范大锚这艘渔船在两条生根了的铁锚支持下,与狂风对峙了小半宿,最终船板被大浪一口一口地嘶咬去了,渔船像被脱掉了衣服一般,只剩下了在大浪中不屈不挠地摇摆着的龙骨。渔船已经不复存在了,范大锚和船上渔民各自抱着撕裂开的船板,在狂风巨浪中四散漂泊。
夜黑得恐怖,浪打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范大锚的脸避过风头,趁着大浪的间隙,大口大口地吸着气,那种滋味真像是被扔进了阴间的油锅里。不管怎么样,范大锚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落在大风大浪的大海里,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必须节约所有的体力,随风而飘随浪而去,等待救援。
不管风多凶浪多狠,范大锚只有一个信念,将自己所有的手指锁在一起,抱住船板,毫不放松。不知在海里漂泊了多久,冰冷的海水将他的身体泡得麻木了,将他的大脑泡出了许多幻觉,他觉得身体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灵魂飘了出来,他看到了风浪中自己可怜的躯体和无望的挣扎,可他的意识还在顽强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呛到海水,呛到海水,他的灵魂可就真的出窍了。
苦苦挣扎的滋味,比选择死亡还要痛苦,有许多时候,范大锚已经被风浪折磨得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与力气了,幻觉将死亡虚化出了无比幸福的天堂,他真想一撒手,淹死在海水里算了,可他的手和胳膊早已不听他的使唤了,死死地抠着木板顽固地支撑着他意志薄弱的生命。
后来,范大锚的意识真的模糊了,他进入了休克的状态,海水打入他的嘴里他都不知道,灌饱了他的肚子他也没知觉。这时,闹腾够了的大海已经疲惫了,雨停了,风缓了,浪也软下来,世界不再混沌,浮云和大海渐渐地分离出来,天快亮了。可是,范大锚疲惫的头却耷拉进海水里,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只等着死神的召唤。当然,他更不知道是那只巨大的美人蟹救下了他的命。
范大锚身旁的海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劈开,美人蟹从环城礁里冲出来,伸出巨大的螯将范大锚的头拱出海水,送上木板,有时还用巨螯拍打一下范大锚的背。渐渐地,范大锚的灵魂被拍回来了,他有了呼吸,身体也有了动静,嘴也会呕吐了,只是眼睛还不能睁开,生命又顽强地回归给了他。
直升机的螺旋桨轰出了巨大的响声,一道光柱从天而降。最终光柱锁住了范大锚,也锁住了美人蟹托着范大锚脑袋的大螯。螺旋桨掀出的大浪,让美人蟹愤怒起来,好像直升机重新给海里带来了台风,它扬起巨螯,冲着天上示威着,直到直升机压了下来,美人蟹才恐慌地潜入海水,飘然而逝。
援救范大锚的海军航空兵似乎看到了是只巨大的螃蟹,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螃蟹,他们误以为是只海龟,甚至把范大锚送上岸时,还在惊呼,是海龟救了这个渔民的命。
范老桅无语,他知道,肯定是那只巨大的美人蟹。
两名海军航空兵战士从软梯下来,想把范大锚拉上直升机时却犯难了,范大锚身体几乎和那块巨大的船板成为一体了,船板进不了直升机,他们又掰不开范大锚的手指头,只剩下砍断范大锚的手这一个办法了,可他们又不能这样做。没办法,他们只好将范大锚和船板牢牢地绑在一起,吊在空中,运回了岸上。
9
死亡是这一天渔村不可动摇的主题。
清早,风息浪止。可是,人们的心依然阴沉在昨夜,黑洞洞的没有曙光,充满了焦灼与痛苦的等待,她们流出的眼泪仍像滂沱大雨,呼子唤夫沙哑的声音接续着夜里的狂风。每逢有远方的亲人赶来,站在破碎的堤岸,望着黄澄澄的大海,嚎出一声凄厉的哭喊,整个渔村便会是又一轮排山倒海般的哭声。
平稳的海面上,一道道细长的波在缓缓推动,浪也疲惫了,只有到了岸边,才撞出一朵朵细碎的白浪花,像是在给不幸的渔村戴孝。
闹腾够了的大海,安静得像闯过祸的小猫,整个海面像是一匹滑润的绸缎。然而,平静的海面却到处漂浮着破碎的船板、残缺的网浮子和撕烂了的网。渔船就是每家每户的聚宝盆呀,却被大海残酷地击碎了。
海岸上,到处堆积着被海浪推上来的海物,身首异处的对虾、支离破碎的海蜇、缺螯断爪的螃蟹,还有海猫海马海兔子海白菜海芥菜海石花等等,破烂鱼更是满岸都是。一群群绿豆蝇恣意地飞翔,肆无忌惮地在吞食着海难带给它们丰盛的早餐。
面对着海岸浮动着的海物,渔村的人无动于衷,他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无心理会这些送上门来的财富。倒是那些鱼贩子们,和苍蝇一样闻到了腥味,骑着笨重的幸福牌摩托车,觊觎着海岸上漂浮着的这些意想不到的海物。他们想不劳而获地去捡,被渔村里的人一顿臭骂,骂得他们狼狈逃窜。
不幸与侥幸在那一天共同搅拌在刚刚平静的海岸,渔村里的人只知道海军出动了,除了范老桅救下来的二十多个人,还没有任何船只和渔民的消息。渔妇们堆在龙湫背上的海神庙前,引颈远眺,希望着能有渔船穿透白茫茫的海雾,驶入她们望眼欲穿的视线中来。然而,当赤红的光斑穿过白雾,跳宕在海面上时,人们看到的却是被海浪送到岸上来的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