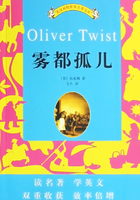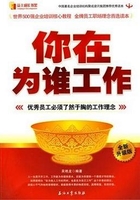苏芹觉得这么提心吊胆地等待实在窝囊,不如豁出担个挨个熊的名儿,让警察来了断这桩麻烦事儿。二河猛地扯住苏芹,他说:“警察只能管一时不能管一世,敲诈的人在暗处,咱在明处,一旦报案,敲诈的人没准真的会对咱下黑手,就是没有下黑手的胆子,也会觉得咱们好熊,等避过风头还来敲诈咱,咱是防不胜防啊。我是想自己把这事儿给了断了。”苏芹愤愤地说:“你了断,你有那狠的心吗,这事我看还是让警察光明正大地给了断了吧。”二河猛地拍了下自己的胸脯,说:“他有本事闯进咱家门来面对面地讹我,偷鸡摸狗地塞信,那是怕我,不敢见我,我有啥不敢了断的?再说了,这事儿警察一插手,敲诈的人躲起来猫风,怕是这辈子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对咱起了这么歹的心。”
苏芹无可奈何地止住了报警去的步子,咬着嘴唇,用颤抖的声音说:“他既然怕咱,我这个女流之辈也能了断,我要用更毒的招儿去了断。”苏芹说着,就翻箱倒柜,她先拿出三千块准备买饲料的钱,甩到了炕上,然后打开一个平日里总是上锁的箱子,不辞辛苦地在里面寻找着什么。
二河莫名其妙地看着苏芹,当她发现苏芹只在药瓶上打转子的时,不禁疑惑地问:“你找啥?”苏芹停止了乱七八糟的翻找,她转过头来说:“找预备给猪生癞时配的药,我把它藏在最底层了。”二河似乎有所醒悟,苏芹找的药中有一个小瓶里装的是砒霜,她是不是想把砒霜涂在钱上,让敲诈的人在数钱的时候中毒身亡呢?苏芹接下来的动作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二河的心中所想。二河按住了苏芹即将打开的那个小瓶。二河说:“这个招法太阴损了,咱不能用,我会有办法抓住那个敲诈咱的人。”
苏芹盯着二河,气呼呼地说:“他敢用毒招儿敲诈咱,我就用更毒的招儿对负他,我要以毒攻毒。”二河摇晃着脑袋说:“你昨竟办些糊涂事呢,敲诈咱的人是该死,我怕的是万一敲诈咱的人不数钱,直截把钱送进信用社,或买东西花了,咱不是做了孽吗!”
苏芹猛地拍了下自己的大腿,恍然大悟。二河拢了拢苏芹的头发,安抚着气急败坏的苏芹,说:“气头上谁都会做傻事的,咱慢慢地想办法,敲诈咱的人连赶走两头猪的胆量都没有,还敢害咱孩子?相信我吧,我有能力弄个水落石出。”
苏芹和二河相对而立,默默地陷入在没有言语的寂寞中。良久,二河缓缓地移动着沉重的步子,准备走出院落。苏芹紧抓不舍地扯着二河的衣袖,心事重重地说:“可要小心呀。”二河艰难地挤出笑容,轻声轻语地说:“我惦记着小青,看看去。”
怒火消褪了一些的二河显出了心力憔悴的疲惫,他的脸收缩成漠不关心的阴沉,严严实实地遮盖着自己内心的焦躁不安。二河就这样低着头,缓缓地动着步子,带着冷竣的面目,行走在阳气十足的街头。野蜜蜂们“嗡嗡”地唱着,讨好地飞翔在二河的身旁,灵巧的燕子穿梭在二河的眼前,招惹着二河的注目。二河的表情始终是阴沟里的老冰,顽固不化地熬在明媚的春光里。
二河走到老甜的大门口,眼光才显出了活泛。他推了几下门,没有推动,显然老甜已经加强了警戒。院里的狗们疑神疑鬼地张望着,鼻子灵敏的狗便昂扬地叫了几声。老甜扶在自己的楼门,警惕地问:“谁?”二河便大声地向妈回答着自己的名字。老甜很坦然地走出开门,狗们在听到二河的声音之后表现出宦官才会有的热情,摇头晃脑地恭维着二河。
小青从楼里冲出来,活泼得像只燕子,他冲着老甜喊:“你给我回来,野杏树掉眼泪的故事你还没给我讲完呢。”老甜的身子被小青缠住了,小青一个劲儿地嚷:“讲,讲!”老甜说:“野杏树老糊涂了,它老得该死了,不能掉眼泪了。”
提起野杏树,二河的心里一激灵,那丑陋的树干便浮现在他眼前,幸亏小青活泼地站立在他的面前,他才没有深陷到被敲诈的阴影中。二河训斥着小青:“我咋告诉你的,不许走出楼门,一步也不行。”小青不耐烦地说:“我奶都该憋死我了。”
进了楼里,小青继续缠着老甜讲“野杏树为什么会流泪”。二河吆喝了一声:“上去!”小青便不情愿地爬上了楼梯,嘴里不知嘀咕些什么。老甜不愿意地瞅着二河,说:“小青也是我的心头肉,你咋还不放心呢,你爹把咱家的楼造得铁桶似的,孙猴子来了也只能变成风儿往里钻。”二河搓了搓自己的额头,说:“不是不放心,我是心里太乱了。”
小青在二楼耐不住寂寞,“叮叮咚咚”地跺着楼板,嘴里不断地吵嚷着,老甜吓唬着说:“再跺,你的疯大伯过来会杀了你的小鸡鸡的。”小青继续跺着地板,说:“我不怕,他敢过来,我杀了他的大鸡鸡。”
二河不能容忍小青的这种无所约束,顺着楼梯走了上去。二河正想教训一番小青,忽然看到墙角处摆放着四海曾用过的那只带有瞄准镜的汽枪。二的灵性在那一瞬间勃然大发,一种擒住敲诈者的计划在他的头脑中快速地旋转着,落满灰尘的汽枪便在他眼前更加清晰了,他的计划在默不作语中渐渐成熟了。二河嘱咐几句老甜一定看住小青,不让孩子走出楼门,自己抓过那枝汽枪,包裹得严严实实,匆匆地走下楼梯。
出了小楼走在大街上时,二河不再那么苦闷,野蜜蜂和燕子也能愉快地飞进他的视线中。
三翠是在二河走后进入老甜的楼门。三翠蓬松着头发,一进屋就露出了哭天抹泪的模样,她骂着柏成林是忘恩负义的杂种,是打种没够的臊脬卵子,公狗似的到处闻骚,她骂小梅那个烂×城门洞子似的谁进都中,柏成林也不嫌埋汰,一个心眼儿地住里钻。老甜的背上爬着淘气的小青,老甜虽然在骂人上也是才华出众,但她也得顾及孙子小青呀,她对三翠当着小青的面儿无所顾及的骂法显露出了不高兴,就很懒怠地说:“过去了,就就算了,哪个猫不吃腥,男人都是这个味儿,吃着锅里惦着盆里的。”
三翠叫了一声“我的妈哟”,抓住了老甜的衣袖“鸣鸣”地又哭了起来。三翠说:“咱们娘们儿紧紧巴巴地过日子,省下钱来却让他成把成把地拿出去买臊,吃着我的嚼着我的住着我的花着我的,还拿我的钱出去嫖别的女的,我的妈呀,我得用啥招儿管住他呢。妈你再不帮我,我下半辈子不得守活寡吗。”
老甜看着自己一向泼辣的的闺女让柏成林这个男人搞得如此窝囊,气恼地用指尖点着三翠:“你真是犯贱,由他去,他愿意睡谁就睡谁,只要他兜里没有钱,谁也不能让他白睡,实在不行就撵他出去,三条脚的蛤蟆找不着,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有楼住着还愁招不来一个好女婿,你大哥都成了那个样子,不照样有个好媳妇。”
三翠摇着头,说:“我蠢笨得都没有女人模样了,那男人个能图我这个人,再说了,还有孩子连着呢,帮我想想,能有啥招法把他拴住呢。”老甜沉思了一会儿,眼光忽然一亮,她说:“招法倒是有一个。”三翠着急地问:“啥招儿?”
老甜没有立即回答三翠,转过身去,撵着小青上楼玩去。小青歪着脑袋问老甜:“你还没给我野杏树为啥会哭呢。”老甜推着小青的后背,说:“你在楼上等着,奶跟你姑说几句就上去给你讲。”小青说了句“说话算数”,伸出手和老甜拉了下勾,便痛快地跑上楼去。
老甜回转过身来,小声对三翠说:“真是傻丫头,过了好几年还没摸准男人是啥脾性,想治住你女婿,只有一个招儿,就是没完没了地跟他办事,给他抽干吸净,他就没有力气和别的女人乱扯了。”
三翠恍然大悟,脸上不由自主地袭上一丝红云,但很快就消失了。
柏成林在悠荡了两个晚上之后,觉得还是三翠的身边暖和,尽管小梅会令他神魂颠倒,那只是片刻的欢娱而已,睡女人和过日子是两码事儿,他靠的是和三翠天长地久地过日子。柏成林在小楼高高院墙的外边走了好几个来回始终没法拉下脸去敲门。
柏成林在门外徘徊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二河,他觉得只有二河才能帮他摆脱尴尬。柏成林悠悠荡荡地进了二河的院子,看见二河俩口子正忙着各自的活计,便干咳几声,用以吸引二河的注意。二河很淡地打了个招呼,柏成林便很积极地凑了上来,没完没了地自圆其说。柏成林说:“二哥,都啥时代了,没听人说吗,男人没小姘活着都没劲,女人没情夫死了变成猪,我都不怕戴绿帽子当王八,三翠咋还计较我和别人好。二哥,你劝劝她行吗,我以后一心一意只跟她好,再也不惦着别的女人了。”
二河心不在焉地敷衍着,依然不耽误自己手里的活儿,他没心事听柏成林这么多废话,挑了下眼皮说:“你不就是想回家吗,直说呗,拐这么多弯干啥?”柏成林高兴地拍了下巴掌,说:“还是二哥理解我。”
二河唤过苏芹,让苏芹炒几个菜,和三姑爷喝两口,好歹也是张家的姑爷子,没工夫陪唠喀说得出嘴,没工夫做饭就让人笑话了。苏芹瞟了眼正在院中视察肥猪的柏成林,靠近二河细声细气地说:“三翠女婿不是个好饼,是不是他敲诈的咱,你得防着点儿。”二河瞪了眼苏芹,从唇间喷出的气流中携带出:“别瞎说。”
有些醉意的柏成林跟在二河的身后进了张家小楼。老甜打开大门,冷若冰霜地看了柏成林,说了句:“都老大不小了,啥事不懂,咋就管不住那一疙瘩肉。”说完扭头走回了自己的套楼,老甜虽然很喜欢教训人,但她不想再接再厉地教训柏成林,自己虽然是为闺女好,训过了火,人家小俩口掀开被窝睡一宿就好了,当妈的却两头不够人,何况自己的闺女还没和人家掰生的打算呢。
三翠靠在自己的楼门口,肥壮的身体把门挤得狭窄,她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嘴里飞快地吐着瓜子皮。柏成林醉眼朦胧地凑近三翠,恬不知耻地作着揖,嘴里叫着:“好老婆,想死我了。”三翠将一把瓜子摔向柏成林的脸,把柏成林摔个满脸开花。三翠不屑一顾地抬高眼光,拉着长音说:“老婆再好也比不上小姘呐,睡野妞舒服吧。”
柏成林望着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三翠张口结舌,他把救援的目光投给了二河。二河紧绷着脸走了上去,他把三翠推进楼内,说:“我把柏成林给你带回来了,你们愿意打架,就在屋里蔫乎地打,打个够,别在外边丢人现眼。”柏成林见缝插针地挤进楼里,顺坡下驴地接过二河的话:“二哥,是我丢人现眼,我错了,你帮三翠打我吧,打死我也活该,今后我再不老实,你们就把我那玩意割下来喂狗。”
三翠一把扯住柏成林的耳朵,嘴里狠狠地说:“狗都嫌臊。”接下来,左一个“该死的”右一个该死的就骂开了。二河听出了三翠的骂声里有嗔怪的音调儿,就在“该死的”声音中退了出去。二河本来就没有闲心替柏成林做这种无聊而又虚假的捏合,趁此机会早早退出,去谋划他那迫在眉睫的事情。那是桩弄不好真的会出人命的大事情,二河不敢有半分的倦怠与疏忽。
黄昏以后,三翠陷入到痴迷的欲望之中,反复无穷地要求着柏成林的高潮,一直把柏成林折腾个骨肉酸麻。柏成林光着身子,鸡啄米似的给三翠磕头,说娶一个三翠等于娶十个媳妇,求三翠饶过他。三翠随手抓过一个孩子用过的尿布,擦试着胸前与柏成林共同挤出的奶液,无限自豪地问柏成林:“我和小梅谁有本事?”柏成林连三连四地说:“你厉害,你厉害。”
二河那一天的举动惊动了野杏村的许多人,那些闲得发慌的老人和妇人们听到二河家此起彼伏的猪叫声纷纷围拢过来,观看野杏村不多见的热闹场面。
这个上午距三翠与柏成林和好的日子并不久远,春风满村传送着樱桃花瓣儿,县肉联厂雇来一溜汽车就在这时停在了二河的家门口。二河将上百头猪一次性地卖给了肉联厂,听说肉联厂要拿二河的猪去挣外汇,二河一下子又成了十个万元户,这回还不知道拿哪个兜子往回装钱呢。二河心里嘲笑着这些人的蠢笨,发展到这个份儿上,早就用支票了,现钱交易只是与小打小闹的屠户才能发生。其实,这大规模的卖猪活动也是二河引蛇出洞的谋略,他觉得敲诈他的人不会不对他即将到手的大量钞票眼红心跳。
二河家的猪“嗷嗷”地叫了小半天,那些装满猪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走了,二河也跟随着那些车进城去结帐。一下子空下了十个猪圈,苏芹的心也有些空落落的,猪们毕竟是自己一瓢瓢喂出来的,日积月累的情份一下子被抽走了,多少有些依恋不舍。猪们少了一大半,苏芹的活儿也轻闲了一大半,闲下来的苏芹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两封出自一个人的敲诈信。想想猪去钱来,苏芹面对着暖融融的的日头恐惧得胆颤心寒。
二河是坐着出租车回来的,下车的时候手里拎着圆鼓鼓的皮包,那皮包很自然地让人们联想到猪的价格。二河边往家走去边想着,成败就看这个晚上了。
苏芹挟着二河拎回的皮包走到野杏树下的时候,夕阳播洒着浑黄的光芒,漠不关心地照耀着苏芹。苍老的野杏树在昏黄的阳光下,显得更加丑陋不堪,令苏芹一阵阵毛骨悚然。苏芹在接过皮包前来送钱的时候,还是一副大义凛然,现在她却是有些望而生畏了。苏芹是不怕人的,她怕的是野杏树那副妖魔鬼怪的样子,这时她就有些怨恨二河了,挺大的男人平时恨敲诈者牙根直,事到临头了胆小得让女人去送钱。这时的苏提对二河用意还没有弄清楚,也不知道皮包里仅仅在表面装点一些十元的票子,中间夹的是与钱规格大小相等的纸。
苏芹盲目地四下张望着,哆哆嗦嗦将装钱的皮包塞入野杏树根部那个树洞里,她望着活像妖魔鬼怪的野杏树,便觉得这妖魔鬼怪真的活了,慌慌张张地往村子里跑去,简直比那个敲诈别人的人还要心虚。苏芹跑出一段距离之后,胆怯也随之减小了一些,可她还觉得身后背着妖魔鬼怪的影子,这时她想起了有关鬼怕唾沫的传说,便立住了身子,折回身“呸呸”地吐着唾沫。这样的吐下去,她仿佛给自己装了胆,敲诈咱的人都不怕野杏树,我这么害怕也太让人笑话了,再说了,那个敲诈者在得知二河有钱了的消息后肯定会更加关注这野杏树,没准就在村子里的某个地方幸灾乐祸地看着她呢。苏芹壮了壮胆,缓缓地往回走去,随着最后一抹夕阳的消失,她无限延长的身影已经寡淡得没有了踪影。
事后的苏芹觉得那一次提心吊胆抑或是胆颤心惊实在是值得的,她的大胆换来了以后自己家的长治久安。她曾不止一次嘲笑自己,竟然成了胆小如鼠的人。
其实,苏芹在野杏树下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二河的监视之下。此时,除了二河知道二河在做什么,谁都不知道二河在做什么。二河在天光还很早的时候,就三转两转地转到了村外,又转了很大的弯子转到了野杏树西边的沟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