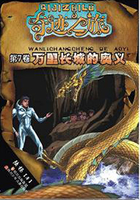我刚刚从汉林路的一个朋友家里,迁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了两个房间,一做卧室,一做书室,显得宽敞得多了;二则,我的一部分的书籍,已经先行运到这里,可读可看的东西,顿时多了几十倍,有如贫儿暴富;不像在汉林路那里,全部的书,只有两只藤做的书架,而且还放不满。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及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一大片的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的窗是朝东的,太阳光很早的便可以晒到,冬天不生火也不大嫌冷。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总有整整的半天,是晒在太阳光下的。有时,看书看得久了,眼睛有点发花发黑。读倦了的时候,出去走走,总在田地上走,异常的冷僻,不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很满足,很高兴的住着。
正门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瓷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的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9、10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囱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起来后,我的环境更坏了。四周围的英美人住宅都空了起来,他们全都进了集中营。隔了几时,许多日本人又搬了进来。他们男人大都是穿军装的,还有保甲的组织,防空的练习,吵闹得附近人家,个个不安。在防空的时候,他们干涉邻居异常的凶狠,时时有被打的。有时,我晚上回家,曾被他们用电筒光狠狠的照射着过。
有一天,厨房的灯光忘了关,也被他们狠狠的敲门打窗的骂了一顿过。
一个早晨,太阳光很好,出去走走,恰遇他们在练习空防。路被阻塞不通,只好再回过来。
说到道路,那又是一个厄运。本来有一条道路,可以直达大道,到电车站很近便。自从周佛海搬来后,便常常被阻塞。日本人搬来后,索性的用铁丝网堵死了。我上电车站,总要绕了一个大圈,多花上十分钟的走路工夫。
胜利以后,铁丝网不知被谁拆去了。我以为从此可以走大道了,不料又有什么军队驻扎在小路上看守着,不许人走过。交涉了几回也没用,只好仍旧吃亏,改绕大圈子走。
和敌伪的人物无心的做了邻居,想不到也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