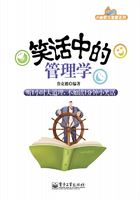一、天心阁的小客栈里
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到长沙天心阁侧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愤慨,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因为贪图便宜,客栈底主人便给了我一间非常阴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后面的窗门,靠着天心阁的城垣,终年不能望见一丝天空和日月。我一进去,就像埋在活的墓场中似的,一连埋了八个整天。
天老下着雨。因为不能出去,除吃饭外,我就只能终天地伴着一盏小洋油灯过日子。窗外的雨点,从古旧的城墙砖上滴下来,均匀地敲打着。狂风呼啸着,盘旋着,不时从城墙的狭巷里偷偷地爬进来,使室内更加增加了阴森、寒冷的气息。
一到夜间,我就几乎惊惧得不能成梦。我记得最厉害的是第七夜——那刚刚是我父亲死难的百日(也许还是什么其他的乡俗节气吧),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我望着灯光的一跳一跳的火焰,听着隔壁的钟声,呼吸着那刺心的、阴寒的空气,心中战栗着!并且想着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的情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尤其是——自己的路途呢?交岔着在我的面前的,应该走哪一条呢?……母亲呢?……其他的家中人又都飘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窗外的狭巷中的风雨,趁着夜的沉静而更加疯狂起来。灯光从垂死的挣扎中摇晃着,放射着最后的一线光芒,而终于幻灭了!屋子里突然地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拳头。我偷偷地爬起来了,摸着穿着鞋子,伤心地在黑暗中来回地走动着。一阵沙声的,战栗的夜的叫卖,夹杂于风雨声中,波传过来了。听着——那就像一种耐不住饥寒的凄苦的创痛的哀号一般。
“结——麻花——哪!……”
“油炸——豆——腐啊!……”
随后,我站着靠着床边,怀着一种哀怜的,焦灼的心情,听了一会。突然地,我的隔壁一家药店,又开始喧腾起来了!
时钟高声地敲了一下。
我不能忍耐地再躺将下来,横身将被窝蒙住着。我想,我或者已经得了病了。因为我的头痛得厉害,而且还看见屋子里有许多灿烂的金光!
隔壁的人声渐渐地由喧腾而鼎沸!钟声、风雨的呼声和夜的叫卖,都被他的喧声遮拦着。我打了一个翻身,闭上眼睛,耳朵便更加听得清楚了。
“拍!呜唉唉——呜唉唉——拍——拍……”
一种突然的鞭声和畜类底悲鸣将我惊悸着!我想,人们一定是在鞭赶一头畜生工作或进牢笼吧!然而我错了,那鞭声并不只一声两声,而悲鸣也渐渐地变成锐声的号叫!
黑暗的,阴森的空气,骤然紧张了起来。人们的粗暴而凶残的叫骂和鞭挞,骡子(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地确定那被打的是一头骡子)的垂死的挣扎和哀号,一阵阵的,都由风声中传开去。
全客栈的人们大部惊醒了,发出一种喃喃的梦呓似的骂詈。有的已经爬起来,不安地在室中来回地走动!……我死死地用被窝包蒙着头颅很久很久,一直到这些声音都逐渐地消沉之后。于是,旧有的焦愁和悲愤,又都重新涌了上来。房子里——黑暗;外边——黑暗!骡子大概已经被他们鞭死了。而风雨却仍然在悲号,流眼泪!……我深深地感到:展开在我的面前的艰难底前路,就恰如这黑暗的怕人的长夜一般:马上,我就要变成——甚至还不如——一个饥寒无归宿的,深宵的叫卖者,或者一头无代价的牺牲的骡子。要是自己不马上振作起来,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战的巨大的勇气——从这黑暗的长夜中冲锋出去,我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的情形,又重新显现出来了。从窗外的狭巷的雨声之中,透过来了一丝丝黎明的光亮。我沉痛地咬着牙关地想,并且决定:
“天明,我就要离开这里——这黑暗的阴森的长夜!并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气来,搏战地,去踏上父亲和姊姊们曾经走过的艰难底棘途,去追寻和开拓那新的光明的路一种突然的鞭声和畜类底悲鸣将我惊悸着!我想,人们一定是在鞭赶一头畜生工作或进牢笼吧!然而我错了,那鞭声并不只一声两声,而悲鸣也渐渐地变成锐声的号叫!
黑暗的,阴森的空气,骤然紧张了起来。人们的粗暴而凶残的叫骂和鞭挞,骡子(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地确定那被打的是一头骡子)的垂死的挣扎和哀号,一阵阵的,都由风声中传开去。
全客栈的人们大部惊醒了,发出一种喃喃的梦呓似的骂詈。有的已经爬起来,不安地在室中来回地走动!……我死死地用被窝包蒙着头颅很久很久,一直到这些声音都逐渐地消沉之后。于是,旧有的焦愁和悲愤,又都重新涌了上来。房子里——黑暗;外边——黑暗!骡子大概已经被他们鞭死了。而风雨却仍然在悲号,流眼泪!……我深深地感到:展开在我的面前的艰难底前路,就恰如这黑暗的怕人的长夜一般:马上,我就要变成——甚至还不如——一个饥寒无归宿的,深宵的叫卖者,或者一头无代价的牺牲的骡子。要是自己不马上振作起来,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战的巨大的勇气——从这黑暗的长夜中冲锋出去,我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的情形,又重新显现出来了。从窗外的狭巷的雨声之中,透过来了一丝丝黎明的光亮。我沉痛地咬着牙关地想,并且决定:
“天明,我就要离开这里——这黑暗的阴森的长夜!并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气来,搏战地,去踏上父亲和姊姊们曾经走过的艰难底棘途,去追寻和开拓那新的光明的路道!……”
二、在南京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船泊下关,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抱了什么苦都愿意吃,什么祸都不怕的精神,提着一个小篮子,夹在人丛中间,挤到岸沿去。
马路上刮着一阵阵的旋风,细微的雨点扑打着街灯的黄黄的光线。两旁的店面有好些都已经关门安歇了。马车夫和东洋车夫不时从黑角落里发出一种冷得发哑了的招呼声。
我缩着头,跟着一大伙进城的东洋车和马车的背后,紧紧地奔跑着,因为我不识路,而且还听说过了十点钟就要关城门。我的鞋子很滑,跑起来常常使我失掉重心,而几乎跌倒。
雨滴落到颈窝里,和汗珠溶成一道,一直流到脊梁。我喘着气,并且全身都忍耐着一阵湿热的煎熬。
“站住!……到哪里去的?”
前面的马车和东洋车都在城门前停住了。斜地里闪出来一排肩着长枪的巡兵,对他们吆喝着。并且有一个走近来,用手电筒照一照我的篮子,问。
我慌着说:由湖南来,到城里去找同乡的。身边只有这只篮子……马车和东洋车都通行了。我却足足地被他们盘问了十多分钟才放进去。
穿过黑暗的城门孔道,便是一条倾斜的马路。风刮得更加狂大起来,雨点已经湿透到我的胸襟上来了。因为初次到这里而且又无目的的原故,我不能不在马路中间停一停,希图找寻一个可能暂时安歇的地方。篮子里只有十四个铜元了。我朝四围打望着:已经没有行人和开着的店面。路灯弯弯地没入在一团黑的树丛中。
我不禁低低地感叹着。
后面偶尔飞来一两乘汽车,溅得我满身泥秽。我只能随着灯光和大路,弯曲地,蹒珊地走着。渐渐地冷静得连路旁都看不见人家了。每一个转弯的阴黯的角落,都站着有掮枪的哨兵,他们将身手克全包藏在雨衣里,有几处哨兵是将我叫住了,盘问一通才放我走的。我从他们的口里得知了到热闹的街道,还有很多很多路。并且马上将宣布戒严,不能再让行人过了。
就在一个写着“三牌楼”的横牌的路口上,我被他们停止了前进和后退。马路的两旁都是浓密的竹林,被狂风和大雨扑打得嗡嗡地响。我的脚步一停顿,身子便冷到战栗起来!
“我怎么样呢?停在这里吗?朋友?……”我朝那个停止我前进的,包藏在雨衣里面的哨兵回问着。那哨兵朝背后的竹林中用一枝手电筒指了一下。
“那中间……”他沙声地,好像并不是对着我似他说。“有一个茅棚子,你可以去歇一歇的。一到天明——当然,你便好走动了……”
我顺着他的电光,不安地,惶惧地钻进林子中间去,不十余步,便真有一个停放着几副棺材的茅棚子。路灯从竹林的空隙中,斜透过雨丝来,微微地闪映着,使我还能胆壮地分辨得棺材的位置和棚子的大小。
我走进去,从中就升起了一阵腐败的泥泞的气味。棚子已经有好几处破漏了。我靠着一口漆黑的棺木的旁边,战栗地解开我的湿淋淋的衣服。不知道怎样的,每当我害怕和饥寒到了极度的时候,心中倒反而泰然起来了。我从容地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还不曾浸湿的小棉衣来,将上身的短的湿衣更换着。
路灯从竹林和雨丝中间映出来层层的影幻。我将头微靠到棺材上。思想——一阵阵的伤心的思想,就好像一团生角的,多毛的东西似的,不住地只在我的心潮中翻来复去:
“故乡!……黑暗的天空……风和雨!……父亲和姊姊的深沉的仇恨!……自家的苦难的,光明的前路!……哨兵,手电,……棺材和那怕人的,不知名姓的尸身!……”
这一夜——苦难的伤心的一夜,我就从不曾微微地合一合眼睛,一直到竹林的背后,透过了一线淡漠的黎明的光亮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