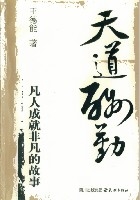“喂,”那个人向他说:“怎么的,站在这儿?”他猛然转过身,看见是一个同志,一个最能够抄写和最擅长宣传的同志,也是一个为工作而不知疲劳的人物。
“印字机!”他叫出他的浑名了。“你也来逛公园么?”
便和他握了手。
“我只是过路,”他的同志回答:“你怎么老不叫我王振伍呢?我们在中学时候就给你叫惯的。”
“这是你光荣的符号呀!”他笑着说。
王振伍作出不乐意的样子:
“我可不愿意这就是我的光荣呢。我们是该干出一点更大的工作的。”接着问:“你笑些什么?”
“我快活我现在看见你,”你真心的说。
“我们不是常常见面么?”
“也许是我自己的缘故,”他继续说:“我今天看见你特别觉得高兴。”
“你发生什么得意的事?”王振伍猜着问。
“有一点,但是现在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你站在这儿做什么?”王振伍猜想这是一个原因。
“看风景,”他玩笑的说。
“的确是一件雅事呀。”他的同志感到兴味似的说:
“你一个人的情致倒不错……我呢,我成天只知道运动我的手和嘴,我从没有用眼睛看过风景——我不想这种开心……”
他插口问:“你现在到那儿去?”
“回去。”
“到我那儿去吧。”
两个人便动步了。
他们一面走着一面密谈起来。
“刚才,”王振伍低着声音说出秘密机关的代表名称——“‘我们的乐园’里接到一种消息……”他把眼睛看了两边——“恐怕在上海就要发生大事件呢,说不定就是空前的大事件……而且是马上就会发生的。”
“什么时候接到的?”
“下午一点钟,”接着又用低声说:“如果这一次真的发生了,是我们将来胜利的预兆……我们实在应该在这时发些火花……所以……好的,我们等着。”
“那末你的意见呢?”
“我自然是贯彻我的主张:须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得到大成功,我们是必须经过许多小暴动,否则,要一次就将我们的全民众激动起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我们的民众们还是太幼稚的,至少要给他们几次大刺激,然后他们才能够醒觉而自立起来,而站到我们这一面。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这样想,现在我们最急切的就是牺牲——同时也就是暴动。我们是应该赶快把我们的火花散开去,而且要散得多,散得远。”
“好的,我们等着。我想我们要走到紧张的第一步了。”
便不约而同的握了一次手。
于是静默地走了好些路。
“我刚才看见张铁英,”王振伍离开了正题目,而说起闲话了:“她今天很不高兴,一连给我三个钉子碰。我想这是我替你受的冤枉……你今天没有看见她么?”
“看见过,”刘希坚平淡的说,在他的心里还飘荡着白华的影子。
“这就是她不高兴的缘故了。”王振伍笑着说:“我猜的没有错。”
“你不要乱猜,我和她没有什么的。”
“我知道,”他望了希坚一眼。“我知道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在你的观念上——自然只是对于异性的观念上——你不会喜欢她。”
刘希坚没有回答。
“其实,”他接着带点严重的声音说:“张铁英在我们的工作上她是成功的,可是——她在恋爱方面总是失败的。我听说她以前曾爱过好几个人,人家只把她当做开玩笑的目的。”
“的确,”希坚承认了他的话。“她是我们的好同志,最能够工作的一个很难得的好同志。”却把恋爱的一面省略了。
“她真能够吃苦呢。”王振伍接着称赞似的说:“这自然有她的历史做根据的。她父亲是一个雇农——”
刘希坚惊讶的插口问:“你怎么知道?”
“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她九岁时候就替人家看过两条牛,她十四岁还在田上帮她父亲播种,你只看她的样子就会相信了……”
“是的,”希坚用坚决的声调说:“我相信。我早就看出她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连小资产阶级也不是呢,”王振伍赶快地补充说。
“她怎样跑到北京来的呢?”希坚探求的问:“为什么她离开她的环境?”
“我不大清楚。她没有对我说。她只说她的父亲被穷苦所迫而变成一个暴戾的酒鬼,要卖她……我想她跑出来就是这个缘故。”
刘希坚沉思着。
王振伍接着问:“她没有对你说过么?”
“没有,”刘希坚简单的回答。
“怎么会没有呢?”
“不知道,她从没有说到她以前的生活。”
“大约是这样的,”王振伍想了一想便分析的说:“她把我看做一个朋友,而把你看做……唉,我们所处的地位正相反!”
刘希坚被这位忠实朋友的自白而笑起来了。他想着这位朋友在工作上是前进的,在恋爱上便常常被人挤到落伍者的地位。
“你可以努力进行,”他笑着说。
“完全没有用。”王振伍尊重的回答:“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是不行的。我努力也不行。我已经失败过好几次了。对于张铁英,我认为是最后的一次,以后我不想再讲恋爱了。”
“你们怎么样呢?”刘希坚完全关心他朋友的问。
“没有什么,”他低沉着声音说:“我不会使女性喜欢,这就包括一切了。不过我对于张铁英并不这样想,因为我认为在我和她的出身阶级的立场上,我们是应该结合的。
你知道,我也是从……”他把话停住了,过了一会又接下说:“我常常回想我以前当学徒的生活……”
刘希坚不作声,只望一下他朋友的脸,在心里充满着对于这朋友的历史的同情。
彼此都沉默着。
这时的天色已经灰暗起来了;暮霭掩住了城墙上的楼阁;孤雁开始在迷茫的天野里作哀鸣的盘旋;晚风躲在黑暗里而停止在树梢上;路上的行人和车马都忙碌地幌动于淡薄的灯光里……王振伍忽然用慎重的低声说:“上海内外棉织会社的罢工风潮,我对于这风潮的扩大,认为我们的民族革命要走到爆发的时期,你呢?”
刘希坚向他点着头。“到公寓里再谈,”他说。
他们便加快了脚步;十分钟之后,就走进三星公寓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