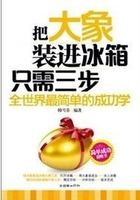我是嗜好文学的,也曾多时努力于文学的创作;然而我却不是文学研究家,对于文学,我没有深湛的理论,关于别人的深湛的文学理论,我所涉猎的也极有限。因之我对于文学的知识,与其说是由学习得来的,勿宁说是由经验得来的,更为确切些。
文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究竟负有何种使命?在我平日提笔创作时,对于这个问题,就不曾思索过。我只觉得我要创作的动机:有时是为了回顾既往的生命伤痕,不知不觉发生感喟与悲叹的呼声;有时是为了不满足现实,而憬憧于未来的乐园,写出瑰奇的理想;有时发见生命的真意义,以某种事实为象征,写出极兴奋和突进的生命的波动;有时是为大自然的伟丽所惊吓发出赞美与歌颂;有时为了一种同情而悲哭而狂呼……将我创作的动机归纳起来,可以说只是为了表现我自己的生命而创作,至于这些作品所收的效果,也许有时要出我意料之外的有意义。譬如说我看见一个人力车夫,在狂风暴雨之下,拉着车子,在那泥泞的路上扎挣,而坐车的人们,还是怒容满面,嫌他拉得慢,我便想到这个人力车夫,他怎么就该这样受苦难?他也有灵魂,他也有智慧,而人们对他为什么特别残刻呢?如果有一天,命运也是一样的播弄我,使我也落到这步田地,其痛苦将如何?
——这时我的意识上有了一种极痛苦的感觉,似乎我也正是那个人力车夫,不知不觉心酸落泪,这种的热烈的同情,真占据在我灵魂深处;直到从街心回到我的家里以后,心头还似乎有所梗塞,无论如何排遣不开,只得坐下来,伸纸拈毫将这件事的印象,——我的灵魂所体验的情绪,不加丝毫掩饰与造作,很忠实的描写出来。当这篇稿子完成的时候,我被压迫的心灵,便渐归平静,并且感到舒适与欢喜。
关于描写一个人力车夫的经过既如上头所说。那么,我的动机当然只是要发泄我自己对于人力车夫的同情而描写而创作,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了。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看我那篇文章的人,有的或者要加我以尊严的头衔,说我这篇文章大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一篇打破社会制度,革命的文学作品。因之我就是最可钦佩的,最时髦的革命文学家了。倘若果真有这么一天,我是被人们这么恭维的时候,我除了受宠若惊之外,还要汗流浃背,因为问良心,我当时就没有这么尊严的想头。
说到这里我不免连带想到我们伟大的作家易卜生来了。他写《傀儡家庭》,当时许多新妇女认为他是为了提倡妇女运动而写那个剧本的,都到他面前大恭维他一顿,但是她们所得到易卜生的回答,可是太出人意外了。易卜生说:“我只为作诗而写《傀儡家庭》的。”那些妇女听了这话,都不免暗暗称奇,然而这却是真正的作家,对于文学的态度呢!
创作只是因为创作,这种原理并不是很神秘而深奥的,只要我们能明白什么是文学,和文学家对于社会人类所负的使命,就知道因创作而创作是很自然的结果。
什么是文学,各家对于文学的定义,说法很多。我们用不着陈列古董似的,逐条列举,只要在各家的说法中归纳出文学几个必具的条件就够了:
一、文学的四要素;二、文学的普遍性与永久性。
以上两个条件,是文学的基本原则,下文当逐条论之:
一、文学的四要素就是说凡是文学,不可缺少思想,感情,想象,形式四个要素。所谓思想就是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等,但是一篇作品中,仅有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这只是一种知识,只能使人知,这是哲学科学的职能,而文学乃是使人知而且感的东西。文学是把知的作用的直觉,附贴到情上的,所以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同情。没有同情的作品,是不会与人发关系的,使达人由醒而醉,使俗人由醉而醒,都不过是同情而发出来的奇异的光彩。所谓同情,就是超于自身利害之外的“大我”之情,与拘束于个人得失“小我”之情不同。诗人之作诗是发于情,即诗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个情便是极伟大的同情,乃抉千万人心灵深处共有的情感而唤起,这种情感就是文学的生命,所以看了别人受痛苦,仿佛是自己受一样。这种与宇宙合一的伟大情感而写成的作品,自然具有丰富的感人之力,自然可以成为人我心灵交通的一道桥梁,自然是我与宇宙万有间的一把锁匙了。这种作品,定能使读者有“先得我心”之感了。
文学由感情而成立的,但同时也就是由想象而成立的,因为同情是想象的产物,或副产物。所以王尔德批评列颠狱官的没有同情,而说:“那人连一点想象力也没有的。”意思就说虽然没有受痛苦,但是看了别人的痛苦可以体验出那苦痛的滋味。这种的体验是想象也就是同情,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密切的。兰斯肯虽分想象为三种:一、联想的想象力,二、洞察的想象力,三、冥想的想象力,然而总须与同情相溶洽,才能写出最优良的文学作品。
至于形式对于文学也极重要,前三者——思想,感情,想象——是文学的内在精神,而形式是属于外表的,这个内在的精神是否能完全表现出来,那就全看外形的巧拙了。
二、文学的普遍性与永久性文学的四要素中的感情、想象诸原则,也就是文学的永久性与普遍性的根据点,文却斯德(CTWinchester)说“文学是含有不朽的兴味的著作”。这种兴味就是根据于诉于人的感情之力,这种力是随时可以唤起人们感兴的。所以大文学家优良的作品,可以百读而不厌,这就是文学的永久性;然而这种诉于人类的感情之力,绝不是特殊的个人之私情,乃人类共通的情。文却斯德又说:“各人的感情是瞬间的,个别的,而人类一般的感情却是共同的东西,所以为共同者就是超越时间空间,以及人人都能共感共有的话。”所以千古常新的文学,一定不是某种主义的奴隶,也不是某种思想的工具。
文学的本质是打破一切因袭与束缚,是完成自由的东西,它是要努力,将重重物欲所遮掩的真相,暴露于人间的,所以它才能万古常新,不然荷马时代的东西,为什么到今日还是一样的使人感兴呢?韩退之的《秋怀》诗说:
“……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这也是文学有永久性的证明。
文学如果只有时代兴味,而没有越超时间空间及国民性等的独立精神,这种文学就失去它万古常新的效能,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永久性与普遍性了。这种文学就象一株凌霄花,将随它所倚附的禁种树而并逝,——离去它的时代,它就没有存在的可能。譬如英人Pamfret,他是为时代的趣味而作诗的人,当然虽然是名重一时,被人尊重为最伟大的诗人,但不过百年就寂然无闻。
我们对于什么是文学——即文学的根本原则既然明白了,那末文学家对于社会究竟应当负有何种使命,当然也可以迎刃而解了。
文学家诚然是社会的先驱者、预言家,他与时代发生极密切关系,他可以统一人的感情,并引导着趋向同一的目标去行动,譬如意大利之所以能收统一之效,有人归功于但丁(Dante) 的一部《神曲》。法国的卢梭与福禄特尔对于法国革命也有极大的影响;他如歌德对于德国帝国之成立,其力量不亚于俾士麦,这些事实我们都不能否认。但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先驱者,预言家,必须有独立不拔的精神,才能不受社会的因袭之束缚,不为利害而顾虑,并且努力打破一切的因袭与束缚,抛却一切利害的顾虑,在这虚伪残刻的社会,而培植上美丽的生命之花,这就是文学家唯一的伟大的使命,否则宛转因物,又怎配作先驱者、预言家呢!
世俗的一般人,对于文学家不是把他们崇拜如一尊神秘的偶象,就是把他们看成一个不足轻重的吟风弄月的骚人墨客,——只为风雅点缀而无益于社会,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有一些虚伪的文学家,他们实在有可以予人攻击的弱点,他们不是作些无病呻吟的假文学,就是引人到堕落的路上去的满足粗鄙的肉欲的作品,再不然就是迎合时好,作些应时小卖的作品去投机,这种人根本他自己就没有认识他自己的灵魂,他又怎么配表现自己的人格呢?他们的灵魂正在阴影中麻木的睡着了,他们所发出来的欢喜与悲伤,都不是从他们灵魂深处抉发出来的,只是些浮浅的含糊的梦呓,这种梦呓当然没有活跃的生命力的,要想发生诉于人的感情之力的效果,又怎样可能呢?
这一种人,他们自甘堕落,固可勿论。还有一种人,他们倒也并不甘于灵魂的堕落,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文学,因之他们不从文学的根本上努力、培植,唯注意文学的形式派别,什么写真,浪漫,理想等主义的分歧。这种思想便占据他们的全心灵,每一举笔,先把自己安放于某种主义的束缚之中,而不能充分的发展自己的灵性。这种作家绝不能作社会的先驱者,预言家,他只是忠于模仿别人的创作,而自己不能创作,这是有貌无神的作品。所以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心里,绝对没有主义没有派别,他们只知为创作而创作。
自然,作家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又焉能不受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无论翻开哪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从那作品里看出作者的时代,作者的地方,以及作者的国家,然而这并不与越超时间空间的问题相矛盾的,因为前者所说的是文学的基本原则,后者所说的是作品自然发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不期然而然的,这种的表现是无害于根本的共同的情感,而永久存在于日光之下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打一个譬喻来说明,例如有甲乙两个人,一个是极富一个是极贫,这两个人的形式上当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怎样差别,根本上他们都是人,这句话谁也不能反对吧,同时他是某甲,同时他也是人;同时他是某乙,同时他也是人。文学家所取的材料,不妨有各种各式,并且越要描写得特别真切,特别恰合,所描写的每个人越有区别越有个性越好。但是切不可忘了他们都是人,他们有人共有的情感,作家若果明白这一点的奥妙,那么他创作的时候,自然不甘拘虚于某一种方式之下,而甘为某一种主义所屈伏了,也不甘为某种主义工具了。并且越不存心宣传什么,只赤裸裸的表现自己的生命,表现自己的全人格,而他的效果,也许具有绝大的动人的力,越与人类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学作品,乃是因纯粹的艺术冲动而创造出来的,不受浮沉时代表面的小潮流和漩涡所卷没。这种作品可以使我们忘记我们窒息的时代,消失我们不纯洁的观念,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活更向上去努力,这才是实感与表现混合结晶,是向上的优秀的艺术。
因之,我们有志于文学的人们,又应当努力的去生活,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力扩大起来,对于社会的真实的要求,加以充分的体验,有了相当的涵养,自然而然可以产生最好的文学。
并且我们还应当注意对于真正的文学的阻碍力,正似乎魔鬼般,变幻出种种迷人的色彩,极力的引诱我们,使我们极自由的灵魂,被拘于人间极残刻的牢狱中,就是一般人,所呼号的文学应有主义,文学应当加上革命的头衔,使凡作家都困顿于这种时代趣味之下,满纸都只是造作的不真实的痕迹,把文学独立的上进的精神完全埋煞,不去努力更伟大真实的作品,只是与浅薄的人间厮混,这是人类文化的大劫运。——自从世界商业化之后给予文学的毒害,已经是不浅了,若果再加上些别的束缚与桎梏,文学的前途将更黯淡了,所以我们爱好文学的人,应当把文学从那可怕的漩涡中救出来,而使它恢复原有的光耀,而增进它的光耀,这就是文学家唯一的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