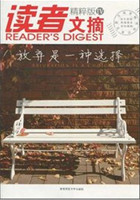在老马和欧阳琼的保驾下,两位身强力壮的红军战士抬着一副担架快步走来。
担架上侧躺着昏迷的张华男,身上盖着一床军被,看不见他受伤的地方。
姚秀芝近似小跑地越过霍大姐,赶到担架旁边,不住声地叫着:“华男!华男……”
霍大姐赶过来:“老马同志!张副参谋长的伤……”老马边走边说:“不轻,大姐……”
霍大姐:“快抬进院中抢救!”
还是那座庭院中外日
两个红军战士把担架轻轻放在竹床旁边。
老马和欧阳琼小心地把张华男从担架上抬到竹床上。姚秀芝紧紧抓住张华男的一只手,迭声呼唤:“华男!你醒醒,你醒醒……”
这时,身材颀长,戴着金丝眼镜的红军大夫拿着医疗器械走到竹床旁边。
霍大姐伸手接过医疗器械。
大夫撩开盖在张华男身上的军被,特写:
张华男的臀部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军装和军被。姚秀芝本能地惊呼:“华男!……”
张华男渐渐从昏迷中醒来,他微微地睁开双眼,并看见了姚秀乏,无力地叫了一声:“秀芝……”
姚秀芝惊喜地:“你……你可醒来了!”
霍大姐摇了摇头:“秀芝,你快去给张副参谋长准备点吃的吧!打下手的事,由我来帮着做。”
姚秀芝很不情愿地说了声“好,好……”,冲着张华男点了点头,遂转身踉跄向厨房走去。
霍大姐拿起剪刀,把臀部的裤子小心地剪了一个圆圈,由于淤血粘得太紧,掲不下来。
大夫看了看:“端点盐水来,浸泡一会儿再揭。”
张华男边说:“不用了!”边用手揭了下来。
霍大姐惊得“啊”了一声。
特写:张华男臀部的伤口渗出了殷红的鲜血。
大夫:“决去端点盐水来消毒!”
霍大姐:“是!是……”她余惊未消地向厨房走去。
厨房外屋内曰
姚秀芝心慌意乱地向碗中倒开水,竟然倒在了自己的手上,烫得险些把碗扔在地下。她急忙把水碗放在锅台上,又转身取来些许盐巴放入碗中,用筷子搅拌。
霍大姐走进屋来“秀芝!快弄些盐水,”
姚秀芝双手递上那碗盐水:“给,我已经弄好了。大姐,他……”
霍大姐边接碗边说:“是条汉子!放心吧,用盐水洗伤,他顶得住。”说罢转身走出屋去,遂又转过身来叮嘱:“秀芝,拿出我们留下的白米,绐他做碗热乎乎的米粥。”姚秀芝:“是,我这就生火做饭接着,她惶恐不安地淘米、生火,不时地还侧耳听听院中的谈话。
霍大姐:“华男同志,要忍着点,盐水洗伤口会很疼的。”
张华男:“没事!你们洗伤的盐水,决不会比国民党的辣椒水更刺激吧?”
大夫:“当然没有!可我还必须告诉你,我们没有麻醉药品,做手术将会是非常疼的!”
张华男:“大夫,你就放心大胆地动手术吧,我虽然不是关云长,可我的骨头,也绝不比他软!”
姚秀芝听罢惊得—怔,她匆忙向火中添加一把柴禾,遂又禁不住地探出头,窥视院中做手术的情况。
姚秀芝因距离较远,只能看见大夫拿着剪刀的动作,以及霍大姐捧着医疗器械忙碌的样子。她看不见张华男的表情,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柴火正旺,锅中的水滚沸,溢到火苗上,发出刺刺啦啦的响声。
姚秀芝急忙转身救火,揭开锅盖,放上白米,加柴煮饭。
庭院中夕卜日
张华男静静地躺在床上,额头上布满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面颊滚下。
特写:张华男头部两边所谓的枕头上湿了两大片。
大夫终于做完了手术,看了看张华男的表情,敬佩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命令地说道:“快拿块毛巾来,给伤员擦擦这满脸的汗水。”
霍大姐转身取来毛巾,轻轻擦去张华男额头上的汗水。大夫“秀芝!白米粥煮好了吗?”
姚秀芝在屋内回答:“煮好了!”
大夫:“端过来,给伤员喂饭!”
姚秀芝:‘好!我这就来。”
有顷,姚秀芝端着一碗白米粥走出厢房,来到手术床旁边关切地:“疼吗?”
张华男微微地摇了摇头。
姚秀芝盛了一勺白米粥,吹了吹,复又用舌试了试,小心地放人张华男的口中。
张华男无力地、却十分香甜地吃着。
姚秀芝细心地给张华男喂米粥,突然一股异样的情感扑人心头,她泪水盈眶,痛苦地盛了一勺白米粥,未加处理,放入张华男的口中。
张华男因米粥太热,烫得欲吐不行,欲吃不得,十分狼狈。
姚秀芝惊慌地,“对不起,吐了吧……”
张华男强作英雄地:“不!不热……”忍烫咽了下去。霍大姐看着泪水滚动欲出的姚秀芝,不解地:“秀芝,你这是怎么啦?”
姚秀芝边说“没什么……”边又盛了一勺白米粥,吹了吹,泪眼模糊地放人张华男的口中。
黎平城郊外日
朝霞染得碧空万紫千红,映得山川生气盎然。
笛声悠悠,“哎呀来”的旋律在晨空中自由飘游,显得是那样的清纯、悦耳。
姚秀芝驻步一条小溪旁边,循声望远方,怅然凝思。老马沿着小溪大步走来,他望着痴迷于笛声的姚秀芝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
笛声突然终止了,姚秀芝不无遗憾地自语:“彤儿,你怎么不吹了?”
老马紧走两步,怆然地:“她准是吹累了。”
姚秀芝闻声转过身来:“老马,你……”
老马很不自然地一笑:“和你一样,听彤儿吹笛子。”
姚秀芝:“我看,是有事吧?”
老马“对,首长请你。”
姚秀芝淡然一笑:“请我?……”
老马:“一点也不错!”
姚秀芝:“新鲜!”
老马:“我想,他也可能是听到彤儿吹的笛子声了吧?”
姚秀芝:“那……他是可以把彤儿叫来的啊!”
老马:“可他……”
姚秀芝:“就因为我的原因,连可怜的彤儿都可以不见,是吗?”
老马:“我……不清楚。”
姚秀芝猝然变色:“告诉他,我不想见他!”
老马:“那你……”
姚秀芝:“我留在这儿,等霍大姐回来。”
老马:“是不是想从她那儿……听听黎平会议的精神啊?”
姚秀芝沉重地点了点头。
祠堂厢房中内展
张华男卧在竹床上蹙着眉头,不时地耳听听室外的动静,复又叹气摇首。
有顷,他下意识地哼唱起了“哎呀来……”
小溪旁边外展
霍大姐兴奋地:“黎平会议结束了,中央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改变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作战计划,西出贵州,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重建革命根据地。”
姚秀芝沉吟有顷:“这能不能说,毛主席又开始指挥红军打仗了?”
霍大姐:“我的那一位对我说,起码证明毛主席在军事上有了发言权了!”
老马:“这就好了!根据我的经验,毛主席指挥打仗行。”
霍大姐:“就是肃反不行,对吧?”
老马:“这……是两码子事嘛……”
姚秀芝:“我这个毛派骨干分子……”
霍大姐:“还是不能平反,对吧?”
老马:“这……不知道。”
霍大姐:“我知道我们的老马同志多的是原则性,少的嘛……是灵活性,对吧?”
老马突然把头一歪:“我看啊,这顶帽子给霍大姐戴上也正合适。”
霍大姐一怔:“一点也不合适!”
老马激将地:“你敢不敢把彤儿叫来,让他们一家三口团圆一下啊?”
霍大姐:“是你的主意,还是你们首长的意思?”
老马:“这……你就不用问了。”
霍大姐笑了:“秀芝,你说呢?”
姚秀芝痛苦地低下了头。
厢房祠堂中内日
张华男依然卧在竹床上,蹙着眉头,微合着双眼,完全陷人沉思中。
姚秀芝悄然走进,打量一下张华男的表情,有些冷漠地问:“你找我有事吗?”
张华男蓦地睁开双眼,有些慌乱地:“没、没事……”姚秀芝生气地:“没事派人找我干什么?”说罢转身就走。
张华男慌忙地:“秀芝,你……”
姚秀芝闻身又转过身来:“有什么事吗?”
张华男:“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
姚秀芝:“你认为有这种必要吗?”
张华男涨红着脸:“有,有啊!……比方说。你有没有心事和我说说呢?”
姚秀芝就要发怒了:“像我这样的人,向你这种人述说心事有什么用呢?”
张华男:“有啊,有啊……不妨说说看。”
姚秀芝蓦地摘下那顶没有红星的军帽,双手捧到张华男的面前,怒不可遏地:“我要你把收回的那颗红星还给我!”张华男狼狈地:“这……”
姚秀芝:“办不了!对吧?再见!”
张华男:“秀芝!秀芝……”
姚秀芝驻步原地,一动不动。
张华男哀求地:“我们谈谈彤儿好吗?”
姚秀芝猝然又动了感情:“你还有什么资格和我谈彤儿!离开中央苏区两个多月了,为什么不让彤儿来看我一次?就说你负伤了,为什么也不想和彤儿见一面?你扪心自问一下,对得起我们的彤儿吗?”
张华男:“我怕给彤儿的心灵造成创伤啊!”
“妈妈!”
姚秀芝和张华男闻声同时循声望去:
彤儿哭喊着跑进厢房一头扑进了姚秀芝的怀抱中。姚秀芝双手用力抱着彤儿,大颗大颗的泪水滴在了彤儿的身上。
张华男从惊愕中醒来,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双手吃力地撑着病床,忘情地喊着:“彤儿!彤儿……”
这时,霍大姐走进厢房,走到姚秀芝身边,动情地:“彤儿,爸爸叫你了彤儿仰起泪脸:“爸爸,你怎么了?”
张华男:“挂彩了。”
彤儿:“一定很疼吧?”
张华男:“擦破了点皮,不疼。”
彤儿:“你怎么不派老马叔叔叫我去啊?”
张华男嗫嚅地:“我……”
姚秀芝再次火起:“他怕影响自己当官!”
张华男:“你……”
姚秀芝:“我只不过说了句实话!”她说罢拉住彤儿的手:“妈妈什么都不怕,走!跟妈妈进屋说会知心话去。”张华男伸出双手:“彤儿!彤儿……”
姚秀芝拉着彤儿快步走出了厢房。
张华男再次呼唤:“彤儿!……”十分痛苦地合上了双眼。
院中传来彤儿答话声:“爸爸!……”
霍大姐叹了口气:“算啦,让她母女先亲热亲热吧。”
张华男凄楚地:“那我……”
霍大姐:“我陪着你谈谈。好吗?”
张华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姚秀芝的住处内日
姚秀芝边给彤儿剥橘子边说:“剧团的同志们都好吗?”彤儿边吃橘子边说:“好,大家可想你呢!”
姚秀芝:“排练什么新节目了吗?”
彤儿:“没有。”
姚秀芝:“为什么?”
彤儿:“大家说,没有你这个团长编和排,只能演过去的一些老掉牙的节目;另外,长征以来,天天不是跑就是打败仗,大家也没有心思排练新节目。”
姚秀芝叹了口气:“苦妹子好吗?”
彤儿:“不怎么好。”
姚秀芝:“为什么?”
彤儿:“她特别想你!还有,她对爸爸他们这样对待你,怎么也想不通。”
姚秀芝:“还有别的原因吗?”
彤儿神秘地:“听说她肚子里有小孩了。”
姚秀芝怆然地叹了口气。
祠堂厢房内日
霍大姐严肃地:“华男同志,中央苏区是怎样搞起来的,工农红军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你知道吗?”
张华男:“当时,我在上海,不在苏区,但作为党员,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党的功劳。”
霍大姐:“请问我们的军事家,丢掉中央苏区,牺牲这么多的红军战士,又是谁的功劳呢?”
张华男:“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被迫撤出中央苏区,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的结果嘛!”
霍大姐:“不对!前四次反围剿,我们为什么取得了胜利?”
张华男:“这……”
霍大姐:“这是因为敌人的兵力太弱,我们红军的力量太强的结果吗?”
张华男:“你……这是什么意思?”
霍大姐:“很简单:我——不仅仅是我,全体红军指战员历经血战湘江的惨败之后,都在寻求红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同时还在思索你——还有你的那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同学们,为什么一到苏区就反对毛主席?”
张华男:“你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
霍大姐:“你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张华男愕然地:“你……”
霍大姐心平气和地:“我只能这样对你说:我敬重你,才这样剖腹见心地和你谈。”
张华男听后蹙起了眉头,似在思索着什么。
西行的山路外日
红军快步行进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
张华男躺在担架上,非常痛苦地合着双眼。
霍大姐和姚秀芝边行军边交谈着什么。
突然,前方响起休息的军号声。
红军指战员相继停止行军,就地休息。
老马站在一棵大树底下,大声地:“把张副参谋长抬到这儿来!”
两个抬担架的红军战士应声走过来,小心地把担架放在大树下边,一个用衣襟擦汗,一个捧着军用水壶喝水。老马赶过来,取出一个饭团:“首长,吃点东西吧?”张华男边说,“不吃!”边拿起身边的拐杖用力站起来。老马慌忙扶住张华男,“首长,你……”
张华男,“我要下地锻炼走路。”
老马边扶着张华男一拐一瘸地走路边交谈。
张华男:“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老马想了想:“是想听真话吗?”
张华男生气地:“你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提问?”
老马:“我知道说真话会惹得你不高兴的。”
张华男:“你要注意,不要跟着他们瞎议论,更不要把矛头对准现任党中央。”
老马:“如果错了呢?”
张华男:“你怎么知道对和错?”
老马不知如何回答。
不知何时。霍大姐赶到了他们的身后,不服气地说:“华男同志,看来我们只能当阿斗了?”
张华男瞪了一眼,没有说什么。
霍大姐话中有音地说:“不要不服气!只有那些知错就改,敢于向真理低头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张华男有气地哼了一声。
霍大姐有些挖苦地:“共产党人是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的,有话放在肚子里会发霉的。”
张华男近似自语地:“说就说,我就不相信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我更不信山大王式的游击专家能打败敌人……”
霍大姐笑了笑:“华男同志,我劝你还是认输的好。”
张华男:“输?谁输?……”
霍大姐:“那你我就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定格叠印字慕:第二集终
在男女声画外音中,叠印出相应的画面:
男声画外音:“霍大姐和张华男的争论只是红军中的一个缩影,因为广大的红军指战员面对失败的危局,都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在乌江设的防线之后,又出其不意地智取遵义。中央决定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军事路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