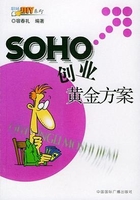“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嘴里能讲出来,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国家的珍宝;嘴不能讲,但有实际行动,这是国家的重器;嘴上讲得好,而行动上做不到,还能为国家所用;嘴上说得漂亮,而行动上则为非作歹,这种人是国家的妖孽。)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曾把官员等级评定为四类,即国宝、国器、国用和国妖。现代著名学者梁济(梁漱溟之父)也说做官有两类人,一类“视官为身家仰给之资,则谋生者不可一日离”;另一类“视官为国事责任所寄,则负疚者不敢一日居”。他在此模糊提到“政治负疚感”,说从政者如果有“政治负疚感”,便一刻不敢逞威福,一刻不敢松懈努力;“以人民救星自居的人,最终不过是人民灾星”。
身怀“政治负疚感”,自觉将服务于社会国家作为自己为官从政的主要目的,在这方面,中国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无疑为后世清官的典范。他自觉身体力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恪守道义,是个模范官员。他曾说:“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及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每夜反省自己一天所为之事是否与俸禄相称,如果不相称,竟至于彻夜不眠,思量次日如何弥补上来。这种带有自虐性的慎独精神,无疑弘扬了先秦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传统。
当然在国府内部,不乏有国宝、国器、国用之才,怀有“政治负疚感”的官员也大有人在,比如国民党名市长、学者吴国桢先生,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等等,都是非常勤政的官员。但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彼时的国民政府,正如一个濒临倒闭的大公司,尽管主管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惨淡经营,员工们也克勤克勉,但依然无法补救破产的命运。
古语云:“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某些人深谙此道,于是枉法舞弊,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假公济私,大发国难财。“人逢利处难逃,心到贪时最硬”,“前仆后继,人见利而不见害;左游右泳,鱼见食而不见钩”。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生活简朴的官员,肯定都是勤勉政事,不会徇私舞弊或贪赃枉法的清廉之士,而奢侈腐化必是堕落的温床。某些国民党官员醉心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社交娱乐生活,“费辄千万钱,供得一时乐。杯浮赤子膏,筵列苍生膜。宫廷日欢娱,闾里日萧索。犹嫌白日短,醉舞银蟾落。”(《饮宴诗》)报纸上也经常乐此不疲地传出某某高官与某某明星的花边新闻。他们忘怀国事,醉心于酒池肉林,风月场中鱼游春水,游风戏浪;他们倚翠偎红,最爱美人朱唇上那颗樱桃,皓齿间两行碎玉,没魂乡里眠花梦月,惹草招风。
“蝇伏蜗居朽木生”,官员腐败如同食物变质一般不可禁止,又如箱中的烂苹果具有惊人的破坏力和感染力。蒋介石老先生本人能够克难奋进,克己克俭,但却无力改变这普遍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此他心力交瘁,痛愤之至而又无可奈何。而最为他忧虑的则是财经界和军队的腐败问题。
财经界高官贪腐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1945年4月30日蒋介石日记)。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深感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1942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问题,用美国对华5亿元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美金公债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然而,虽有美金作底,各地人民对美金公债却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的一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者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彼时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发财的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仍可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元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竟然批准,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告诉陈赓雅,真正的分成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
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因1945年春国库局几个知情年轻人的秘密检举,最终为蒋介石知悉。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部长俞鸿钧(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部长,由原财政部政务次长兼中央信托局局长俞鸿钧继任)彻底查究。俞鸿钧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系列日记中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了问题所在。
与美金公债案几乎同时,原任部长孔祥熙掌控的财政部还发生一起“黄金加价舞弊案”。1944年3月,战时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地方法院审理。
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就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1945年5月5日,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中,孔祥熙和曾襄助孔祥熙的粮食部部长徐堪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 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孔祥熙字庸之,作者著)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 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在重庆开幕,参政员陈赓雅率先提案揭发: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以致不可究诘,构成侵蚀公款至美金1150万余元巨额之舞弊行为嫌疑。该项债票市价因之狂涨,由20元递涨至数百元,刺激物价,扰乱金融,莫此为甚”。该案共提出三笔可疑账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吕咸“借推销公债之名,签呈中央银行当局,怂恿购买美债余额3504260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当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陈赓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胆大妄为,可云罕见”,要求国民参政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孔祥熙贪腐案,同时引起了一位传奇人物的注意。他便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而他不畏强权炮轰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则为他赢得了“傅大炮”的雅号。
傅斯年从1938年起,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也来自内部的腐败,来自内部既得利益阶级的蚕食。对于政府的腐败,社会上许多人士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之所以容忍主要是不希望看到政府的垮台,从而引起更大的混乱。傅斯年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蒋介石为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性情刚烈,疾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7月15日,他在陈案的基础上又草拟了一份提案,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这份提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而是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联署者达21人。该案称: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特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
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做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 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傅先生今天发言不?”孔祥熙一直坚决否认舞弊,甚至赌咒发誓。蒋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觉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对这位与自己共事多年的老姻亲,蒋介石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复转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孔关系一向良好,认为孔“可耻之至”,这是很少有的现象。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又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组织了18个人连夜造账,以对付审查。孔祥熙甚至还向审查者出示了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7月16日,蒋介石审读中央银行的审查报告,再次召见孔祥熙。当日日记云:“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
面对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债案以及孔祥熙一再强词辩解,蒋介石深感苦恼,“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蒋介石7月21日日记)以致整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22日下午,孔祥熙又向同时调查此事的陈布雷(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表示:“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蒋介石听了汇报之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当日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最后蒋介石决定不能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颟顸”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规定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