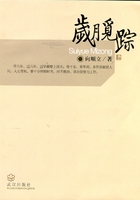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初读这句评语时,尚未明白其中深意,便已心折。后来细读《诗经》,读到“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才知这般洗练如白描的诗句,方是最动人的爱情表达。
《诗经》的“思无邪”,好比婴孩的天真任性,不可复制,无法模仿。因此,《诗经》中的爱情,少了情思的婉致曲折,少了欲拒还迎、欲怒反笑、欲语还休的缠绵悱恻,却添了几分充沛蓬勃的生命力,多了一段岁月静好的平常与安稳。
《诗经》中的男男女女,出入宫闱家室,来往城门郊野,驰骋沙场猎场,奔走乡间山林,游玩河边原野,因而《诗经》中,既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这样鲁莽生动的爱情,也有“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这般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
还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这种对远方征人的彻骨思念,更有“心之忧矣,曷维其亡”这类斯人已逝,睹物思人的悲凉情怀。
从《野有蔓草》的一见钟情、私定终生,到《雄雉》中漫长无期却从未放弃的念念不忘和等待,再到《鹊巢》中步入婚姻殿堂,为爱筑巢的圆满幸福,及至《谷风》中女子被弃的哀怨凄苦,最终到《击鼓》中难觅归期的生离死别,《诗经》将所有人间情爱,无一遗漏地挨个演绎过去。喜、怒、哀、乐,莫不直白热烈,却也蕴藉深沉。
《诗经》的这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源于先民们原始天然的心性。在那个天地初立、民心尚未开化的时代,无论下地耕作、上山砍樵,还是虔诚祭祀、合众狩猎,或是远行出征、淇水游玩,都是先民生活的一部分。《诗经》中每一场爱情的起、承、转、合,都与这些日常的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所以,先民们从不在自恋和自怜中将爱隔绝于现实,而是在原野、山川、河流边,在采摘、砍伐、游乐之中,尽情享受爱情中的美丽,同时也尽力去承接爱情中的苦恼与伤害。
相遇、相识、相恋、相知、相契、相守、相弃、相离,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成诗,爱情的每一个步骤都能拿来歌唱。这种健康的心性,是《诗经》所处的时代中最纯粹的一抹色彩。
《诗经》记载着周朝至春秋期间悠悠五百年岁月的吟哦,在经历三千年时光流转,褪尽历史繁华之后,流淌不尽的仍是那份“思无邪”的情怀。在不谈爱情、害怕去爱、算计着去爱的现代人那里,清澈纯美的《诗经》也许是一道过于理想的光。
然而,倘若能在强撑笑脸、故作坚强的疲累中,翻开一卷古老的《诗经》,沐浴温暖的午后阳光,轻轻吟诵那些简洁丰润、唇齿留香的诗句,伸出手去触摸先民们鲜活得如在目前的朴实生活,体会其中不加修饰的旋律,无一粉饰的爱恨,就会豁然开朗。原来,爱情只不过是生活,它只需要我们尽情哭笑,安然相守,最后淡然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