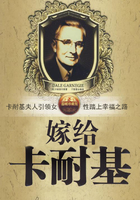童稚时候推着快乐的贩车,在春风春雨里四处游荡,是不知愁的贩者;少年时候推着梦幻的贩车,在暖风和雨时下乡闲逛,是不知世事的贩者;青年时候推着多情的贩车入城流连,是不识时艰的贩者;而中年,中年推的是期许的贩车,有豪情慷慨,有盛事伟业,在秋风秋雨里沿街兜售,是繁华世事前如醉如痴的贩者;到了老年,老年啊,风尘劳顿之余,只能推着破旧剥落的贩车,在肃杀寒风里,做一个疲倦又萧索的贩者。
南宋蒋捷的听雨词,很能把世事维艰的变幻写出来: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多少惘然,落寞,都在阶前点滴声中,滴滴溅出——情天幻海,转眼即非;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那一盏小小的灯,代表的,岂仅是贩者的颠沛、困顿?“只恐飞尘沧海满,人间 际知何限”,那凄风苦雨中昏黄的光晕,怕还透出更多千古寂寞的人生憾恨吧!
死是美丽的
死,就是去很美的地方啊!
张海迪
死是美丽的。
我写下这个题目天正下着秋天的雨。
我第一次觉得死是美丽的就是一个正值秋雨的日子。那时我约五岁半,住在医院里。那时我几乎长年住医院,住在儿童病房,等着我的腿好起来,等着回到市委保育院大班那群快乐的孩子们中间去,在那里真有说不出的快乐,我可以尽情地跑,尽情地跳,尽情欢呼,也尽情地调皮捣蛋。
一天我住进了白色的病房里,四周静极了,屋里只有两张带铁栏的儿童病床。虽然医生说我的病情很严重,可在这里我算病得最轻的。我还能坐着,从铁栏里向外张望,观望屋里也观望窗外。我还能说话,只要有护士阿姨,我就会不停地说,不停地问:阿姨,我什么时候好?阿姨,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阿姨……如果几个护士阿姨凑在一起,她们便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精神?
的确,我没有一会儿安静。我坐病床上玩腻了所有能摸得到的东西,实在没有东西玩儿了,我便拔开暖瓶盖,看着那一缕缕热气变幻着形状冒上来,飞升去。我曾期望对面床上的那个孩子跟我说话,跟我玩儿,可他却整天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发出轻轻的鼾声。他的头上缠满了白色的绷带,鼻子里插着一根细细的红色的小管子,手上脚上终日吊着盐水瓶。他的爸爸来了,他也不睁开眼睛,他的爸爸给他带来一堆花花绿绿的罐头、果子露,他还是不睁开眼睛,而那一切都让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垂涎欲滴。我们班里有个男孩子为了想吃一口罐头,故意在下雪天脱光上衣,飞跑到门口让冷风猛吹一下,回到床上很响地打喷嚏,好让自己感冒发烧打哆嗦,住进隔离室,等待吃罐头。
我的床头没有罐头,也没有果子露,我只是腿不能走路,我照样香喷喷地吃饭,可我羡慕那个孩子的罐头和果子露。于是我想叫醒他,喂,喂,你还没有睡够吗?呸,你讨厌!他叫也叫不醒,喊也喊不醒。我拿根小棍轻轻捅捅他,轻轻敲敲他,为了能够着他,我差点儿从床上摔到地上。
阿姨说这个孩子没长脑瘤之前又活泼又调皮,后来病重了,做完手术他累了,就睡着了,他正在做一个很长的梦。
他做什么梦?他梦见了什么?我不停地问。
阿姨说他梦见自己坐火车到很远的地方去,那里是个很美的地方,等火车到站他就醒了。
于是我盼望男孩坐的火车快些到站,然后他睁开眼睛,然后他跟我说话,然后他让我尝尝他那些花花绿绿的罐头和紫红色的透明的果子露,再告诉我他所看见的一切。
我每天双臂伏在铁栏上,下巴懒懒地靠在胳膊上,等待他醒来。男孩子很漂亮,圆圆的脸庞,翘鼻子,嘴巴微张着,有点儿像笑的样子,可以看见他像我一样掉了一颗大门牙。他没有睁过眼睛,我想他的眼睛一定又大又亮。每当看到他黑黑的眼睫毛眨动,我就会高兴,我就会叫他,喂,喂,你看,你看,外面下雨啦,有一只蜻蜓飞来啦!
有一天,很冷,天真的下起了雨,雨不大,发出均匀的淅沥声,屋里很昏暗,我很闷,很想哭,伏在栏杆上不耐烦,就睡着了。
忽然我听到一阵忙乱的声音,猛地睁开眼睛,看见男孩子的床边围着一圈医生。他们悄声说话,摇头,无声地收起听诊器,无声地收起病历夹,又无声地走出去。护士阿姨拔去男孩子鼻子上的红管子,拔掉他手上的吊针,又用白色松软的毛巾为他擦脸。男孩子的脸色变白了,更安静了,他的睫毛不再眨动。阿姨扯起白色床单将他全身盖严了。
为什么把他盖起来?我还等他醒来呢。我说。我不敢大声说,只是小声嘟哝,因为屋里的人都放低了声音说话。
后来,男孩儿的爸爸妈妈来了,他们给他穿了崭新的蓝色有白杠的海军服,还把一顶后面有两根飘带的海军帽戴在他缠满白色绷带的头上。然后他们悄声哭泣,哭湿了手绢。
这时来了一辆带四个轮子的平车,人们把男孩儿抱上去,推他走了。我听到更伤心的抽泣声。
看窗外细细长长的雨声,我呆呆地想着,恍惚看见那个男孩子睁开眼睛,扯下了头上的绷带,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跑上火车。长长的绿色的火车发出呼叫,轰隆隆向前开,闪亮的车窗像幻灯片一样闪过。我想起自己去武汉爷爷家就坐过火车,车窗外面真的很美,有田野,有小河………死,就是去很美的地方啊!
我的小小的心安静下来,就困了,就睡着了。
我现在所读的课程叫人生
我现在所念的大学叫做社会,我现在所读的课程叫人生。
他他
初中毕业那年,万般无奈之下,我报考了师范学校。
那时,我多么想报考高中,然后,圆我的大学梦啊!可是,我的家境不允许我这样做。父亲早逝,母亲的腿又有残疾,无法做太累太重的活计,母子俩相依为命,生存都很艰难,哪里有余钱再让我去苦读高中呢?师范学校有助学金,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可将它念完。我几乎是满含热泪,在报考专业那一栏里,填上了师范学校的名称。
那时候的我,虽然十分不甘心,但是,心中却也坚信,我此生与大学无缘了,因此,便也一心一意地去念我的师范了。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回了家乡的山村小学教书。虽然偏僻,虽然清苦,但是,与其他还在种田的同龄人比,总算是有了一个打不破的铁饭碗了,按说,也应该知足了。于是,我便在这种自我慰藉的麻木中,庸庸碌碌地过了一年。
那年7月,我接到了远方一位朋友寄来的一份西北大学作家班的招生简章。那一年我刚满20岁,但是,我的心还是活了。
刚刚走上社会的我,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揣上300元钱,背上一只旧背包,不顾母亲的坚决反对,便从东北向着遥远的大西北出发了。
20岁的我,也真够浪漫的了,见到西安,便想起了李白,便梦想着像李白一样靠写诗混饭吃,来念完这几年大学。因此,在考前准备得非常充分,几乎将老师们布置的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学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文化成绩考得相当不错,还居一百多人中的前几名呢。
可是,上作家班仅有文化成绩是不够的,还要有创作成绩。那时候,我总共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作品加在一起也不过才二三十篇,虽然还获过三次全国大奖,但是,都是中学生范畴内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样的写作水平在一百多名中只能居中游,可能入选,也可能落榜,正好徘徊在中间。怎么办?刚刚树立起来的一丝信心,难道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泡汤了吗不!不能!经过多方打探,我终于在一个傍晚,怀着一腔的悲愤,来到了中文系主任刘建勋老师的家里,声泪俱下地向他讲述了我的境遇。刘老师听后,非常受感动,他当场便表态,无论结果如何,都请我放心,有条件让我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让我上,西北大学中文系能够给我这样执著这样艰难的青年提供一片园地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就这样,我留在了西安,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我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钱。在当时,靠写作混饭吃是不可能的,一来当时的稿酬极低,写一部长篇也挣不了多少钱;二来那时我的写作水平也不高,写出的文章发表率很低,虽然我十分勤奋,但也无济于事。我从家里带来的300元钱。去掉车费、食宿费和报考费,已经寥寥无几了。
班上的一名同学得知了我的情况,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去打工,到校园外面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谋到什么赚钱的差事。我沿着大学南路,一家一家地找,一家一家地问,终于在一家小饭馆里找了一份活儿,为前来吃饭的客人写菜单端盘子。这是一份比较简单的活计,除了有的时候客人的西安话我稍微有点听不懂外,一切都非常顺利。虽然每天上午上完课我便要匆匆忙忙地奔赴那个小餐馆,身体很累时间也很紧,但是,每个月80元钱的收入,总算让我的生活有了一点保障。
可是好景不长。那天,刚拖完地,便来了一位客人,由于地面未干有水渍,我脚下一滑,一下子便摔碎了3个盘子。老板一见,大为恼火,不但扣了我当月的工资,还把我赶出了小店,炒了我的鱿鱼。我“失业”了,不得不与那可爱而又可怜的80块钱告别了。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一转眼,元旦便要到了。我从同学那里借了一点钱,到批发市场上批发来了一大批贺年片,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园内摆了个小摊叫卖起来。在当时,勤工俭学的学生还少,竞争并不激烈。偌大的校园中,大学生们贩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可是,贩卖贺年卡的却只有我一份儿。那段时间里,我的收入相当不错。我不但为自己买了笔、本等文化用品,而且,还用挣到的钱为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也算是一种较为奢侈的自食其力了。
自那之后,我卖过衬衫、卖过袜子、卖过手套,帮人站过柜台,替人看过小孩……可是,每一种工作都没能干长远,不是不赚钱,便是老板过于苛刻,或者是人家嫌我过于木讷。就这样,我饥一顿饱一顿,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不畏艰难的精神,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
一转眼,又到交学费的时间了。
那时候,读西北作家班每年的学费是1 800元,其实并不算贵。可是,对于我来说,那已经够把我吓昏过去了。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能够糊口就不错了,根本帮不上我,而我自己呢,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没有盈余,甚至有的时候,连生存都很成问题。那么大数目的一笔钱,让我上哪去弄呢?我思来想去,终究还是无计可施。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根本就没有力量来完成我的这份学业,我的大学梦,也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是无法变成现实的。回到我的小山村,继续做我的乡村教师,是我最初的起点,也是我最后的归宿,我的梦想发自那里,也止至那里。
我又回到了那所学校,重新做起了我的老行当——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虽然我的大学梦破灭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我仍然意气风发地在另一所大学里,读着我的课程。
一个人生活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我相信最终我们都将走向统一的终点。念不念大学,我们同样都能取得成功。
我现在所念的大学叫做社会,我现在所读的课程叫人生。
平 凡 人 生
生命仅仅是一个过程,一个转瞬即逝的过程,短暂得如天穹中一颗消隐的流星。
丁宗皓
生命仅仅是一个过程,一个转瞬即逝的过程,短暂得如天穹中一颗消隐的流星。
关键在于我们在身后能留下什么?
哲学家留下了深邃博大的思想,多少年过去了,世界依然被他的言语笼罩;诗人留下慑人心魄的情感;诗人陨落了,诗句却为世人吟诵;伟人在身后留下了一座丰碑,上面镌刻的是生的伟大、是业绩的辉煌,丰碑太高,高得使人只能仰望;英雄在一刹那留下了果敢与坚强,留下了情操与人格,使世人为之闪动的是点点泪光……我们可能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平凡得如路基下的一粒石头。然而我们不能抱怨,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本来就无法选择母亲、选择职业……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在平凡的时光里,让思想、情怀、品格盛开成三月如诗如画的原野,在寂寥的人生之路上,唱一支热烈而充实的歌。认真地爱一切值得去爱的一切,恨一切必须去恨的一切。因为我们平凡,我们才可以自由地伸展一如粉红色的牵牛花;因为我们平凡,我们才可以认真地度过这平静的每一天,在平凡的土地里播下不平凡的人格与操守,尊严与责任的种子,在人群里,习惯默默地承受痛苦,默默地奉献情感,默默地改造着环境,默默地让生活充满友爱和信赖。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丰碑躺倒在原野上,而小草又一年一度欣欣向荣。可能我们的生命尚不如原野上的草,但我们绝不遗憾:我们曾真诚地生活了。
我们正真诚地生活着。
生命需要什么
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脏!
刘燕敏
利奥·罗斯顿是美国最胖的好莱坞影星,他腰围6.2英尺,体重385磅。1936年在英国演出时,因心力衰竭被送进汤普森急救中心。抢救人员用了最好的药,动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仍没挽回他的生命。临终前,罗斯顿曾绝望地喃喃自语:“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脏!”
罗斯顿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在场的哈登院长,作为胸外科专家,他流下了泪。为了表达对罗斯顿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提醒体重超常的人,他让人把罗斯顿的遗言刻在了医院的大楼上。
1983年,一位叫默尔的美国人也因心力衰竭住了进来,他是位石油大亨,两伊战争使他在美洲的十家公司陷人了危机。为了摆脱困境,他不停地往来于欧亚美之间,最后旧病复发,不得不住进来。
他在汤普森医院包了一层楼,增设了五部电话和两部传真机。当时的《泰晤士报》是这样渲染的:汤普森——美洲的石油中心。
默尔的心脏手术很成功,他在这儿住了一个月就出院了,不过他没回美国。苏格兰乡下有一栋别墅,是他十年前买下的,他在那儿住了下来。1998年,汤普森医院百年庆典,邀请他参加,记者问他为什么卖掉自己的公司,他指了指医院大楼上的那一行金字,说:“利奥·罗斯顿。”
不知记者是否理解了他的意思,总之,在当时的媒体上没找到与此有关的报道。后来我在默尔的一本传记中发现这么一句话:富裕和肥胖没什么两样,都不过是获得了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
也许,这就是答案。
人生第一课
这次外出,只知道是去度生活的艰难,却还不知道人生的悲哀。
那年我才十二岁。
韶华
我小时候,华北连年荒旱,颗粒不收,活不下去了。
父亲背着一个褡裢,手拿一根打狗棍,在前面走;我则只拿着一根打狗棍,在后面跟。我父子二人是去远方讨饭的。在这以前,除了串亲戚,我还没有出过远门。这次外出,只知道是去度生活的艰难,却还不知道人生的悲哀。那年我才十二岁。
第一天,我们走四十里路,天黑时,到了一个叫作“两门镇”的大集市,找了一个住一夜只要两个铜板也只提供平地上铺一层草的小客店,住下了。外面的大街上卖饭食的小贩高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