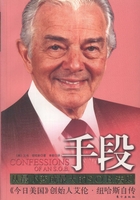我依旧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自己在心里设想,那样一份梦寐以求的礼物会如何地出现:
我希望是一位不知名的朋友,从遥远的地方寄给我一个严严实实很神秘的包裹。然后,我一层一层地打开,就在我快不耐烦的时刻,会有一只精美的音乐盒呈现在我面前。
甚至,我不惜捕来童话里的人物。想像着会有一个穿白纱裙的小仙女,趁我睡觉的时候,在我的手心里放上一颗榛子。
等我敲开它的时候,就会蹦出一只小巧的音乐盒来。
可是,无论我的想像是多么的精彩,一切却平淡如常,什么奇迹也没有。除了妈妈在圣诞节的清晨拎着我那在床头挂了一夜却还是软瘪瘪的长袜子,告诫我以后不许乱放东西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更不用说什么神秘的包裹、小仙女的榛子了!
17岁的时候,我的音乐盒依然如同灰姑娘的水晶鞋一样,遥不可及。
直到有一天,有个男孩子抱着一只大大的纸盒走到我面前。他一边忙着打开盒子,一边满脸认真地对我说:“我建议你留起一头长发,那样比较像女孩子!”
我生气地瞪了瞪他,走到镜子面前,忍不住伸出手梳了梳乱糟糟的短发。
身后,响起动听的音乐。转过头去,桌上一只很别致的小盒子正对我唱着歌。走过去看着它,想起从前的渴望,忍不住轻轻笑了。
它多像是一个青春的盒子呵!盒子里满满地装着年少时那些绮丽的梦。每一个,都像那飘飞的音符,动人而美丽。
最后串成一支青春的歌谣!
而送给我那只盒子的人,是我的弟弟,他无意中看到了我很久以前的日记……
拥 抱 太 阳
拥抱太阳,战胜未来。我们的双臂荡起雄风,历史的长廊将永远地回响……
宋绍荣
21世纪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不是在遥远万里的天地交界,不是在苍茫浩渺的大海远处。每当我们揭开一页崭新的日历,都感到它的光瀑已倾泻在心灵之窗。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青春的热血怎能不加速奔流,激荡的思绪怎能不升腾起现实的梦想!真恨不得顿生双翼,飞跃时间和空间,去拥抱现代化的太阳。
夸父逐日,竭泽而死。古代神话将自信心扩张到了极点,也难以比拟我们的焦灼,我们的渴望。
——去挥动虹彩的画笔,按着祖国的构思,描绘栖凤的亭台和飞檐的楼群,点染花果的笑容和稻谷的芳香;——去架设科学的云梯,探究浩瀚的银河,让每一颗星辰都闪烁中华儿女的智慧之光;——去铺筑金色的路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轨道上为改革开放的列车插上腾飞的翅膀……多少事,从来急。21世纪凯旋门的宏伟工程,历史地放在我们肩上。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开拓者,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要把太阳紧紧搂在怀里。太阳是真理的挚友,真理是思想的太阳。用太阳的光束编织我们的思绪,让信仰的旗帜激溅出劳动与创造的光焰,向全世界展示光明事业的灿烂辉煌!
拥抱太阳,奔向明天。我们的足音踏着节拍,时代的花蕾会应声怒放。
拥抱太阳,战胜未来。我们的双臂荡起雄风,历史的长廊将永远地回响……
将芳年写在心灵
那么,将打扮外表的时间剪一段吧,用来塑造一个崭新而充满活力的心灵世界。
艾明波
我们匆匆地踏上了人生的旅程,便接受了世事的风雨。于是岁月操起了无形而尖利的刻刀,用沧桑和无奈勾勒着你心中的世界以及你的容颜,于是人们拒绝衰老,痛恶衰老,不遗余力地讨各种良方驻守芳年。
为了打消青春不再的苦恼,为了打扮如花似玉的容颜,有些人不惜代价将青春涂抹在自己的脸上,让花花绿绿的化妆品抹平岁月之痕,然后对着镜子说:我真年轻。
更有些人将青春穿在自己的身上,似乎一两件高贵的服饰足以抵挡时光的流逝和肌体的萎缩。
有一种善待青春的美好这固然可贵,而如流的光年却不能停留在生命的某一个章节,成为永恒的骄傲。季节会不断地更迭,人终会衰老,稀疏的白发并不因我们极力地拒绝而远离我们的额头。与其说芳年写在脸上与身上,不如将它写在心灵,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即使时间在晚上犁满辙印,那么生命也会繁荣与蓬勃,只要希望不会老去,那么就会芳华永驻。
如果将所有的时辰用在雕琢于外表上,未免太负生命了,因为生命灿烂的鲜花不仅仅是它的外表而是它所能给予人间的创造以及这创造的不朽。
那么,将打扮外表的时间剪下一段吧,用来塑造一个崭新而充满活力的心灵世界。
自己写在脸上的作品终会随时光暗淡,而写在心灵与历史的作品才会光照后人——因为,岁月终会凋谢容颜。
我 仍 纯 洁
一个孤独的农村弱女子,终于拥有一扇很小很小的窗口看外面很大很大的世界了。
罗西
一个漂亮女孩的故事
认识郑春梅,是缘于这么一件事: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匆匆经过福州花巷时,有个长得很帅的男孩向她“求爱”,她不搭理,继续走她的路。那小伙子貌似正派人物,实际上是个流氓,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掏出匕首,要郑春梅陪他去一个地方玩……郑春梅想,今晚是撞上真鬼了!也好,趁机“实践”一下刚刚学的几套武术招式,原来她刚从武术教练康先生家出来。想到此处,郑春梅飞脚一踢,再加一记疾拳,便把对方制服在地上,很快就把那家伙扭送到派出所。
因此事,郑春梅的名字登报了。她的名言是:与色狼没有外遇!敬佩之余,我前往采访这位有个性的女孩。要拍照时,她婉拒了,理由是:我不是英雄。
很小的时候,有人就捧着她称她是“小公主”。实际上,她来自闽北的连城,地道的农家妹子,家道贫寒。
县职业高中毕业后,她开始陷入苦恼:学的是装潢设计,可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很少有机会派上用场。一天,郑妈妈说:梅梅,要不找个对象,看看行不?母亲的心情,她明白。一个无依无靠的农家女子,惟一的出路就是找个好夫君,从此一辈子生活有了保障。但那似乎又不是幸福。春梅常在心中暗暗比照两个公众人物,那便是周洁和宋祖英,一个跳舞的,一个唱歌的,她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红透了半边天。而她们最初又都是农家出身,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走向人生的辉煌。这一切,令春梅好生羡慕。
春梅想去大城市一试身手,于是她来到广州,成了一个又激动又怯生的打工妹。经一个同学的姐姐介绍,终于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歌舞厅当“跑堂”。这位同学的姐姐笑着对她说:多亏你有张好脸蛋。她感激地笑了笑,而心里却在说,是的,但这不是我最后的王牌。
这一夜,春梅为一个城市的灯海而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孤独的农村弱女子,终于拥有一扇很小很小的窗口看外面很大很大的世界了。
她很快适应了自己的工作,她心里也很清楚,在这种地方,鱼龙混杂,自然得多几个心眼。
春梅在一天天成熟起来,动人的微笑,轻声的问候,温馨的招待,常令一些“倾心”的男人自作多情。为了保住饭碗,为了不改初衷,往往要应酬得有礼、有节、有理,还要天衣无缝。她和几个姐妹关系不错,常常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往往若一个被缠,另一个便会上前通报:“请去账台”或“老板请你去一趟”……一次,有个不三不四的男人,拉着春梅的衣袖说:“小姐,陪我喝几杯。”情急之下,春梅指着一旁沙发上的两个小伙子说:“先生对不起,我的男朋友在那边,另一个是他的同学……”趁那男人发愣的时候,溜之大吉。
那两个小伙子很面熟,是大学生,这儿的常客。事后,春梅红着脸走近他们,想解释一下,并表示歉意。那个被她指为男朋友的男生,站起来说:“没关系,人在江湖嘛。其实,我也早想做你的男友。”一句幽默的话,不再令春梅忐忑不安,她坐下来与他们闲聊了一会儿。
这男生姓李,山东人,平头。他是自费上大学的,他本想在这个假期出去打工,找点感觉什么的,最终什么也没找到,便常到春梅所在的歌舞厅来玩。
很快,春梅把初恋全给了李。感情这东西很怪异,春梅接受他的爱,也仅仅因为他皮肤黑,而且是山东人。后来才知,李家很富有,他父亲与韩国人合作经营一个公司。
但最终,李离她而去,他要她做他的情人,仅此而已。李说,他们之间有距离,城乡距离、文化距离,这两种距离如果存在于情人间,那是美好的,如果放在夫妻间,那就危险了。
“到头来,原来仅仅让我做情人!”郑春梅愤愤不平地说。她不解也不甘,为什么漂亮的一定当情人?她说,我还有贤慧,还有能干,还有许许多多的好品质。
在一个阳光暖人的下午,她平静地送李上了飞机。春梅尊重爱,但也遵循一个信念:不做情人。随后,她去了福州一家大酒店当公关部经理。这次是她自己真正的选择。
在工作中,常有人恭维说:“小姐,你好漂亮好迷人。”春梅只好客气地说:“谢谢。”但她心里却一遍遍地说:美丽是重要的,但尊严更可贵。她有一个朋友是做秘书的,这位小姐说过这么一句话,只做秘书不做情人。公私区分得眉目分明。春梅很是敬重这个小姐妹。一天,春梅的几个伙伴,指着一本杂志里登的一则征婚启事笑作一团,原来这则启事的内文里有这么一句话:本人,处女……有人说,这个时代还强调自己是个处女,未免令有些人贻笑大方。但春梅却不以为然,她心想,我也是个守身如玉的女孩,我无愧而且骄傲,因为我也是一个处女。她觉得做个女人,并不难;做个好女人,也容易,因为这更容易激发你去克服困难,也更有理由激励你一往无前。虽说漂亮的女人可以多一些机遇,而一个不漂亮的女人,则可以少一些麻烦。她觉得这个世界是公平的,重要的是如何把握自己。
白色,青春的殊荣
白色,无忧无虑的标志,青春时代的殊荣……
李芳
夏季,色彩的季节。衣饰缤纷,溢彩流光,而年轻人总是其中的主力军。按照通常的理论,艳丽绚烂是青年人的特权,甚至是义务——试想,倘若有一天年轻人都不穿那些美丽的颜色了,这个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没法儿看。夏日炽热,衣裙亮丽,世界充满阳光。
而我却在这个夏季怀念起白色来……大街上,五彩人流里悄然飘来一抹白色,仿佛一位自甘寂寞的美女,幽然吐出那遥远的清纯气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关于白色的记忆,至少,少年时代的白球鞋、白衬衫,还有“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白是一切颜色的底色,它像“人之初”的“善”,或者刚刚出生的婴儿,它的魅力是难以抗拒的。
所以,在单纯如白纸一样的读书时代,我的衬衫是白的,裤子是白的,连衣裙、鞋、袜子也是白的,甚至连钢笔、日记本封面以及头上扎的蝴蝶结统统是白的……走在街上,昂着头,满不在乎地迎接人们的注目,真像一只骄傲的天鹅。
小学,中学,大学,我都是一身素洁度过的。不论做什么衣服,当妈妈问我要什么颜色时,我几乎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白的!”
结束读书时代,我被扔到乡下做了教师。当我第一次一身洁白走在窄窄的街道上时,四周投来的目光几乎将我吞掉,这目光,使我感到孤独,平生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与环境不协调。
当了教师后,和粉笔交上了朋友。每当一节课讲完,全身都沾满了灰白的粉笔末,此外学校条件差,得生火炉自己做饭,如此一来,几乎用不了两天,我便由“白衣少女”而变成《水晶鞋》中的“灰姑娘”了。尽管我疲于洗衣,但衣服总不免要变色,白色实在是经不起任何污染。
半年之后,我不再穿白衣了,取而代之的是上下浑然一体的黑色,尽管我仍挚爱着白色,但实在厌烦了洗衣的忙碌和不必要的引人注目。
我不是爱走极端的人,只是感到让白色保持本色太不易了。
时隔几年?白色对于我已经遥远。“白衣少女”的时代,我万不会想到,生活与我喜欢的白色竟然会是冲突的!在我心中,只有那么一丝不变的记忆……白色,无忧无虑的标志,青春时代的“殊荣”——我不知道衣服颜色变化是否与思想有关,反正此后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失掉了以前的单纯和明朗,变得神秘了,我不想承认,因为我还不想过早的成熟。
人人都有少年时
我是个聪明的孩子,却并不擅长运动,我的朋友们也都跟我差不多。
我们从来都作观众——不论是哪种男孩子们的运动。
徐倩秋/译
我们先是听到“砰”的一声,接着是一阵呻吟。我和妻子赶紧冲出门去,发现我们12岁的女儿躺在车道上,一条腿在身子底下。
当天的早些时候,因为她所犯的种种“罪行”及拒不认错的恶劣态度,我们决定把她关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关门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嘴唇紧紧地抿着,眼中射出愤怒的目光。后来,出于一种反抗情绪,她想从窗户爬出来,结果却摔了下去。幸运的是,只扭伤了脚。
“好了,这下她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到处惹祸了。”在从诊所回家的路上,妻子长吁了一口气说,“而且,我想她得到了教训。”
我从后视镜里观察着女儿。还是那对紧抿着的嘴唇,还是那种反叛的眼神。“我们也得到了教训”,我说,“那就是我们的孩子成了个小疯子。”
“我不是疯子。”后座上一个声音咕哝着。
“好,那么你说,一个毫无理由就从二楼的窗户往下跳的人是什么?”我反问。
那天晚上,妻子对我说:“我能理解你很生气,但你不该那么说她。”
“我想,我有权利这么说。”我答道:“她做的事,只有发了疯的人才做出来。她可能会摔破脑袋或摔断脊椎。然而对我来说,更可怕的是,我想她根本没意识到,她可能从此就变成一个残废。”
我心里乱糟糟的,不想再谈下去。于是我独自走出家门。想好好想一想。可我想得越多,心里就越乱。
“女儿到底怎么了?”我站在一条宽大的马路旁问自己,一辆辆汽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我忽然意识到,我那12岁的疯疯癫癫的女儿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冲进那几乎没有间断的车流中去。
突然,一件早已被忘却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12岁——不错,正是12岁。
我12岁时,我们家住在纽约市的东鱼克林区。我们一伙男孩子——大约五六个,每天放学都乘地铁回家。
我是个聪明的孩子,却并不擅长运动,我的朋友们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从来都做观众——不论是哪种男孩子们的运动。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自己创造了这种游戏。我们叫它“海岸线大赌博!”每天放学回家时我们都要玩一遍。
铁路在布鲁克林区的大部分线路都是在地面上架设的。坐在车厢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铁路两旁的一切。站在站台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列车在半英里外的前一站徐徐启动。
这就是游戏开始的信号,我们大家马上跳下站台,站到铁轨上,把双手支在齐胸高的站台上。我们就这样站在那儿,喘着粗气。盯着逐渐向我们驶来的列车。然后,我们一个接一个爬上站台。最后一个上去的就是胜利者。
我总是输。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失败者的群体里,我也是最糟的一个。有一天,我发誓一定要赢,尽管吓得要死,我也还是坚持了下去。
火车越来越近,其他的孩子陆续爬上了月台。火车只有半个街区远了,我的最后一个对手也放弃了。当火车开始鸣响汽笛的时候,我用手在站台上一撑,准备爬上去。
可是,我的肩膀突然抽筋了。我狂乱地向朋友们呼救,但是火车的汽笛声掩过我的叫声。“你赢了”,我看得出他们在说,“还想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