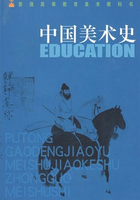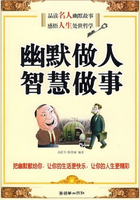(一)米芾所处的时代
米芾出生于1051年,那时距北宋王朝的建立(960年)已过了将近百年,距宋王朝南渡(1127年),还有七十余年,这时是北宋王朝的相对繁荣时期,同时也是暗流涌动的变动时期。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是比较高的,一方面,文教政策比较开明,导致宋人在文化方面富于怀疑、创新、开拓精神;另一方面,国势的不振也使整个社会心理缺乏像唐代那样有向外开拓的气度,而是倾向于向内退避,来寻求心灵的自适,特别是文人的大量出现,更助长了这种精神。文艺是和心情有关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劳心费力的心灵,总是需要一方净土来栖息悠游,所以当人们真正从事艺术活动时,那些政治的和道德的说教,就成了九霄云外的缥缈之物了。大家游戏笔墨,不问工拙,但求适意,其乐融融,营造了中国美术史上一段颇为轻松而讲究味道的时期。米芾就是其中极为“艺术化”的一位。由于处在官僚集团的边缘,他没有那么重大的政治道德责任意识,也就不必满口仁义道德、经国治世,他能够以相当纯粹的游艺态度从事书法绘画艺术,从而集中地展现了宋人意态纷呈、精微澄澈、优游自适的风貌。
(二)米芾的政治生涯
与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不同,米芾的身世是比较特殊的。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宋初的勋臣米信是他的五世祖,高祖、曾祖以上又大多是武职官吏,而不是以诗书传家的高门,他的父亲米佐,开始读书学儒,官至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县)公,一生业绩并不显著。他的母亲阎氏,曾是英宗皇后高氏的乳娘。米芾幼时,就生长在皇亲国戚的豪华邸宅中。据说米芾自幼聪慧,6岁时日读律诗百首,过目一遍便能背诵;七八岁时学习颜真卿书法,能作大字;10岁时写碑,旁人称赞他有李北海的笔意,他还不以为然。由于母亲的关系,米芾凭借皇室的照顾踏上了仕途,而非通过考试。但这种“幸运”实际上蕴涵着很大的后患—在以文人集团为主体的北宋官场中,这样的出身是被视为“冗浊”的,不仅会耽误许多升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强烈的异类感会深深地刺痛米芾敏感的神经!可以说,这种仕进影响了他的仕途,并进一步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生活。
在米芾18岁时(1068年),高后之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高后贵为太后,念及阎氏的乳褓旧情,不久,就“恩荫”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这是米芾的第一份差事。此后,他几乎每两年换一个地方,担任辅佐官职,从1071年到1089年将近二十年的宦海生涯,谈不上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就,这或许就是“出身冗浊”的负面效应吧。所以他在东坡《木石图》的题跋里说:“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有颇多的感叹。1097年米芾受命主持涟水军(江苏),但他对政务的重视程度似乎降低了,他把涟水当成了寄情翰墨、游戏艺术的宝地。涟水有很多奇石,这正投米芾所好,野史记载说,他一到任,即大量收集奇石,并一一加以赏鉴命名,有时整天藏在书房,足不出户,以致公务荒疏。
有一次,朝廷管司法和官吏考核的按察使杨次公巡视到涟水时,对米芾严肃地说:“朝廷将千里郡县交给你,你怎么能终日玩弄石头呢?”米芾从左袖中取出一块灵璧石,嵌空玲珑,峰峦洞穴俱全,色极清润,在手中翻转并抛给杨按察使看:“这石头怎么样?”杨不看,米芾将石头纳入袖中,又取出一块石头,叠峰层峦,奇巧得很。杨仍然不看,米芾又纳入袖中,最后取出一石,极尽天画神镂之巧,看着杨说:“这种奇石,怎么能不爱呢?”杨忽然开口道:“并非只有你爱,我也很喜欢它。”他从米芾手中抢过这块奇石,径直登车离去,也不再纠缠米芾的“失职”问题了,米芾这才逃过考核一劫(《宋稗类抄》卷之四《放诞》第十四条)。然而用这种方式在仕途上行走,的确很难得志。
本传还说他“尝奉诏访《黄庭》小楷书作周兴嗣《千安韵语》。又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人以为宠”。野史记载宋徽宗多次召见米芾书写屏风。宋徽宗本人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书法家,他所创造的“瘦金书”,风格独特、气质典雅。能够得到宋徽宗的肯定,这既是艺术的成功,也是政治的成功。米芾当然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有一次写了一首五绝:“目炫九光开,云蒸步起雷。不知天近远,亲见玉皇来。”深得皇帝赞赏。但另一次,却不太高明了,宋徽宗与蔡京在一起谈论书法,大概谈到了米芾,徽宗兴之所至,即命召米芾入朝当面书写一大屏风。米芾空手而来,徽宗即指御案上的笔砚,让他使用,米芾当着满朝君臣,反捋袍袖,大笔挥洒,笔走龙蛇,从上而下其直如线,宋徽宗看后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大加赞赏。米芾看到皇上高兴,待其书毕,即捧砚向徽宗跪道:“此砚经臣米芾濡染,不堪皇上再用,请赐予臣米芾。”徽宗皇帝看他如此喜爱此砚,又爱惜其书法,不觉大笑,将砚赐之。米芾得了御砚,喜不自胜,遂拜谢皇上,随即将皇上心爱的砚台装入怀中,抱着砚台跑了出去,墨汁四处飞溅,弄得墨渍沾满襟袖。表面看来,这有点恃宠的迹象。然而,他的作为给宋徽宗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徽宗对蔡京说:“这米芾,‘颠’名不虚呀!”这显然是不利于仕进的一个评价。蔡京对米芾不错,大概是想为他加强点正面印象,所以回奏说,米芾的人品确实高,可以说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后来的情况是,一年后,米芾获得礼部员外郎的任命,有进一步上升的势头,但这立即招来了反对,理由非常直接—一是他“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二是他“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
从以上的简单介绍来看,米芾一生在政治上是不算成功的。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米芾不是道学家,立德谈不上;他一生这样的经历,也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至于立言,如果宽泛地理解,以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倒似乎可以沾点边—但书法在宋代以后,不过是文人的雅好而已,还够不上“立言”的高度。但是,在中国古代重视“德艺双精”的传统下,以他这样极不出色的政治、道德、文学建树,竟然能够跻身于“宋四家”、创造“米家山”,更说明了他在书画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和突出贡献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三)米芾的精神世界
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四《题所得蒋氏帖》中说:“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生平。”大概反映了米芾在政治上的抱负与艺术志趣之间的矛盾心态。米芾的“颠”,集中反映了他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了解他的“颠”,也就了解了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他的“颠”。
首先,米芾之“颠”,不是为颠而颠,而是他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宋史》本传讲他“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甚至连毛巾也不用,两手相互拍干。米芾挑女婿也按着自己的洁癖来,上门求婚的人里面,有一个南京人叫段拂,字去尘,米芾一看就高兴了:已经拂过了,还要再去一下尘,绝对是讲卫生的人,这才是我的女婿,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这个人。而他的洁癖,更多的是表现在对待书画艺术的态度上。他对艺术是真正的投入,所以不能容许有一丝一毫的玷辱。《宋稗类抄》卷《古玩》第四十二条载有他因好洁而不惜弃去心爱之物的故事:有一次,米芾得到了一块珍贵的玛瑙砚,他非常高兴,约他的好友来,向他夸耀说:“你看我最近得到了这个稀世的玛瑙砚,很美吧?”朋友知道他有洁癖还特地用手帕擦擦手,再拿起砚台观赏,边看边点头说:“这砚从外形看来真的很美,但不知道发墨如何?”米芾立即叫仆人拿水过来,才一回头,这位朋友已经等不及地吐了一口唾沫在砚上,拿了墨块就磨起来,米芾很不高兴地说:“你刚刚还晓得擦了手再拿砚,怎么现在往上面吐口水呢?这砚已经弄脏了,我不要了!送给你吧!”无论如何,他也不肯再收存了。
这样的表现,来源于米芾对精神生活“纯粹性”的一种坚持,而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习惯的“洁癖”。《清波杂志》记载,米芾的亲友偷看过他写信,结果看到他写“芾再拜”这句客套话时,竟然放下笔,恭恭敬敬地拜了两拜。这是最真实性情的流露,这种痴很纯粹,是一种坚持,这是米芾“颠”的第一层。
其次,米芾的“颠”,又是他展示、强调“文人”气质的手段。
他需要比一般的文人显得更文人,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宋史》本传称米芾“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这是米芾为自己设计的形象—唐人的衣冠,这当然是出奇的。1087年他刚服完母丧到汴京,每次出门都要撤去轿顶,戴着高檐帽,招摇过市,非常引人注目,晁说之称他像朝廷刚刚俘获的西羌首领“鬼章”。《蔡志》也说他“冠服用唐规制,所至人聚观之。视眉宇轩然,吐音鸿畅,虽不识者亦知为米元章出”。米芾不穿戴当时的服饰,而是穿戴前代的衣冠,他的出奇,终于达到了目的。
米芾一生还非常喜欢把玩异石砚台,有时到了痴迷的程度。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所爱之石,定非凡品,并开创了玩石的先河。据《梁溪漫志》记载:他在安徽做官时,听说濡须河边有一块奇形怪石,当时人们出于迷信,以为是神仙之石,不敢妄加擅动,怕招来不测,而米芾立刻派人将其搬进自己的寓所,摆好供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口中念念有词:我想见石兄已经二十年了,相见恨晚!此事日后被传了出去,由于有失官方体面,被人弹劾而罢了官。但米芾不怎么感到后悔,后来还作了《拜石图》。作此图的意图也许是为了向他人展示内心的不满。元代的倪瓒《云林诗集》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不虚得。”后世画家也喜欢绘制《米颠拜石图》,拜石一事,遂更喧腾人口,传为佳话。李东阳在《怀麓堂集》时说:“南州怪石不为奇,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两膝不着地,石业受之无愧色。”这里可以看出米芾对玩石的投入和其傲岸不屈的刚直个性。大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情怀。
据说米芾的死也很离奇。死前一个月,米芾就安排后事,跟亲友告别,把他喜欢的字画器玩全部烧了,就像知道自己要死一样。米芾还准备好了一口棺材,饮食起居全在棺材里。死前七天,米芾洗澡换衣服、吃素焚香。别人看他做作惯了,就由着他的性子闹。死的那天,米芾把亲戚朋友全请来,举着拂尘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说完扔掉拂尘,合掌而死。
再次,米芾之“颠”,还是他释放、表达自己艺术感受的一个途径。作为一个敏锐的艺术家,米芾的情感是丰富而热烈的,艺术判断是独到精深的,有时他口出狂言,单刀直入。《海岳名言》中记载:“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襄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看起来,米芾对其他的书家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即使对他所敬重的苏轼也没留什么情面,真是一个不能“随世俯仰”的人。但却不能不说他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这样的评论,普通人看着是“颠”,而在专家眼里,却是真知灼见,至少其中不乏重要的艺术判断。
由以上种种轶闻趣事,不难看出米芾是无愧于“米颠”二字的,但仔细分析起来,米芾的“颠”又很值得推敲。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群体构成来看,米芾不能完全算是主流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带有许多隐者的特点。换句话说,米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有一定的边缘性。“颠”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待这种边缘性的策略,其目的很大一部分是强化自己与主流知识集团的联系。但有趣的是,这个策略只是达到了精神上的效果,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却反而强化了他自己的这种边缘性。当然,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历史的幸事,由于他的“颠”,米芾提升了自己人生与艺术空间的自由度,从而得以较大程度地保全自己的纯真天性,得以充分展示自己所具有的文人素质,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多姿多彩,使自己的艺术道路、风格选择与众不同,最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面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人选择的对与错,今人又怎么能说得清呢?但话又说回来,历史上的怪人数不胜数,而米芾之所以能永载史册,终究是因为他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他的书法,自成一体,为后世所珍视;他的画,别开生面,被誉为“米家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