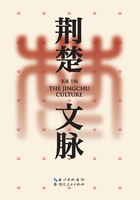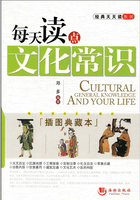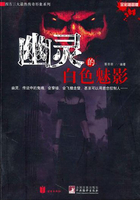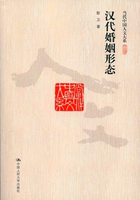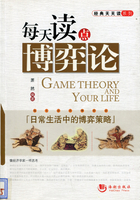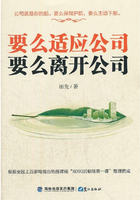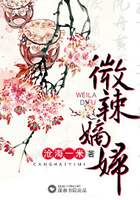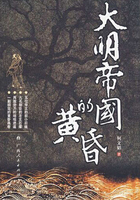西周晚期金文,长篇更多,其中毛公鼎达四百九十七字,是迄今发现的最长金文。这时金文多反映战争及社会动乱。随着周王朝的衰落,有些金文也趋于简单,例如梁其诸器,就出现一些脱漏错讹,这在早中期金文中是罕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这一时期铁器渐渐出现,青铜铸造的乐器也增多了,在青铜乐器上铸文成为可能,因此金文所录的内容,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只记录王公大臣贵族阶级的事,像战功、音阶等,这些都有了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个别刻成的铭文,在铭文中错金也有发现。北方晋国逐渐流行一种笔画头尖腹肥的字体,可能即汉晋人所谓“科斗文”;而南方各国则流行以鸟形作为装饰的美术字体,即所谓“鸟书”,这两种特殊字体都流传到战国早期,有的在汉代还有孑遗。南方各国金文多刻意求工,用韵精整。
战国早期金文基本继承春秋时的统绪。由于诸侯分立已久,文字的地方性更为突出,形成《说文》序所说“文字异形”的局面。大体上说,西土的秦和东土六国分为两系,而东土又可分为三晋、两周、燕、齐、楚等亚系。各系不仅文字结构诡变不同,金文的用词和格式也有许多差异。战国中晚期,金文以刻成的为主,内容转为“物勒工名”的形式,即记载器物的制造者、使用者、置用地点、容积重量等,有的还用干支、数字作为编号。此类金文有助于研究当时职官、地理、度量衡制等,也有很大价值。
与此同时,还有少数传统形式的铭文存在,并且有长篇的。例如战国中期末的中山王方壶铭四百四十八字,中山王鼎铭四百六十九字,内容记中山乘燕国内乱、齐国进军占领燕都之机,举兵伐燕,取得大片土地。这是文献所缺书的重大史实。
中山王三器蕴涵丰厚的文化价值。
战国时期的中山,即春秋时期的鲜虞,本是戎狄部落的一支, 1974年以来,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重要遗址,遗址坐落在平山县三汲公社东灵山和西灵山的南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圆壶合称中山王三器。中山王三器行文流畅,文字精美,风格独特,是中国古文字的精品奇葩。铭文以中山王鼎最多,也最精美。铭文为刻款,体现了华美的书写风格。其中中山王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是1977年在西灵山一号大墓中出土的,鼎为铁足刻铭铜鼎,周身刻铭77行,计469字。鼎系中山王十四年铸,是用以赏赐中山相周的。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圆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 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中山王鼎铭文字数之多,仅次于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更属罕见。铜鼎铭文的风格,接近三晋文字,字体修长,匀称流美,装饰意味十分浓厚,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中山王圆壶为中山王的嗣王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除歌颂先王的贤明外,还大加赞扬相邦马赒的内外功劳。此壶及其铭文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中山王方壶,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朝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添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 ,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
铭文大约刻于公元前314年,是迄今发现的第三长的铭文。记录了本壶的制作时间、用料动机等情况。把先王值得赞美的功业和事迹刻在壶上,以显扬先君光辉的德行。 把燕国国君子哙仿效尧以国禅让子之所造成的国亡身死、卒为天下耻笑的教训也镌刻在壶上,以告诫继位的君王。表彰相邦“竭志尽忠”地辅佐中山王璺“协理国事”,早晚不懈地举贤荐才,任用能人,为中山国开拓了疆界等辉煌功绩。
秦代金文一般均为“物勒工名”之类。具有特色的是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的诏版、诏量、诏权,有的还加有秦二世胡亥的诏书,称为两诏。
汉代金文沿袭秦代传统,而在格式上更为规整统一。已经发现的汉代金文数量很多,容庚在20世纪30年代编写了《秦汉金文录》和《金文续编》,其中汉代金文占主要部分。此后新出的又不止数倍。考古发掘还发现有成批成组的有铭青铜器,对研究汉代各种制度很有意义。特别是金文中的职官如与汉印结合研究,将会起较重要的作用。
(四)金文的制造过程
把文字“写”在坚硬的金属上,并且还要写得漂亮、传神,一想起来就觉得颇有难度。更让人费解的是,殷周金文经常可见是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这更加让人匪夷所思了。专家推断,青铜器上的字应该首先被刻在铸模上,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大致如下:
1. 利用黏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同的土胚(模型)。
2. 另外再用黏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黏土,作为外模。
3. 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
4. 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
5. 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6. 将已熔化的铜注入。
7. 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但是,还有一个让人不解的地方,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进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怎样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仍然是一个谜。对于加上这些凸出来的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1.将熔成泥状的黏土,逐渐贴上。
这是清朝金石学权威阮元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2.在内模贴上薄黏土,再削去多余部分。
这是民国以前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这样在青铜器上也会留下印记,然而实际上并没有。
3.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黏土填满后,再将黏土移印至内模上。
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做假设。
(五)金文研究著作
我国对金文的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张敞曾考释美阳所出周代尸臣鼎,其释文今天看来大体正确。宋代人收藏铜器极其重视铭文,故出现了很多著录和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最早的有《皇祐三馆古器图》、刘敞《先秦古器记》、李公麟《考古图》;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内容颇为丰富;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现传最早的是吕大临的《考古图》,体例已相当完善,图象、铭文、释文等项都已具备。宋元时期还有人编集金文文字,汇为字书,现存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杨銁《增广钟鼎篆韵》。
元明时期,由于理学居统治地位,金石之学被讥为玩物丧志,金文研究一时衰微。
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著录和考释铭文的书籍数量远超前代,名家辈出。著作有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等,均有较大成绩。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是一部比较好的金文字典。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 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翔实,考释严谨,对后世影响颇深。
清末以来,研究金文的学者更多。罗振玉、王国维注意铭文与器物本身相结合的研究,王国维有《两周金石文韵读·序》。罗氏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迄今仍是一种最重要的金文汇集。郭沫若用科学方法整理研究金文,所著《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为利用金文探讨古代社会开拓了道路。《金文丛考》是郭沫若于1932年所著,与《两周金文辞大系》为姊妹篇。内容包括《金文丛考》8篇,《金文馀释》释字16篇,《新出四器铭考释》4篇,《金文韵读补遗》共40器。其中“丛考”部分论金文中所表现的周人的传统思想、谥法的起源、彝器人名的字义以及毛公鼎的年代等,考证详明,多非前人所能道。论毛公鼎的年代一文,从铭辞中所透露的历史背景,从文辞中的熟语跟《诗》《书》中文句的比较,从器物的花纹与形式等几方面来考察,推定其为宣王时器,可谓尽考证之能事。其他解字辨韵各篇,大都可以作为定论。1954年作者把本书又与《金文馀释之馀》《古代铭刻汇考》和《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有关金文部分汇集为一书,命名为《金文丛考》。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
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史料虽不尽是金文,但其反映了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一千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对青铜时代历史的考察意义十分重要。
其他海内外学者著作不胜枚举,如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等等,各有贡献。近年编著的工具书,如周法高《金文诂林》,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青铜器论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等,都有助于对金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