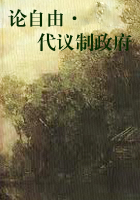第四章是在阐述了反共主义起源、发展及实践的基础上,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论述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本章首先阐述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即作为美国的外交“理念”和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然后论述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随后又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主要指导思想(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以及它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后分析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发挥作用的三条规律(即当美国国力强盛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作用;当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趋向于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美国战略对手强大并强调意识形态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本章的最后一节探讨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发挥作用的趋势。总趋势是:一方面,意识形态外交将仍然存在,有时还会强化;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趋于弱化。意识形态外交会仍然存在的原因是:“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美国的“一超”地位会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形势比较好;全球化的影响。本章侧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将趋于弱化的原因,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使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减弱;全球化使两种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多极化使美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冲淡了两制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吸取经验教训,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这部分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由于本章理论性较强,对理解全文的内容起着指导作用,而且难以驾驭,因此是本课题的又一个重点和难点。在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便利,作者使用了“基本国家利益”和“一般国家利益”概念,将国家利益分成不同的层次,这对理解本章的观点和思路会有所帮助,同时有助于理解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虽然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但内容却有交叉。一方面,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织部分,但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比较起来,它又是处于次要的位置上,是一般的国家利益,而后者则是基本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贯穿、渗透在基本国家利益中,影响人们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
在结束语中,主要针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作用的发展趋势,联系中美关系的现状,阐明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采取的战略对策。首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否认意识形态外交作用的“右”的倾向;另一种是夸大其作用的“左”的倾向。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承认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又不能反应过度,盲目夸大其作用。其次,为了减弱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的动力,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应当注意树立、宣传正确的意识形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但必须明确,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寻求和平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寻求搞“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第三,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以及全球化和多极化等大趋势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正视这些共同利益,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好关系。第四,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这是符合时代主题要求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国策,也是增强两种制度国家间人民相互了解,改善国家间关系的重要途径。第五,针对两种制度国家间所存在的利益差异和对立,应当本着“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的原则,尽可能化解矛盾,不让那些差异与对立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结束语的内容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本书论题的范围,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作为本书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
四
国内外学者对意识形态至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美国哈泼·科林斯(HarperC·llins)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对“意识形态”一词做出了4种解释:1、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是指有关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的思想流派,这种流派是与宗教相分离的。但是这个词语的含义后来演化得更富有哲学色彩。美国政治的主流从未受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左右;只是两个主要政党的极端部分——即极“右”或极“左”——更关注意识形态。一位名叫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作家曾在60年代就认定“意识形态在美国的终结”。很多“后二战”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实用主义已被美国人选定为“意识形态”。2、凡是人们相信的有关政治过程的事物,无论它是否是相互关联的。3、用相对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社会现象的相互关联的观念系列或世界观。4、关于一个社会如何运作的有选择的而且经常是扭曲的概念。一个集团可以坚持将这种概念作为维持并巩固该集团的工具,也可以将之作为解释他们已经疏远了的世界的工具。
国内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界定“意识形态”概念:一是从哲学角度,将之看成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二是从政治、社会角度,将之作为一个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同的学派对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定义。俞吾金在《意识形态论》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给意识形态下了这样的定义:“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上述《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中的4种解释则是从政治学角度下的定义。不过,在这4种定义中,第一种更接近本文所用的“意识形态”概念。
然而,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很难将哲学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上的意识形态截然分开。王缉思教授所下的定义就带有综合的特性:“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王振华教授将意识形态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意识形态通常是指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与群体对外部世界和社会所持的一整套紧密相关的看法、见解和观念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国际关系和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一种价值尺度和辩护体系。”“从狭义上说,意识形态也可以表现为一些具体的伦理道义原则。这些原则既可以成为对外政策和某一国际行为的目标,也可作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本文所取的正是这个狭义“意识形态”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表现为“反共主义”。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反共主义一方面是美国的外交理念,是一项政策目标,是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作为工具,首先是争取国内公众和国际盟友及中间力量支持和同情的旗号;其次是压制、控制盟友及中间力量的手段,也是欺骗国内公众、制造舆论的手段;最后是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
当然,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仅限于反共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扩张主义等也都是对美国外交有着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其中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为深远。从一定程度上说,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中最基本的意识形态,维护、促进民主和人权从美国立国后就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目标,并渗透在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中。只是由于十月革命后,美国人将共产主义看成是它推进民主、人权的最大障碍,反共主义才暂时取代了民主和人权,成为美国外交的目标和工具。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已不再构成推进民主和人权的主要障碍,于是民主、人权才又重新回到了美国外交的前台,取代了冷战期间反共主义的位置。时常听到这样的争论: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如果抽象地回答这个问题,肯定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实际上,如果具体地谈,有淡化的一面,也有强化的一面。由于美国决策层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威胁美国安全的最主要因素,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确实处于低潮,所以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弱化了;然而,推进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却有所提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得到强化。
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贯彻在美国外交始终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同自由主义一样,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不完全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尽管也适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因为本书的论题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而反共主义则是其集中表现,具有特殊性,所以本书主要是探讨反共主义问题。当然,特殊与一般是有着有机联系的,在论述反共主义问题,尤其是在冷战后的表现时,又不可不涉及带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冷战后的反共主义是隐含、渗透在一般的意识形态之中的。
在美国,有些学者和外交实践者不承认存在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托马斯·贝雷(Th·masBailey)在1945年时曾将美国的目标或“基本政策”概括成如下几点:“孤立,不干涉或‘不卷入’;门罗主义(影响范围限于西半球);海上自由;门户开放,特别是在中国——这是美国公民在与其他外国人平等的基础上在国外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泛美主义;机会主义。”贝雷认为,这些是美国外交的目标,但不是意识形态。小亚瑟·斯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Jun.)认为,意识形态对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有一些美国例外论的理论家倾向于把“Americanness”甚至“America”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fstadter)宣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但自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的好运。”另一位美国例外论理论家西摩尔·里普塞特(Seym·urMartinLipset)认为:“美国是围绕着一个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这个意识形态包括一系列关于一个好社会的特征的教条。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是一种‘主义’或意识形态,这与共产主义或***主义或自由主义是‘主义’同理。这个意识形态可以用4个词来概括:反中央集权主义(Anti-statism),个人主义,民粹主义(P·pulism),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
当然,更多的学者承认美国外交意识形态。斯考特·卢卡斯认为:“就像美国与之争斗了如此长时间的苏维埃制度一样,美国也有一个‘意识形态’。它可能不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那样被赋予严格的定义;然而它仍然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依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给它们以生机。”
约翰·杜姆布莱尔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辩护者和实践者都倾向于坦率地承认,“Americanness”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1987年就宣称:“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的、作为本世纪标志的意识形态大搏斗基本上已经定局”。这里,舒尔茨清楚地表明,冷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搏斗,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同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或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斗争。美国自由民主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1)民主与资本主义相互依存;(2)个人自由并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3)权力有限的政府,法治,自然权利,人类社会的可臻完善性,以及人类进步的可能性。美国人确信,美国的民主历史使它成为民主的楷模,当然也就是奉行这种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楷模。杜姆布莱尔进一步归纳道:自由主义的敌人,右边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左边是那些宣称只有通过超越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人类自由的各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柱,摆动于不卷入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国际主义之间。笔者赞成杜姆布莱尔和卢卡斯的观点。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这里所讲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政治文化,或者称之为政治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并不是政治文化的全部,而是其核心内容,人们在使用“政治文化”一词时,所包含的内容更宽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但也包括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内容。迈克尔·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所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就是政治文化。
当代的许多学者,往往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来研究。可以说,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意识形态各要素的综合反映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本书在使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文化这三个词时,基本上是这样处理三者关系的: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价值观又构成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当然,这种包容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几何图形式的包容,有时三者之间,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之间是相互交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