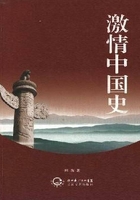万万料想不到,风云骤变,在一九六六年,傅雷又蒙受了更大的屈辱!在那年八月二十八日夜里十点,有人敲门,傅雷还没睡,赶紧去开门。门开了,一群戴着红色“造反”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傅雷的鼻子大骂“老右派”!接着,傅雷被隔离在阳台,傅雷夫人被隔离在卧室,保姆被隔离在厨房。大抄家开始了。地板被掘开。就连傅雷埋在月季花下面的毛豆荚、带鱼鳞之类,也被挖出来“审查”一番。抄家的重点目标,是家书。傅雷视家书如家珍,他写给儿子的每一封信,总是由夫人抄下留底。傅聪写给他的信,他总是编号保存。他还根据傅聪的来信,分别摘录在两个题为“学习经过”和“国外音乐报道”的本子上。抄家者主要是某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本想从家书中查到傅雷“里通外国”的罪证,万万没有想到,家书是谈音乐艺术的,是谈做人道德的,是谈爱国之情的。“红卫兵”们竟然忘了自己是在执行“抄家”任务,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起家书来!除了傅家的几位挚友至亲看过家书之外,这些戴着红袖章的青年,可以算是家书的第一批读者!这批家书被运到“专案组”之后,常常有人来“查阅”,还有人在下班时偷偷把它带走,回家后连夜抄录,第二天一早又悄悄放回“专案组”的档案柜。那些“手抄本”,大概是家书的最早的版本吧。即使在那动乱、黑白颠倒的年月,傅雷家书仍闪耀着它的真知的光芒,射进“红卫兵”们的内心深处……
大抄家一连进行了几天几夜,成箱的书、稿、信被汽车运走。直到九月二日上午,才算结束。那天上午十点,抄家者把傅雷拉到家门口,站在方凳上斗。二十多张大字报,贴满了傅家的墙壁……
傅雷是正气凛然的人,他疾恶如仇。他不能忍受对他人格的凌辱,不能忍受对他事业的践踏。当天子夜之后,傅雷夫妇双双愤然离世……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诗人于谦的这两句诗,是傅雷当时心境的最确切的写照。他临终留下一个用火漆封口的大包,放在他为儿子买的那架心爱的钢琴上。里面有十个信封,写着他的遗言,放着他的遗物:
一、请把这月的房租五十八元,交给房管处;
二、这是两人的火葬费,请代办;
三、这是留给阿敏的话;
四、我的手表,送给阿敏的女朋友;
五、这是我妻子的手表,送给保姆菊娣做个纪念;我们死后,菊娣生活没有着落,这五百元存单留给她;
六、这只手表是一位朋友托我叫人修理的,请转交我的朋友;
……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傅雷是非常冷静、清醒、明白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傅雷夫妇的死,震撼着无数人的心。多少正直的人们,为傅雷暗暗流泪、叹息,为他不平、愤懑。在傅雷去世后的第三天,当时也身处逆境的周煦良教授潸然命笔,写下了注满情谊的诗《吊傅雷》:一街南北过从频,仓促谁知隔死生,未必精魂来入梦,拥衾黑坐苦思君。
在那样的年月,傅雷夫妇是属于“黑五类”,死了不仅谈不上开追悼会,连骨灰都不许保存。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发生了:当傅雷去世的消息悄悄传开之后,忽然冒出一个傅雷的“干女儿”,向火葬场要傅雷夫妇的骨灰。
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青年,喜欢音乐,听过傅聪的演奏。就是这位“干女儿”,把傅雷夫妇的骨灰保存了下来!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难征服的是人心!”这位突然出现的“干女儿”,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
这位“干女儿”曾到火葬场办过寄存骨灰的手续,曾去过天舅舅和保姆家中。她总是戴着大口罩,看不清面目。一直到最近,费了莫大的周折,傅聪才算打听到她的姓名。
傅雷呵,你的在天之灵,把她认做“干女儿”吧!
我要归队
“即使想到你,有些安慰,却也立刻会想到随时有离开你们的可能。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的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傅雷致傅聪。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里,傅聪才从法国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父母去世的消息。他的脑海中,回响着苏轼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台湾方面,更加起劲地想趁机拉拢傅聪。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他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的离世所表达的唯一的方式。
许多朋友都劝傅聪,既然你父母双亡,你在国内没有“根”了,你更不必回去了。
不,不,我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爱国的心。我酷爱生我育我的祖国。父母的去世,更加重了我对祖国的思恋与怀念。我多么想有机会回到祖国,把艺术贡献给人民,用我的琴艺向哺育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进行“反哺”。--傅聪期望着有朝一日归队!
他多次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向祖国表达他的返归之意。无奈,历史的误会尚未消除。
傅聪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订阅了许多中文报刊。他也从外国报刊、广播、电视中,时时关注着来自祖国的消息。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访华时,傅聪又动心了。他托朋友转达了他想回去看看的心意,但是没有回音。
一九七七年初春的一天,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听到中央乐团的演奏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出现。他想,也许是时候了。
这年,傅聪打听到与他断绝音信十多年的弟弟阿敏的下落,给他写了信。在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思乡心情,说不知哪天能够再看到故乡上海的风光,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和朋友。接到阿敏的回信,傅聪才知道,弟弟本来在外交学院上学,要被培养为外交人才,由于父亲问题的牵连,后来到一所中学教英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现在为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去英国访问。当年,傅聪在波兰留学时,吴祖强在苏联留学,他们之间有过许多交往。傅聪很希望在伦敦见到他。可是,很不巧,当时他即将出发去瑞士演出,他托英中文化协会的朋友转告吴祖强,回来后一定要去拜访。
傅聪在瑞士结束演出后,匆匆赶回伦敦。他看到吴祖强给他留的地址,欣喜万分。当天晚上十一点,知道吴祖强回到旅馆,他就急切地直奔那里。到了旅馆,当吴祖强看见傅聪穿着一身中式棉袄,傅聪看见吴祖强竟已头发灰白,都愣住了。在热烈地握手时,傅聪的视线模糊了!虽然他在英国见过很多从中国来的人,但是见到吴祖强,他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他把吴祖强看做祖国的代表!傅聪向吴祖强倾诉了别离之苦,思乡之切。他恨不得把他的赤子之心,掏出来给祖国看!他的话像开了闸的水,哗哗流个不停。是啊,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整整二十年积在内心的话,都想向老朋友倾诉……子夜之后,傅聪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那一夜,他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
几天之后,当傅聪在伦敦伊丽莎白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时,吴祖强带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出席。为了表达对祖国亲人的谢意,傅聪在独奏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加演了他最喜爱弹的《牧童短笛》。这是贺绿汀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名作,它描写了牧童在牛背悠闲地吹笛,漫游于中国南方水乡。傅聪加演这首曲子,用他的钢琴语言,抒发了他的乡思。敏感的外国记者马上发觉音乐会上的异常气氛,把它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
这是一颗信号弹。
这之后,傅聪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很想回来看看他唯一的亲人弟弟;如果现在国家需要他的话,他愿为国家做些事情。
傅聪打算回国看看的消息传开以后,引起种种议论,有些朋友给他泼冷水,劝他千万不要期望过高,说中国还很穷苦,回去后肯定有好多事情会看不惯。傅聪不以为然,他说,“儿不嫌娘穷”,我本来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嘛!有的人劝他说,作为一位有地位的艺术家,中国不邀请,就不回去。傅聪也不同意这个看法,当年是他自己走的,怎么能让国家请才回去呢?国家有国家的尊严。
他终于得到祖国的谅解。他终于回来了!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
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站在父母的遗像前,傅聪感慨万千!值得庆幸的是,祖国阳光明媚,那阴霾的日子已经过去。傅雷的骨灰盒,当年为了避免麻烦,写了他的号--傅怒安。如今,堂堂正正地写着“傅雷”两个字,安放在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啊,总算大难已过!傅聪见到阔别多年的亲友,说不尽的离别之苦,说不尽的重逢之喜。此情此景,恰似唐朝诗人李益在诗中的描绘:“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这次回来,傅聪在祖国住了十天。在上海的时候,他住在天舅舅家里。这十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天,也是最痛苦的十天。这十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纵然外国文明进步、科技发达,但人情淡薄。他在故乡重享亲人、朋友的温暖,他为那些如饥似渴、求知欲强烈的学生讲课,他感到幸福。他痛悼故去的双亲,听到朋友们悲惨的遭遇,看到国家这些年遭受的灾难,他心中悲痛。
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二十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如今,他已经回来五次了。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
这几年以来,有两件事,最使傅聪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