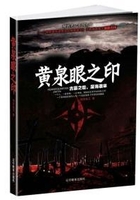放猫去逮捕。
不见鼠踪迹,
只闻蛐蛐笑,
猫儿泪涟涟。
“那蛐蛐怎么那么坏?”陌生人听明白了歌谣的情节,说,“还装成老鼠进厢房了,不像话。”
坐在陌生人邻座的姑娘不由哑然失笑。陌生人红了脸,用手抻了抻衣领。赵雷便仔细打量他的这位旅伴,他是长条脸,小眼睛,下嘴唇明显比上嘴唇要突出一些,所以给人一种受冤的感觉。他的颧骨较高,而且是赤红色,而额头、面颊和下巴却是青黄色的,看上去有些不谐调。他的耳朵与脸形一样细长,很薄,说话时那耳朵便微妙地跟着颤动。他的脸给人一种许多天未洗的感觉,赵雷仔细琢磨了一番,发现是因为那些粗黑的鼻毛从鼻孔钻出来作怪的缘故。鼻毛与胡子连在了一起,就使那一块仿佛成了垃圾场。
陌生人喝了几口水,然后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对赵雷说:“你说喝凉水会得胆结石,还能得别的病吗?”
“别的?”赵雷含糊其辞地回答,“我想别的病也会一样得的。”
“真的?”他提高了嗓门尖叫一声,而且拍一下茶桌,“狗蛋就爱喝凉水!他打小就这样,整天喝得小肚子溜溜的圆!”
“狗蛋是谁?”赵雷问。
“狗蛋就是狗蛋。”他说。
“我是说他是你的什么人?”赵雷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故事,于是追问道。
“我是他舅舅。”他说,“他是我外甥。”
“他多大了?”赵雷问。
“十一岁。”陌生人叹了口气说,“没准他的病是喝凉水落下的?他整天就捧个水舀子喝凉水,还不爱吃热饭。咦!”他拍了一下腿,一副后悔不迭的样子。
“狗蛋得了什么病?”赵雷问。
“白血病。”他悲凉地说,“他才十一岁。”
“他怎么得了这个病?”赵雷的心抽搐了一下,说,“是遗传的吗?”
“这个病不遗传,再说全家也没有得过这病的人。偏偏让他给摊上了,真是不公平!”
“他现在治得怎么样了?”赵雷颇为同情地问。
“在北京治了一年了。”陌生人惆怅地说,“我这趟就是为他去的。那个可怜人啊,脸煞白煞白的,胳膊和腿都细了。人变得比以前懂事了,还在病床上学课本,还帮同一个房子的人买饭和打水。见了我一个劲地说:‘舅舅,你别担心,我会好起来的。’这哪像个孩子说的话?病都把他磨成大人了!”陌生人哽咽不语了。赵雷望着他眼里那像磷光一样闪烁的泪花,也忍不住一阵辛酸。可惜他还不知道该怎样用言语安慰大人,于是就把自己的水杯递给他,说:“喝点水吧。”
陌生人接过杯子,拧开盖,泪水便夺眶而出坠入杯子。所以他是把自己的泪水又喝回了体内。列车“咣啷”一声停靠在一个小站上,上下车的人并不很多,车只停了三分钟便又重新启动。补票员开始吆喝没票的乘客去补票,而两个穿制服的乘警开始逐个车厢查票了。窗外仍然是汪洋的绿色,铺天盖地,从窗外透过来的风有股腥味,也许他们正在经过盐碱地或者鱼塘。
赵雷开始有些喜欢对面这位忧郁的旅伴了。他想手里若是有巧克力就好了,可以让他吃一颗。因为有一份报纸说吃巧克力可以使人变得热情和快乐。旅客们大多在打瞌睡,也有一些人打扑克、看报、吃零食、织毛衣或者打电子游戏机。过道里一会经过卖杂志的,一会儿又经过捡易拉罐的老头,一会又是售货车吱吱扭扭地过来。地上满是烟头、果皮、纸屑、瓜子壳等杂物,看来列车员一直在偷懒。
乘警抓住了两个无票乘车的人,将他们押至九号车厢。其中年长的是个酒鬼,他手里提着半瓶高粱白酒,走路摇摇晃晃,醉话连篇:“你看补就补呗,揪我的脖领子干啥?我上车前去买票,站上不卖给我,我还想现如今的火车都不用花钱就能坐呢。反正都要天塌地陷了个屁的,不坐白不坐,不喝白不喝!”说完,他定着眼神指着女补票员的粉色内衣领说:“有个苍蝇!”
“你以为坐有苍蝇的火车就不花钱了?”补票员一抖肩膀,使那只苍蝇仓皇离去,说,“别耍花招,掏钱,你这种装疯卖傻的人我见得多了!一抓着他逃票,他不是说得了绝症,就是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再不就是他死了亲人了,刚奔丧回来!”
“你这火车够干净的了,真的,有苍蝇算什么?值!”他说,“我还坐过有耗子的火车呢,耗子比人还精,藏在茶炉的煤渣堆旁,那里暖和呀,晚上它们就去餐车吃饭去了。”
乘警也被他逗乐了,打趣道:“它们进了餐车没来两盅?”
“耗子要是喝酒,我喝什么?”酒鬼精神亢奋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钱,说,“要多少你们拿!”
“你去哪里?”补票员问,“在哪个站上的车?”
“我去德水,在回天堡上的车。”他说。
“去德水做什么了?”乘警问他。
“找儿媳妇算账!”他气愤地说。
“儿媳妇怎么你啦?”补票员麻利地为他补了票,连票带余下的钱一齐放回他的上衣口袋,并且嘱咐他弯腰时要小心,别掉到地上了,让人捡去可就遭殃了。他不以为然地说:“哪能呢!现在不是还在学习雷锋吗?全车厢的人总有三五个是雷锋。”他看见了赵雷,便指着他说:“他那虎头虎脑的样子肯定是个小雷锋!”
众人大笑,赵雷也笑了。
“快说说看,你儿媳妇怎么你了,你要去找她算账?”补票员问。
“她不给我生孙子!”老人理直气壮地说,“头一个生的丫头,第二个生的还是丫头。我为了抱孙子,就把一辈子攒的钱都给她交了超生的罚款了。这回倒好,第三个,又是个丫头,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补票员笑得前仰后合,而民警也乐得直托着下巴,并且气喘吁吁地逗弄他:“你去德水就是为了戳穿这个阴谋?”
“就是就是。”他说,“我得去跟他们说说理。”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人们都落下车窗。车厢里昏暗不堪。补了票的老头摇摇晃晃由乘警扶着走出九号车厢,由于过分激动,他的鼻涕都流下来了。
“这老头,半疯!”女补票员说。
陌生人起身上了次厕所,回来后他小心翼翼地跟邻座的姑娘说:“我能跟你换个位吗?我困了,想趴在茶桌上睡一会。我这边不得趴。”
姑娘爽快地答应了,她说:“你进来睡吧。”
于是他们就交换了位置。在他们交错而过的时候陌生人的腿不小心碰着了姑娘的屁股,他连连说:“不是故意的。”
姑娘笑着说:“没什么。”
陌生人对赵雷说:“丁小天,你好好看着咱俩的包,你要是上厕所就让这位大姐帮着看着。”他又转向那位姑娘,说:“麻烦你了。车上小偷太多,我去北京时丢了一网兜红枣。那是我带给狗蛋吃的。唉!”
“没问题。”姑娘说,“你睡吧。”
陌生人将茶桌上的水杯挪了挪位置,然后双肘环在一起,趴在茶桌上睡了。他大约已经困到极点,很快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赵雷打量着这位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姑娘,她皮肤白皙,鼻翼处有一些小雀斑,细眉细眼,梳着披肩长发,穿一件柠檬色格子宽松上衣,衣摆束在蓝色牛仔裤里,脚上是一双乳白色休闲鞋,不漂亮,但给人的印象比较舒服。她看人时总是微微笑着,显得温和而又礼貌。
“你跟他不是亲戚?”姑娘指着陌生人问赵雷。
赵雷摇摇头,说:“我是在星城车站认识他的。”
“你去哪?”
“古崖屯。”
“去串亲戚?”
“就是去玩。”赵雷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开始盘问姑娘,变被动为主动,“你是干什么的?”
“大学生。”她淡淡地笑着说,“放暑假了,我回老家。”
“你家在哪?”
“周奎。”她说,“半夜到。”
“你上的什么大学?”
姑娘说出了一所赵雷并不知晓的大学。
“你在大学学什么?”
“生物。”她说。
“生物?”赵雷不由思绪翻涌,“学习鸟吗?”
“什么?”姑娘不解地问。
“他说的是鸟。”一直坐在赵雷旁边沉默不语的中年男人用广东腔说道。
“对,就是鸟。”赵雷伸开双臂,抖了抖,做出飞翔的暗示。
姑娘咯咯笑了:“当然学习鸟了。”
“那我问你个问题。”赵雷说,“鸟儿会说话吗?”
“鸟有鸟语呀。”姑娘说,“鸟类相互之间也用它们的语言来交流。”
“那人怎么能听懂它们的叫声呢?”赵雷说,“它们又不会说人话。”
“人是通过观察鸟儿发声后的动作来进行揣摩和判断的。”
“就是说,得用活的鸟才能去研究鸟语?”
“那还用说,死鸟又不会发音。”姑娘说,“我要是研究鸟类语言的,就去森林,那里鸟多。”
“我明白了。”赵雷心下一凉,想道:“看来父亲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
“你喜欢鸟语?”姑娘笑盈盈地问。
“又到一个站了。”赵雷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他指着窗外一带隐隐约约的房屋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大。”
“是集百会。这个地方去年出了个大事,农民播的全是假种子,颗粒无收,追究了好几个月。”姑娘说。
“我在电视上见过报道。”赵雷说,“那些农民蹲在地头哭,真可怜。”
“农民也是没眼光嘛!”广东腔男人说,“买种子不看看好,吃了亏也怪自己嘛。买卖买卖,要看得明明白白的才能成交嘛。”
赵雷很不喜欢他那故作潇洒的谈话方式。而且不喜欢这个语种的声调,在他听来仿佛是大便干燥的人在说话。可班级里却有一些同学模仿这种腔调,引为时髦,一些爱唱歌的女孩子更是趋之若鹜,听得赵雷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不过肖妍从来不用粤语唱歌,这也是赵雷喜欢她的一个因素。他还喜欢她的朴素,她从不穿色彩过于艳丽的衣服。不过她把他送的画册弃在学林书店了。赵雷觉得不该为她再难过了,可他还是鬼使神差地难过起来。
火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停靠在集百会的站台上。陌生人被震得醒了一下,他抬了一下头,茫然地看了一眼赵雷,复又趴下来睡去。
“他的外甥得了白血病。”姑娘小声说,“真是可怜。”
“这个病没个治。”广东人说,“换血也不是个办法,换来换去,还是得死,又白白往外抛钱,不值得。”他的手指做了一个弹烟灰的动作,仿佛患这种病的人不值得再为他做任何挽留。
赵雷有些气愤地说:“那也不能让他等死吧。”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啦!”广东人拉长声调说,“他就是个短命鬼,你怎么想办法也增添不了他的阳寿。”
陌生人就是在这一瞬间突然起来的,他伸出右臂,照广东人的胸前就是一拳。广东人大惊失色地叫道:“你怎么平白无故打人?”
“打的就是你这种冷血鬼。”陌生人又出了一拳,茶桌上的水杯被他的衣袖给碰得一阵哆嗦,赵雷连忙上前扶住。
这时火车刚好离开集百会。车厢里又来了一些新旅客,他们东张西望地找座。后来发现有人在打架,就凑过来围观。
“我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广东人叫道,“我不还手,我不还手,你打啊,你要是把我打死你就有地方去啦,你就不用在这坐火车遭罪啦,也不用为你的外甥操心啦!”
陌生人又要出拳的时候被赵雷给拦住了。他说:“别打了,你接着睡吧,你累了。”
乘警闻讯而来。待到问明事情原委后,就对陌生人说:“打人还是不对,心情不好别冲旅伴发脾气。”
“他算是我什么旅伴?”陌生人指着赵雷说:“丁小天才是我的旅伴!”
“好了好了。”乘警也不愿意多费口舌,他对广东人说:“给你调个车厢吧,你们不面对面坐着就消停了。”
“凭什么让我走?”广东人拍着胸脯说,“他还没跟我道歉呢。”
“那你就等着他跟你道歉吧。”乘警幽默地对围观的人说,“都坐下吧,有什么好看的,这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好解决。”
广东人自觉没趣,他从行李架上取下旅行包说:“君子不和小人一般见识,我到另外的车厢去。不过你得把身份证号码留给我。”
“给你干个屁!”陌生人粗鲁地说。
“我原来得过肺结核,你要是把我的旧病给打出来了,得承担我的医疗费用。”
“原来还是个痨病鬼!”陌生人奚落道,“你知道吗?几十年前你这病比白血病还不如,你靠的还不是后来发明了什么药。你别以为狗蛋就得死,谁要是给他配上血的话,他比你我活得都要好!”
广东人提起旅行袋,对陌生人说:“好啦,我现在不跟你争啦,我知道内地的人个个都这么没教养,不跟你一般见识啦!”
听他的口气,仿佛他并不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而是来自海外。周围的旅客将感情的天平明显倾向于陌生人,对广东人发出一片“嘘”声。他就在这片嘘声中悻悻离去。一个无座的妇女迅速占领了刚空下来的那个位置,她提着半网兜菱角,不住地向下滴水,好像菱角在哭。
(原载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