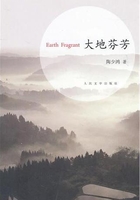周海亮
父亲说啥时候也不能跪下啊!父亲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啊!笨嘴笨舌的父亲只会说这么两句,翻来覆去,如同老僧诵经。
两句话,父亲念叨很多年。
农村老风俗,除夕夜,规规矩矩摆上供桌,旁边燃起黄纸,全家老小跪下,嘭嘭嘭连磕三个响头。父亲却不跪。不跪,也不准家里人跪。供桌照样摆上,酒杯里美酒飘香,黄纸落进火堆,蜷缩,飞舞,满载了全家人的希望。父亲对他说,心诚就行,跪就免了……男儿膝下有黄金啊!不能跪。不能跪。父亲表情虔诚。父亲把膝盖看得无比神圣。膝盖是父亲的神。
他听父亲的,膝盖坚硬如同顽石。小学,中学,大学。毕业,进城,结婚。买房,做官,升官。他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从城里人变成光鲜的城里人。家里常常来客,熟人或者陌生人,来了,有事喝茶说事,没事喝酒下棋。
他知道这个位置的重要性,他需要准确地拿捏分寸。
有人敲门,拘谨不安,就像十几年前的他。从猫眼看,民工打扮,民工表情,民工的卑微与惶恐。把民工让进屋子,问有事吗?民工说,孙董的事。灰黑着脸,低着眼神,瞅着脚尖,呼吸是屏住的。问哪个孙董,民工说半天,他才想起孙董的模样。问孙董什么事?民工说说好年底给钱,可是要了十几趟,硬不给……十几号人的钱呢!问欠多少,民工说每人五千……找您,知道您的话好使。他说您先别急,我总得调查一下。他想给孙董打个电话,翻手机,没有孙董号码,翻名片册,仍然没有,再翻另一本名片册……他一边找一边对民工说,您有事的话,先回吧。
民工突然跪下。嘭一声,膝盖砸上地板,客厅微颤。他一惊,一怔,厌恶感随即而来。他想至于吗?不过五千块钱,至于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啊!跪下的民工不说话,只把头垂得更低。忙把民工扶起,说明天一定找孙董谈谈。心里却恨不得掴这个没有骨气的家伙两记耳光。
翌日在办公室翻到孙董电话,想拨过去,又想再拖一天吧!——那个民工,总得为他的贱骨头付出些代价。
第三天太忙,就把这事忘了。晚上回家,妻子告诉他,来找你的那个民工,白天里,跳了广告牌。当场摔死,脑浆涂了一地。
蓦然想起跪下的狗一样的民工,心里猛一抽搐,两记耳光赏给了自己。他想跪下的纵是一条狗,也得赏它一点残羹剩饭吧?他省掉一个电话,却要了别人一条性命。
然民工至死再没说过一句话。他一言不发地爬上广告牌又一言不发地跳下来,似乎他的死,与孙董没有半点关系。孙董还是孙董,活得圆滑、周全、嚣张并且滋润。甚至,因为这件事,与他,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
时间长了,竟成了朋友——官场上那种。
他知道孙董的野心。他知道孙董为他挖好诸多陷阱。他小心翼翼避着,处处化险为夷。可是终有一次,稍一疏忽,他就深陷进去。孙董隔着饭桌,满意地剔着牙。他的要求不高,一个大工程。
他说不行。这工程不属于你。
孙董就笑了。我有证据……真把那件事抖出去,你就惨了。
他拍了桌子。抖出去,这工程也不属于你!
可是他怕。恐慌。惊惧。彻夜未眠。他是村子的骄傲,父亲的骄傲,他不能出事;他有家,有妻子,有女儿,他不能出事;他有房子,有车子,有位子,他不能出事。他再一次想起那个民工,民工狗一般朝他跪下,却送给他一个陷阱。
第二天再找孙董,低声下气。他说收你的钱,一分不少退你……除了工程,你要什么都行。孙董说我只要工程。他说不可能。孙董说那就对不住了。
他说我们是朋友。孙董用鼻子说,哧。他说求你,我有今天,不容易。孙董再用鼻子说,哧。
嘭!膝盖砸上地板,包厢轻颤……他感觉出地板的坚硬,膝盖的松软……
他的动作迅速夸张,世界訇然倒塌……他像民工一样跪下,像狗一样跪下……
那一刻他想起父亲……父亲磕磕绊绊地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他说,求求你。
孙董扇动鼻子,哧哧。
他一跃而起,拾起旁边的壁纸刀,狠狠扎进孙董胸膛。他说,求求你。
孙董不说话,眼睛惊骇血红。他拔出刀子,说,求求你。刀子再扎进去。扎进去。扎进去……他说,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他畏罪潜逃。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无影无踪。而当人们终将这件事渐渐淡忘,他却突然出现。
是自首。
他说他来自首,既不是良心发现,也不是受够亡命天涯的折磨。他来,只因为前几天,他偷偷回过一趟老家……
“……是夜里,有月。我站在院子里,与父亲告别。父亲送出来,老泪纵横。我们隔着一堆乱石,一棵树,大约二十步距离。父亲说儿啊,你可以提心吊胆过日子,可是你爹不能,你妈不能,你婆娘不能,你闺女不能。父亲说儿啊,你可以背着罪名东躲西藏,可是你爹不能,你妈不能,你婆娘不能,你闺女不能。父亲说儿啊,你杀了人,你应该坐牢。父亲说儿啊,听爹的话,去自首吧!……然后,父亲走过来。他慢慢走到我的面前……他走了很长时间……
他紧紧抱住了我……”
就因为这些?警察有些不解。
是的。他泣不成声,因为,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是跪着走到我面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