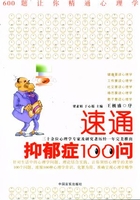各位,我们对于梦的研究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寻求一种新方法。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首先我们要肯定这样一个假说,以此为根据做进一步的研究,即梦是一种心理的现象,而非身体的现象。你们应该知道它的意义,可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假设呢?并没有什么理由,反过来看也没有阻止我们作出这个假设的理由。我们认为:假如梦是身体的一种现象,我们便不必再去研究它;要使我们产生兴趣,就只有假设梦是一种心理的现象。所以,我们愿意承认这个假说的正确,再寻求结果。求得了结果,就可以知道这一假说是否有价值,从而得到更加明确的结论。现在你们要知道,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研究方向在哪里?其实,我们的目的与所有的科学研究没有不同,那就是认识研究对象,明确其存在的关系,最终取得该领域的支配权。
接下来,我们仍然在“梦是一种心理现象”这个假说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梦实际上是做梦人的言语动作,只不过我们不明白而已。你们如果不懂,你们会怎么做?你们必然会质问我的吧?如此我们岂不是同样可以向做梦者质问梦的意义吗?
要记得,曾经我们在研究过失的意义时同样采用过这一方法。当时自然是讨论口误的实例。有人说:“因此那件事发龊了。”我们就会问,说话者即解释:“不,我说错了。”幸好,发问的是与精神分析无关者而不是我们,他们于是问道,这话真是莫名其妙,究竟何意。说话者立刻回道:“那是一件龌龊的事情。”但是他制止了自己,用了较温和的字眼说:“那边又发生了事情。”当时,我曾说过这一询问即构成了精神分析研究的模型。须知,精神分析的技术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让被分析者回答被问到的一切问题。于是做梦者理当解释自己的梦。
然而,我们大家都了解研究梦并不是如此简单的。拿过失来说,一是诸多的实例可采用此方法分析;二是某些例子中被问者不愿意回答,并且听到亲朋代为答复,会怒斥反驳。而对于梦,第一类的实例完全没有,做梦者经常说自己对此事什么也不知道。即便他不曾怒斥反驳,也没有人可以代他作答。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努力求解了吗?他既然不明了,我们也无从着手,旁人当然也不会清楚,因此此事求解无望。假设你们高兴这样,那就算了。然而要是你们不相信,请跟我来吧。我会告诉你们,做梦者都了解梦的意义,只是他本人误以为自己一无所知而已。
关于这一点,你们可能得多留心这一事实:在刚才的几句话里,我已经作出了两个设定,所以,怕是很难再说自己的方法有多可靠了。梦既然是一种心理的现象,又知道一些事情原本是明了的,只是自己不知而已,就像这样的假设!你们必须明白这两种假说是不可能共存的,或许对那些因此而得到的结论,可能也没什么兴趣了吧。
实际上,我到这儿作演讲并非要有所蒙骗。虽然我曾称此次的演讲为“精神分析引论”,然而我可不是来做什么“神谕”,对你们大谈诸多易于连贯的事实,却隐藏起所有的缺陷,让你们轻易地相信自己收获颇丰。其实不然,面对着诸如你们这样的初学者,我才会如此迫切地把这一科学的本来面目详细告知,它的累赘与不成熟,它提出的要求与可能招致的批判,完全告诉你们。我明白不管哪种科学,特别对于初学者都是如此。我也了解许多人在讲授其他科学时,最初总是竭力掩盖其困难与缺陷。然而精神分析不应该这样。因此,我提出这两个假说,其中一个为另一个所涵盖。如果有人认为太牵强或太不确定,或者更倾向于较可靠或精确的事实及演绎,则他们就不必再跟随我研究了。我想给他们以忠告:把心理学完全抛开吧。在心理学领域,恐怕是找不到他们想走的切实可靠的路子。更何况一门科学尽管对人类的认知有贡献,也大可不必勉强令其信服。相信与否,须看成果而论,只要耐心等待研究成果的出现,必然将为世人所瞩目。
可是,有些人却并不因此而感到沮丧,我也将对他们提出警告——这两个假说的重要性并不相同。第一个假说“梦是一种心理现象”将在我们的研究里得到证明。而第二个假说已经在其他领域有据可查,我们只是借用到这里而已。
“做梦者拥有知识却不自知”,我们究竟该如何证明和联想从而认定这一假设正确呢?诚然这一事实使人震惊,我们将因此改变对于精神生活的理解,是无须隐瞒的。顺便说一下,一旦说出这一事实,必定引起误会,而它又是真实不虚的。总而言之,词语间充满着矛盾。然而做梦者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隐瞒的企图。我们既不归罪于我们自己,也不会将这一事实归罪于人们的无知或无兴趣,因为这些心理学问题是有决定性的观察和实验所忽视。
我们将从何寻求到第二个假说的证据呢?答案是催眠现象的研究。1889年,我曾在法国南锡观看了李伯特和柏恩海关于催眠的实验。该实验使人进入睡眠状态,产生各种幻觉。清醒后,被催眠者似乎对于在睡眠中经历过的事情一无所知。柏恩海虽然多次让他说出被催眠时的经历,他本人却说什么也不记得。然而柏恩海坚信他总应该知道什么,记住些什么。被催眠者有了动摇,开始回忆,起初想起了催眠者说出的暗示,接着又想起一件事,他的记忆渐趋完整,最后竟无一遗漏。当时并没有人告诉他什么,全部为被催眠者本人记起。由此可知此类的记忆一开始就留存于心中,只是无从得知罢了;他自己不知道,只好相信不知。这一情形与我们要研究的做梦者完全相同。
如果上述事实是成立的,我认为你们将会惊异万分,会问:“你在讨论过失时说过,人的口误其实藏有潜在用意,只是自己没有察觉因而极力反对,这时你并没有提出这一证据,为什么?假如可以确信一个人能有自己毫不知道的某种记忆,那么会有其他的心理过程在他心中不断进行,他自己却不知道也是可能的。更早一点拿出这个论据,会让我们更加信服,也会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过失。”的确,当时我正有此意,然而我却把它留存到了更需要时再用。因为有些过失本身容易理解,另一些过失,我们想要明白其意义,则必须假设必然存在着他本人也不知道的心理活动。至于梦,我们则必须从别处求得解释,如果是通过催眠方式得到证据,则易于为人所接受。过失的情境区别于催眠的状态而表现为常态,梦的主要条件则是睡眠,睡眠与催眠之间显然关系密切。催眠也被称作“不自然的睡眠”,我们开始对被催眠者说的暗示如“睡吧”,就是与自然睡眠的梦相比拟,它们拥有相类似的心理情境。自然睡眠时,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催眠同样如此,只不过是与催眠者互相感通而已。实际上,保姆在睡眠时大多可称为“常态的催眠”,保姆尽管睡着,却不会停止与孩子互相感通,只有孩子能唤醒她。因此,要用催眠来模拟自然睡眠,也算不上什么胆大妄为。并且“梦者对梦本有知,不过是很少接触它,因此自己并不知晓”这个假设也谈不上是荒唐的捏造了。关于梦,我们曾经从干扰睡眠的刺激以及白日梦着手研究,而今已经出现了第三条路,即由催眠时“暗示”所引发的梦入手。
现在我们如果再来讨论梦,或许把握更大了。我们已相信做梦者对梦本有知,却不知如何从做梦者那里获得这些知识,当然我们并不愿意他立刻说出梦的意义,但是我们肯定由此可推知梦的起源以及梦所由起的思想和情感。对于过失,某人错误地说成“发龊”,如果查问为何说错了,他的第一个联想就是对过失的解释。释梦术也很简单,先以此例作为模型。当我们询问做梦者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他的答复即可作为梦的解释。而关于他是不是认为无所知或有所知,则是无关紧要,我们都将给予同等待遇。
释梦术原本很简单,但是我担心你们的反对会更严厉。你们想说:“又要进行第三个假定了,更加不可靠了!当我问做梦者对梦有什么印象,你认为他的第一个联想真的是我们想要的解释吗?其实可能他根本什么都没有想,或者是上帝才知道他在联想什么。我的确是不能想象你如此期待的理由何在。实际上,你对机会过于信赖,然而这里却需要更多的批判成分。而且梦明显有别于某个单独的口误,它是由许多元素构建而成。那么我们的研究究竟要依据哪个联想呢?”
对于所有非要点的方面而言,你们所说的都很正确。你们认为梦与口误不同,它由很多元素构成这一点也对。当然我们的解梦术会考虑它。我们要把梦分解为多个单元素,一一讨论,如此梦就与口误非常相似了。你也表示,我们如果询问做梦者他梦中的所有单元素时,他可能毫不知情,那也不错。对某些实例来讲,可以接受这个答案,将来我会再来告诉你们都是哪些例子;很奇怪,我们对这些实例都有着较明确的观点。其大意是说,如果做梦者说对梦毫无知晓,我们会予以反驳并要求他务必回答,告知他必定会有一些意念的,结果我们当然没有错。于是他将有一个联想,而他的联想究竟是什么,就与我们无关了。比较容易引发联想的是过往。他可能说:“那好像发生在昨天。”然后列举出两个并不费解的梦,或许“他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因此,前一天的印象容易与梦有联系,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他可能从梦入手,会想到很早发生的事情,最后竟会记起遥远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