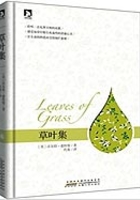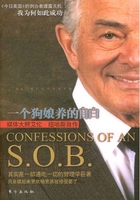击向后世寻觅的无穷
当死亡拼写的永恒
用尽我所有黑夜的墨水
当我被漂白的生命
融进一缕月光冷寂的澄莹
照耀,一爿深夜无眠的窗棂……
来临
咒语的结松开了
蝮蛇冬眠的洞穴
释放出惊蛰的炸雷
最后一支冰凌攥紧的长夜
叩开黎明熹微的门扉
白玉兰澄冽的水晶杯
斟满三月允诺的新生
像章
别在记忆里的像章也别在肉里
那曾是一个无法剜出的盲点
一个年代,那轮照耀别无选择
太阳:唯一的姓氏
葵花的祖辈供奉救世的香火
巨人的石雕勾勒江湖屈膝的姿势
万岁!相濡以沫的铸造
红的底色凹凸黄的遗传
铸造,用冤灵前仆后继的密度
烈焰,是从来世透支的亿万激昂
万头攒动的飞蛾的白夜呵
光芒绝对的入口反复检票
提纯的血液日夜川流不息
为了淬火一枚永不跌落的幻象
即使赭云的天穹熄灭,锈痂剥落
耻辱,仍在现实的胸襟累累发亮
秋天就要说出那个秘密
听,从那张欲言又止的嘴唇出发的风
一路翻搅着灰黄的落叶,这浩荡匍匐的
信徒,昼夜不停地赶往那座斜坡
去覆盖一个背影裸露的不安
向着那里,茫茫芦苇驯顺地倒伏
干枯的茎管里响彻弃绝的辽阔
沉思,使一块块苔石凸出湖面
昨日,正被告别的雁阵一声声衔远……
神秘悄悄结果,在手臂够不到的枝头
除了神秘,什么能安慰秋天的悲苦?
忍不住的秘密在核里放声啼哭:
仅有的孩子受孕于一小片月光的虚无
落光了叶子的树如阴郁的僧侣
互为尽头地肃立,为各自的肉身里
那枚无法交换的宿命的年轮
而把根更深地扎向无望
最后一枚果子砸向冥想者幽蓝的空旷
而那不落的,悬在半空的
还在折磨谁和谁厮守的恐惧:
那裸向高空的巢里,早已空空……
石头的梨落在餐桌上(6首)莫非
石头的梨落在餐桌上
石头的梨落在餐桌上,大雪的四周
被切下。荒废的岁月又从湿润中苏醒
播种者经过泥土的掩盖,伸出我们的
手套。一面大鼓的震动来自深海
世界的抽屉,被庆祝的人群拉开了
所有的铃铛响起等于铃铛变成了灰烬
而树木划破自己的名字。那些生死
与我们早先的知识毫无瓜葛。那些恨
让一群势利小人购买香料。好像忘了
不下雪的云朵,偏偏是又白又壮的云朵
偏偏是,一张纸后面的道路挡在后面
我们抱来的木柴抱在一起,准备旅行
像唱本一样缓慢
像唱本一样缓慢。像骑驴一样笨拙
什么也看不见什么。核桃的轮回
看不见核桃的硬。发芽和朽木紧跟着
胡同拐弯,在直起腰的老地方
屋檐上写字的狗尾草,揭瓦的狗尾草
让最后的雨滴渗入木料。青苔反光
所以看见所以。因为一只鸟飞了
不是飞高了。黑夜架起了笼子
听风声收缩湖面。一片树叶随着乐曲
辗转无常。而钢琴猛敲石头的缝隙
皇帝脖子的凉,已经浸透了秋天
像幸福一样糊涂,像流水一样远去
从呼吸的底部升起
从呼吸的底部升起。这将是一个人
在大雨的尽头,看我们的脚趾
狐狸的初衷模糊。最肥的肉
已经烂掉。灌木丛四周搀扶大地
这将是野兽的喘息,粮食脱掉衣服
而龙头把一束稻草拧紧。孩子们
苏醒了。晚年的窗子正对着梯田
刀锋在露水上迟钝。打气的小板凳
似乎只有倒着走,才可以走出来
蜗牛的早晨,没有一丝盘算
这将是花白的箩筐,喜鹊的翎
淡忘的容颜,恰在冬夜沉睡的时候
有一片叶子有一片红有一片黄
有一片叶子有一片红有一片黄
我是想不到的。尽管我可以看见
在树丛和西风中,果实劈开了
枝条。当枝条汹涌顺势而下
我扛来梯子,摆放一百只葫芦
给药店的人打一百个招呼。如果
一百只葫芦是满的,就没什么
好说的。没什么是没什么的父亲
不是喊而是不吭一声。挖最深的土
然后卖掉山药,卖掉云彩和早晨
所有暴露过的种子,不会发芽
不会相信,有一片叶子已经穿过
太阳停下
太阳停下。冬天从来都是光着脚
从来,梯子在大雨中越飞越高
隧道推开山崖。从来是愚蠢的
无法诊断。干瘪的瓶子已落入沟渠
从来是我们的契约,是两半的蛋壳
疯狂旋转的花钵如今变成了蓝
扎满羽毛的枣树呼喊着,从来是
一个人,在摇晃的大地上收敛星辰
从来到去,我们千里迢迢打扫战场
菊花和石灰的村庄在玉米中闪耀
火的盆子火的豆荚围绕了很多年
在无边的词语中,我们收获了跳蚤
一首从简单到简单的诗
一首从简单到简单的诗,简单到
全是大地的风声,而没有一片落叶
简单到没有枝丫,没有影子尽管
太阳普照,尽管地黄在墙缝中生长
开一样的花,开完就忘掉的花
尽管简单,幸福的人不听话也不说
看云朵在天上飞,看云朵散了还看
有人猜下雨,有人猜打雷尽管
冬天的毛毛虫不见了。尽管窗户的灰
已经可以写下更多的字,更多的
硬币没有年月日。到不简单的地方
换一个人回来,草丛里都是哑巴
在江边(4首)庞培
云影
树在帮你呼吸
不被打扰地做完你的梦。河流、白云也是
清早,当你碰见一个好天气
你能从静静伫立的树身上
感觉到天色何其湛蓝,云影何等欢畅!
我们大家,我们全体
都被托在一枚树叶那么温凉
秋天的掌心
在江边
水是人类扔在荒野
最原始的一件工具
有一天我路过江边
看到闪闪烁烁的长江水
像一堆暗夜燃起的篝火
一艘油轮途经,仿佛
火上炙烤半熟的野猪
波浪的脂肪溅落
星星点点的火苗
篝火四周,那些渡轮、集装箱吊塔
起重机林立的码头
仿佛一群群伐木者部落
每个人手里都有锋利的石斧
围绕潮汐神秘地
来回致命地走动
如意
虽然我长大了,我的童年还在
每一次熄灯,入眠
我重又在黑暗中
挨近儿时称心的睡眠
边上糊了报纸的板壁
油灯,稻柴草
以及灯光的暗影中放大了数倍
白天听来的《三国志》……
世界如此古老。英雄们仍在旷野中
擂鼓厮杀,列队出阵
长夜如同一面猎猎作响的战旗
战旗之下,是我年幼而骄傲的
童年。姆妈用嘴唇试了试
我额角的体温
深夜读诗
我实际上在读褴褛的童年
读我头顶的夜空星星
读村外一条寂静呼啸的河流
读一个金色的新年,一个腊月
我仿佛把脸依偎在稻草香里
在一处农家灶膛的柴火边
在恋人手心
你那被旷野的凛冽冻红的脸
欷歔着爱情的憧憬。深夜
读诗,我实际上在读她的一缕秀发
读当初的见面,永久的离别
替落叶说的替落叶说的(4首)桑克婚姻
与何塞特朝夕相随,亲密程度远非
世俗夫妇可比,一个影子和另一个影子,
仿佛甜蜜的小奶油,但又比之清新,
而且多出来一点儿晚年才显端倪的分寸感。
这不是秀,只是出于天然的性情的流露。
你们看见的当然都是真实的。但是
我必须提醒你们:这远不是事实的全部。
更多的或者更重要的,你们看不见。
星辰或者灯盏曾经目睹的小小甜蜜,
肯定是有的,但是稀少得——怎么说呢?
无法形容或计算。痛苦之类的词汇,
也都是轻的。当然这是甲方的体验。
而在乙方却非如此。究竟是怎样的,
谁能了解?热内?培德?而我只是洞悉
甲方的秘密。他们或她诠释夜晚的方式
的确有点儿惊世骇俗而且闻所未闻。
平静躺在双人床上,肩隙的一英寸,
犹如地中海一样难以飞渡。矛盾的生活。
快乐是日常的,苦痛似乎是野兽的。
以所谓的爱的名义两匹孤兽热烈地僵持。
偶尔的亲昵,更多的隔膜,夹杂着
自尊心与彼此的怪癖。交谈,或者暗示
都是困难的。甲方发展想象,乙方发展
购物的频率。比鸡肋更美的是什么?
婚姻坏了多少人?其实只是两个人。
你似乎接近何塞特的内涵,但又不全是。
真诚的咫尺天涯你见过么?你见过
这种古里古怪而又难舍难分的婚姻么?
而且并非社会要求,只是自我要求。
因而更怪。如果没有意外该是多么恐怖。
只有安全的记忆或者梦境。这是真的么?
但愿是真的吧,否则该是多么愚蠢。
替落叶说的
我落我的叶子,
是时候到了,就像你们死了,
是时候到了。你们之中的一个
拿着扫帚,拍打我的叶子。
我的叶子落了,不是时候到了,
不是我的友人帮忙,
你们为它命名:流动的空气或者风。
我的失去血液的叶子提前落了。
我不怪你的操切,
你只是接了清洁的任务;
我怪催你消逝的细菌,
因为你更想生存。
我的叶子可以停留
一两天么,就像微博的
一两个帖子?然后,
随你送到哪座焚尸炉吧。
我为伤心人准备的
不是手绢,只是眼泪的导火索。
伤心人是大美人,
脸美,心美。
我的叶子,在辛格的小说里,
值得纪念,就如命悬一线的
韧带。在辛格的小说里,
我是巩固你的小命的打气筒。
是我配合着绵绵的
秋雨,是我配合着阴沉的
天色,是我,使你暂时脱离
亚洲的暧昧。
这是秋天了。
是时候孤独了,像里尔克说的。
你分明地记得,
应该如何拂拭书脊的灰尘。
宅男颂
了解灰尘的灵魂,而人类,
只了解一点儿,而且不乐意提及。
何止灰尘的灵魂?比它细小的
细菌的,喜报的,美德的,
照样描述表面起伏的波纹。
还有更加幽微的事物——
能够区分晨昏光线之中的变迁,
区分灯光的类型,甚至灯光与天光
暧昧交融的某一瞬间……
何况疲懒的心跳,行走的步幅?
何况临屏交谈中偶然
而起的良知?虚拟的真实的游戏。
血淋淋的狐疑,无辜的刺刀。
何况更为粗放的事物?
宅门之外的,沉闷之外的……
何况更为广大的尘世?
只选内里,只选更为细腻的
具体的或者抽象的幻影,
或者幻影的某一化身,例如钉子,
例如替你们咽气的烟气。
电影或者想象,或者
睡眠——那是多么辽阔的生活。
出乎逻辑之外的启示,
悲伤或者微妙的喜悦,惶惑的不解的画面。
荒谬与浮华,哪一个更值得铁锹
追求?是的,追求。
主动地,而非被动地宅着。
为风雪助威,为一遍一遍的
修改的冷,为一个又一个的
即将消逝的杨宪益。
愤怒
我越来越愤怒。
我一天比一天愤怒。
我一秒比一秒愤怒。
我不想愤怒,我不愿愤怒。
我恨不得满墙写满制怒。
我恨不得变幻出一千双手,
伸到自己的胳肢窝中。
恨不得扯开自己的嘴角,
让它露出一丁点儿的笑容。
我不想愤怒,我不愿愤怒。
我只想快乐,只愿快乐的声音
伴随我的余生。
然而我越来越愤怒。
一天比一天愤怒,一秒比一秒愤怒。
为这些谎言,为这些柔软的暴力,
为这些用尽全世界的粗口也不能倾泻干净的人与事,
为这个冬天——只有它让我稍微安静一会儿,
只有它让我按下愤怒的暂停键。
然后放声大哭。
锈带(3首)林雪
1974年:报考文工团落选
黎明在郊外青灰色的雾霭和楼顶升起
夜在耸立田野工厂的阴影中悄悄散去
一个女人一生的宿命,从那个早上开始
那辆小电车在电杆的天空间咳嗽
早上六点,在搭连站等待从栗子沟
开来的小火车,来自煤矿生活区
我们从终点站下车,步行
到北台群众文化馆。高音喇叭所传出的
国家庄严的声音里饿着肚子
提前两个小时到达,在肮脏的过道
和厕所的臭气中,换衣,化妆,排练
在模拟的舞台上,肚子阵阵咆哮
那时的生活用贫困强暴过每一个人
一个孩子仍毫无指望地爱它
仍不甘心与它错过
就像我们坐过的小火车
任生活哐哐当当,怨声载道
仿佛它载着的
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而是每个人的忧郁失望
主考官有五人。四个女的,一个男人
他们中有三个年轻和蔼,一个
年长生硬。轮到我时
那个年长的目光犀利
用一根新皮尺量我的头围
量颈和手臂。“这么瘦!这么轻!”
他边嘟囔,边生硬地扪我后背
我费力地盯住视力表。那年轻女人
同时轻蔑地托住我的腮
数我口腔深处。“脊柱右侧弯
左眼裸视04,
右眼06。两颗蛀牙”
我从他们手中滑落下来
带着与生俱来的羞耻
和生而为人的罪恶感
一个月后,我知道自己落选了
我握住一只青柿,跑到秋天的坝下痛哭
那时我们生活晦暗,心灵斑驳破碎
那时,一个小女孩看到了
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裂痕
却无力把它们补救
忍受着种种精神或身体的背叛
仿佛那希望还在人间
当美好一再延迟
幸福不是没有,只是还未来到
1977年:取自荨麻地里的一部童话
那条在青春里鼓动情欲和筋脉的河流
在二百公里以外入海。那道河堤
在雨季,只有一块礁石
冒出水面。这已经足够大了
足够让他俩紧紧抱着
看树枝的火焰翻腾,看水鸟
在故乡上空盘旋。他们
从彼此的臂弯里望着他们
出生的地方。颓墙,塔楼
上世纪70年代的化工厂
那边的荨麻地,埋着他的母亲。
而这儿,这儿,灌木林和树木
是他们的歌词:野马像我们儿时
在原野上奔跑;在这儿,
烧炭人唱着古老的歌谣,
这是他们长大的地方
这儿是我们的祖国:
1977年,秘密地取自荨麻地里的
一部童话。一本书,一块磁铁
一个精神,世界的中心。
他们的十根手指,根根疼痛
请看她手中这些有刺
的荨麻!在他睡觉前,他的朗诵
声音周围长着荨麻
只是听,不可以说话。你说出一个字,
就是出卖。1977年,他们的生命
悬于一线,命犯舌尖
1998年:她徒步穿过那一年的雪
1998年的冬天。我步履蹒跚
看见一个步履蹒跚的女人,徒步
穿过1998年的雪。她
在雪中一路小跑。要去销掉
母亲的户口。三天前,她死在家里时
只有四十斤。一副骸骨的重量
她一路小跑着去推劳务中介的门
十三天前,她下了岗。她一路跑着
去小学接年幼的儿子。他刚上一年级
放学了就会喊饿啊饿啊,妈妈
她一路跑着,去区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