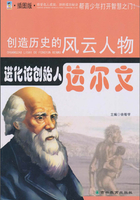真理辩论会(11首)
西川在香港等待台风“鲇鱼”。2010年10月
门卫在旅馆的玻璃门上将乳白色的胶带贴成米字。
送快递的黄色面包车匆匆驶来又匆匆离去。
我逗留的联福道上行人稀少,但本来联福道上行人就稀少;
远处的高楼矗立着,但本来它们就矗立着。
风大了些,旗绳噔噔敲着灰色的金属旗杆。
施工现场的竹竿脚手架究竟能否确保安全我不得而知,
究竟能否在台风之后依然故我我看悬。
台风“鲇鱼”已横扫台湾东北,电视里报道了;
已抵达福建和广东,电视里也说了。
香港天文台已挂出三号风球,然后也许是八号。
这促使我决定在台风到来之前去繁华的街市走一遭,
去热爱一下噪声和人流,去见证一下惊慌的面色。
老房子、小商贩和妓女集中在油麻地和旺角。
时代广场玩概念,广场非广场而是购物中心,矗立在铜锣湾。
台风“鲇鱼”就要来了!海上已掀起十二米高的巨浪。
据说两百年前有过这样可怕的台风,那时还是清朝。
我买了两盒方便面——显然是在起哄。
不过我确也略有担心,遂允许自己喝一瓶可口可乐。
此刻,中央图书馆原本该有一场演讲在进行,
但演讲取消了,那演讲人就成了无事可做的我。
台风,会死人吗?花花世界需要被台风伤害一下吗?
地铁需要停运吗?饭馆需要歇业吗?
政府官员需要在灾害之中冲锋陷阵他们表现的时刻就要到了!
知识分子需要有机会登上道德的制高点他们的庄严准备好了!
而我在逛街!逛街的人碰到逛街的人。转头看,
一个少年与等待绿灯过马路的女孩搭讪。
人到中年我什么没见过!什么都见过我只是还没见识过台风。
一圈电话打出去,给家人,给朋友,
我有点儿兴奋,好像盼着台风来,好像它不是灾难,
好像它到来只为我,好像它是戈多终于要露面,
好像我此来香港就是为了经历一场台风,
淋着大雨,看水漫轩尼诗道,看七米巨浪竖起在尖沙咀岸边。
也许树干会被折断,也许房顶会被掀飞。
我感到这商业的都市它的每一个悲剧的毛孔全张着。
台风呢?台风呢?台风呢?台风怎么还不来呢?
台风不会绕过香港而去吧?
新闻:台风的确绕过了香港。
2010-10-23
墙角之歌
我把一只乌鸦逼到墙角
我要它教给我飞行的诀窍
它唱着“大爷饶命”同时卸下翅膀
然后挣脱我,撒开细爪子奔向世俗的大道
我把一个老头逼到墙角
我要他承认我比他还老
他掏出钱包央求“大爷饶命!”
我稍一犹豫,他薅下我的金项链转身就逃。
我把一个姑娘逼到墙角
我要她赞美这世界的美好
她哆嗦着解开扣子说“大爷饶命!”
然后把自己变成一只两百瓦的灯泡将我照耀
我把一头狗熊逼到墙角
我要它一口把我吃掉
它血口一张说“大爷饶命!”
我一掌打死它,并且就着月光把它吃掉
2010-2-5
真理辩论会
真理越辩越糊涂。
这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
这不是“难得糊涂”的“糊涂”。
那么我们说的“真理”是“真相”吗?
还是对“真相”的无限切近?
真理是嗜血的吗?——三百个人死出的真理
是否等同于三千个人死出的真理?
是可以预言的吗?还是仅仅指向过去?
是数学计算出来的夜色一般安静的结果吗?
还是此内心跟此内心、此内心跟彼内心的高声较劲?
寻找真理是更需要不满和批判呢?还是忧伤的想象力?
在大家彻底糊涂之前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
……
意犹未尽。再聚拢,再开会。
喝茶的人开大会,上厕所的、门外吸烟的开小会,
接电话、打电话的头脑开溜再返回。
与会者的头脑仿佛清醒。早晨,然后正午,然后天黑。
在这些“清醒”的头脑又一次糊涂之前
有人在场外开始签名运动,
要求把真理辩论清楚,辩到五一、七一、十一。
不是还有那么多的节假日吗:端午、中秋和春节!
有人在签名运动的周围卖起了面包、矿泉水和冰棍。
远处,一座“糊涂”的纪念碑拔地而起。
更远处,一个疯子对着旷野高呼:“散会!”
2010-10-15
但什么力量使树木不再生长
看见了使树木生长的力量,
但什么力量能使树木不再生长?
感到了为空气加温的力量,
但什么力量能阻止温度继续升高?
听见了使喜鹊唱响的力量,
但什么力量能使喜鹊沉默,在一瞬间?
北方的水渠干涸了。
南方的洪水淹到了屋顶。
使人类生长的力量中是否包含着
使人类不生长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只扮演叫“停”的角色?
如果砖头在生长,像个流氓,
那么钢筋一定也在生长,像个家长。
高度,好的。晕眩,好的。那么,
砖头的欲望会否被流氓的虚无所取代?
钢筋的欲望会否被家长的年迈所消解?
我停下脚步,歇一会儿——
风景是给无所事事的人准备的——
万物皆备与我,我也把自己备与万物
我也与万物同悲且同乐
而我身边的人们还在大步行进。
喜鹊冲在他们的前面。
他们走到海边停下,大海继续前行。
什么力量可以让大海停下?
2010-1-15
死于感冒的人
他不肯相信他会被几个小人所打倒。
他不怕蛇蝎猛兽, 因为凶猛的它们已成陈词滥调。
这逆风而行的人:风愈大,他的脚步愈有力。
他本应倒在雷电之中,如悲剧剧本所述,以便符合一个英雄的身份。
然而他倒下,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不肯相信, 几个小人用小儿科的手段,
抖抖机灵, 就将他打倒;他相信
在小人背后站着阴险而强大的敌人例如一种价值观化成的巨妖。
所有人都看见了, 他是负有使命的人;
他自己更要求与他崇高的理想相对称的敌人。
多年以来他瞧不起市侩,
远离市侩, 他断定历史会赏脸把他的意思弄明白。
从生活的全部滑稽中挤出了往往呈现于打架斗殴的严肃性。
你看他被几个小人所打倒, 不可能呵。
这让错愕的蛇蝎猛兽们只好求助于陈词滥调:哎呀,哎呀。
仿佛他战胜了癌症, 却死于感冒。谁也没有料到。
2007-8-19
论摄影
风景,拍下来,回头再看,
看见了一个近视眼没看见的东西:
那些事物的阴影,那些不甚美丽的东西;
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很小,
开始没注意,此刻看见了。
房屋,拍下来,回头再看,
看一座房屋,干净的,窗帘拉开的,空的。
使用房屋的人不在房屋里,
仿佛站在我身后,说,拍吧,
我不在那里。
女人,拍下来,回头再看,
看一个女人,看见她的某时某刻。
看见她自己不曾看见的自己:
她的只属于某时某刻的脸、
衬衫下的乳房,她坐下时腰间的肉。
2009-11
第一次写到童年
在大人们绕道而行的煤堆上小枝子褪下她的花短裤。
我看到了:这就是小女孩的干干净净。
她飞不太高的小翅膀紧张,勇敢,不出声地扇动。
一堂生物课。偷偷摸摸的爱的教育。
我忽然记起,在飞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
穿裙子做作业的甄小蔚跷腿蹬住椅子边,
正好展开了她头戴棕色珍珠的小妹妹。
她喜欢我。她把我拉向走廊尽头。我以为她会对我说
她喜欢我,听到的却是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小道消息。
这小道消息我们在七一小学分享了一星期。
公共浴池里妈妈的女同事们笑话我的害羞。
我闭着眼却也看到了她们水中的身体。
乳房和毛发。公共浴池外一个一本正经的下午。
我一本正经地长成一个男人被称作“叔叔”或“老师”
那些并不公共的阿姨们使我的1969年如此具体。
2009-7-1柏林
凤凰,沈从文先生没写到的。2010年7月
沱江上游某处,某人等待时机。
某人半肚子诗情画意,外加半肚子冲天怨气。
他注视着沱江远下凤凰城,好像那里住了一城的亲戚。
沱江注入凤凰城,过三孔桥,撞万寿宫。
地方太美丽了难怪挤住下太多的人。
两岸的木房子挤挤挨挨,据说古来如此,
害怕瘫入江水的吊脚楼,以木杆自撑,据说古来如此。
诗情画意在沱江上游下了狠心:
要干一回!要干一回!——他要到吊脚楼下扔垃圾,
灭灭凤凰城里旅游业的灯红酒绿。
他愤怒出灵感像一个发疯的艺术家嗷嗷叫成一只大猩猩,
老天爷看在眼里,就借给他一场哗啦啦的大暴雨。
沱江上的水手们赶忙收船,
没成想帮了吊脚楼里的酒吧间使它们人满为患。
大雨暴涨江面,上游和支流寂寞的垃圾
有了在凤凰城露脸的大好时机。
凤凰城原本因落伍而美丽,现在因小资而美丽,
可一霎时,既没了她的沈从文也没了她的黄永玉。
书记觉得丢人,游客认出现实。
凤凰人习以为常,专业清垃圾的汉子下到江里。
凤凰不是凤凰已历多时,
正好可以借江面浮满废塑料瓶和一次性快餐盒喘口气。
发疯的大猩猩擤了鼻涕,乘回风兮载云旗,
回到沱江上游变回诗情画意。
赶去逮捕他的公安没能认出他来便只好回去。
凤凰城依旧美丽期待着更美丽那个咿呀喂!
2010-7-30
逸事(之一)
城铁开到柳芳园车站之前,坐在我对面的女青年站起来准备下车。下车就下车吧,可她忽然对坐在我身旁的一个男青年说:“先生,小心点儿,你钱包快掉出来了!”当时我站在车门旁,握着把手,男青年就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我闻听女青年的提醒低头看那男青年的裤兜,他右大腿上裤兜的部位确实鼓出个钱包的印子,但钱包——如果那是——根本没有要掉出来的意思。这时列车到站,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女青年已经下了车。在她下车的一瞬间我忽然反应过来,可车门已经关上——
你他妈什么意思呀?你丫把我当他妈什么人啦!我像个小偷吗?我操你妈!我这眼镜是小偷戴的吗?我这手腕上的战国鸡骨白玉手串是你妈小偷戴的吗?你丫瞎了眼了我操你妈的傻逼!管他妈闲事你也瞅准了再说!操!什么女人哪!我离他近点儿就是要偷他吗?下次让我碰上我他妈偷你!操,你丫也值得偷!你丫那德行样,我碰你我孙子!怎么碰上这么一傻逼呀!平白无故,平白无故,你丫把我搁这儿什么意思呀!你丫倒下车了,谁他妈给我说说清楚?人家真以为我要干什么呢?我他妈得坐到东直门呐,好几站呐!
我身边的男青年倒没什么反应。再一站,他下车。我坐到他的位子上。我忽然有了另一个念头:那女青年难道是在提醒我或另一个人不成?刚才下车的这个男青年难道有点儿可疑吗?我没发现呀。操,怎么回事呀?下次要是叫我在车上发现了小偷,我一定对那小偷说:哎,哥们儿,当心你的钱包。——嘿,这倒是个法儿呵,也伤不着谁,也能防患于未然,和谐呀!
亲爱的姑娘谢谢你!
2010-10-25
逸事(之二)
到交通队宣传科做驾照年检。坐在服务台里面的中年警察翻开我的驾照和行驶本,然后在电脑上检索我的违章记录。他眉毛忽然皱起,扭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超分了。加上你这还没处理的2分,你今年已经13分了。这驾照已经吊销了,你得去车管所,背交规,办新驾照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去了美国小半年,刚回来。前天我遇堵车着急,借用了一下公交车道,不幸被探头拍了下来。这还没处理的2分指的就是这个。可我记得很清楚,我走之前是9分,加上这新罚的2分,我也就是11分,不到12分的限度。警察把电脑屏幕推转给我,我前天的违章记录在案。我疑疑惑惑,要求查看以前已处理过的记录,忽然出现了我不认识的汽车违章的图片。那不是我的车,车牌号码完全陌生。“把你的护照给我看看。”我幸好带着护照。警察翻了翻我的出入境记录。他也纳闷儿。“你曾经把驾照借给过什么人嘛?”警察问。——没有哇!呃,对了,我在3月份丢过驾照,在望京那一带,可能是在一饭馆里。这驾照是我补办的。“那我们查一查,你等电话吧。”
一星期以后我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我们查过了,那辆车的车主我们也知道是谁了,你来检驾照吧。”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是有人冒用了我丢的那个驾照。我问那人是谁,他说:“是望京那边××局的一个处长。”我立刻表示要找他去说道说道。警察说:“你找不着他了。昨天我们把电话打到他们处,他在前天上吊自杀了!看来是经济问题。”他这话把我轰晕了头。这这这,这是怎么回事呀?前天我犯交规,那个处长自杀,也许我们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时刻呢!太离奇了,不可思议!顿过一下,电话那头的警察忽然幽默起来:“你什么人哪?人家冒用了你的驾照,怎么就弄得非上吊不可了呢!”我有点儿毛骨悚然:是呵,我我我,我什么人呐?挂断警察的电话,我点上根烟。我自我安慰:应该是那个上吊的人自问一下他是什么人才对呀。他死之前也许真的这样问过他自己。
2010-10-25
从一件事想到另一件事
这是十月的南方。树木还是绿的,一个老工人擎着一把长柄剪刀去给树木剪枝。在北方,我印象中给树木剪枝是在春天,这老工人在秋天剪枝,一定是我对自然的了解尚有空缺。这棵树个头不大。我怀疑老工人剪它是为了帮助它缩小自己,好在即将到来的台风中站立不倒。他把剪刀伸到一些枝子的梢上,手在长柄的下端一用力,咔嚓一声就把枝子梢给剪了下来。他又把剪刀伸到几根小枝子上,也是咔嚓咔嚓地剪。我注意到一根枝子,我想他下一步肯定会去剪那根枝子。但是没有。他始终没有剪我认为他会剪的枝子。他离开这棵树,继续去剪下一棵。一个中年女工跟着他,拾掇掉在地上的树枝到一辆三轮车的后斗里。他们走开,我来到这棵树下。人家为这棵树忙乎半天,我得看看这棵树。树干上用铁丝捆着个小小的金属牌,写着这树的名字:宫粉羊蹄甲,属苏木科,是一种我不认识的树。英文Camels Foot Tree, 意思是“骆驼蹄树”,不是“羊蹄”;拉丁文Bauhinia variegata,一变成拉丁文,学问就深了。
不知为什么,一瞬间,想起个朋友。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河南来到北京,在西单百货商店门前看到一群人在抢东西。准确地说,是有人在派发什么东西,肯定是为了做宣传,做广告。这位朋友虽然不知道大伙儿在抢什么,但凭着中国人的本能和直觉,他也冲了上去,一副不抢白不抢,有钱不拿是傻瓜的劲头。老电影里穷人去抢地主家的粮食也是这个场面。他抓住一个别人塞到他手里的小纸盒,挤出人群,摊开手一看:ob卫生栓,是一种女性用品!他觉得非常滑稽,太好笑了,就跑到火车站附近我住的地方,把这盒ob卫生栓留给了我,然后回了河南。我也不知道该拿这盒卫生栓干什么,就丢进了抽屉。后来我结婚,老婆在抽屉里发现了这盒卫生栓,遂坚信我有什么事瞒着她。我给她讲了河南朋友的事,她半信半疑。
2010-10-26
极端诗学丛书(5首)臧棣
光棍丛书
光棍光芒万丈——海子
他们介绍说他是光棍,但看上去不像。
他们解释说他绝对是光棍,
他身上有一种光,可以和最深奥的棍子媲美;
甚至让命运也感到羞耻。
但是,拨火棍却不买账。
他们暗示说他不仅仅是光棍,但敏感的
现实却感觉不到一点儿压力。
他们补充说他的外号也叫光棍,
因此,语言是你永远的新娘。
2010.10.
冰岛诗学丛书
她没看出来,你也没看出来。
你见过从鲨鱼变成的人,也见过又变回企鹅的人,
你见过戴耳机的海豹,它最爱听的音乐里
飘着火山的灰。你见过她没有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