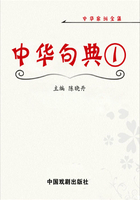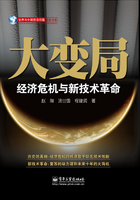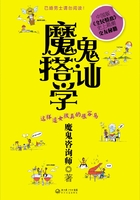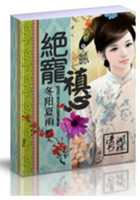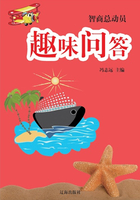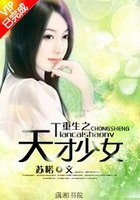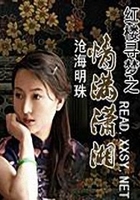《培养杂技人才的几点体会》(赵伟宁,2005)在认识团带班培养杂技人才缺陷的基础上,介绍了一个新的、可行性强的教学模式,即南京采用杂技团和中学联合创办杂技中专班,学制七年,设置了除杂技之外的文化课、舞蹈课、形体课、表演课等,在教学过程中借鉴舞蹈、戏曲、体育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局限性在于研究比较肤浅,停留在表面,所提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大同小异,都是修修补补性建议,没有寻找根源和制度性、全局性解决方案。其中几位作者是杂技业内人士,他们虽然比较清楚杂技教育的问题,可文字水平有限,限制其研究水平。纵观这些文章,没有一篇发表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可见学术界的关注很欠缺。
《试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杂技教育》(张振元,2005),是可检索到的关于杂技教育中最为深入的探讨,该文给杂技教育定位为特殊技能人才教育,指出其教育状况处于非常落后的“孤独状态”。在概述杂技教育的特征、解释其落后的表现的基础上,认为“杂技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教育‘盲点’”,并指出为杂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定位的必要性,作者很有新意地提出建立杂技教练专业。缺点是依然空洞,具体可行的措施少,作者一再强调给杂技定位,却始终没有给杂技教育一个合适的定位。
由于多方面原因,中国民俗学长期偏重的是杂技本身的研究,这也导致民俗学界对于杂技艺术的传承人——以卖艺为生的民间艺人的研究非常罕见,包括如今众多的民俗学教材中也很难见到相应的章节。事实上,由于对这些艺人群体生活的漠视,在中国相关的艺术史教材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除张紫晨的《民间文艺学原理》之外,虽然一般的民俗学教材、专著、地方民俗志中都有民间游戏、竞技等章节,但在涉及民间艺人时都一笔带过,只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民间艺人”一词,对不同类型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学界对民间小戏、说唱、杂耍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表演现象本身,而忽视了对表演活动主体之一的表演者——民间艺人的记述和研究。
(二)民间艺术研究
1.民间艺术概念及研究进程
民间艺术起源于蒙昧的原始文化,但其概念的出现却是19世纪中叶后的事情。民间艺术,通常和民间文学一起,被并称为“民间文学艺术”,其英文是“folklore”,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W·G·Thoms在1846年使用,他在论述民族成员传统、习俗和超自然的观念时使用到这个概念。⑤“Folklore”一词最早由日本学者将其翻译为“民俗”,为我国民俗学界所采用。⑥在我国,钟敬文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民间艺术”的概念,他认为,“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⑦民间艺术研究20世纪初传入中国,诞生礼是1918年2月由北京大学发起的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活动。上世纪50年代,各级文化部门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中专院校对民间艺术进行了一定的调查和整理。一方面,此次调查研究梳理了各地民间艺术线索,整理出来的“集成”系列,对政府组织文艺调演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由于政治思想的导向性影响,整理出来的资料倾向性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学术本身的宗旨,造成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并对原有民间文化生态造成较大的破坏。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受政府委托而下去“采风”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来说,民间艺人只是民间艺术资料的提供者,而非研究对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间艺术的复兴,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得到发展。民间艺术研究长期以来限于社会史研究,研究民间艺术的发生学和变迁史,目的是理解中国社会过去的状况。这一路径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主流。因此,虽然看似民间艺术研究存在多个流派,但是从根本上讲仍沿袭进化论的英国人类学的“遗留物”说。⑧一种倾向是以理论探讨为宗旨,试图从文化特征的角度对民间艺术的性质予以确认,如《民间艺术的文化寻绎》(胡潇,1994),该书从六个方面对民间艺术予以阐释: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艺术与“民间”,民生的显象,主题的文化剖析,艺术造型的图式,民间艺术中的象征。书中还结合部分国外理论对于中国民间艺术作了梳理。也有部分学者继续对民间艺术的“发现”给予细描式的研究,和50年代“采风”式研究方法不同,他们更加注重对艺术文本内部结构的分析。另外还存在一种在商业利益模式的暗示下,将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准商品来阐释,这种方法割裂了民间艺术与民俗生活的联系,不利于对民间艺术的真正阐释。这三种模式多限于艺术层面和民俗层面。与精英艺术相比,其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民间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契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兴起。从国家意识形态来说,民俗曾经被视为“四旧”,现在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候补遗产。民俗从社会边缘(边缘地区、边缘人群)扩及都市主流社会,成为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中心议题。⑨
2000年前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国内流行起来,各相关学科越来越积极地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题。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国际社会提出的重大课题,已经在最近几年成为国际上最受关注的文化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中国首先是作为保护工程被接受的。有的学者把保护工作中的缺失归纳为盲目性、机械性、片面性和近利性,也从正面概括保护工作的若干原则,如生命原则、创新原则、整体原则、人本原则、教育原则。⑩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包括民间传说、习俗、语言、音乐、舞蹈、礼仪、庆典、烹调以及传统医药等。从2001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进行了两次评选,共批准了47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我国的昆曲和古琴。这项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唤起非西方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信心。中国就是这样的受益国。中国政府在2002年十六大发布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2003年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政府的支持便于保护工作的开展,于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我国从2003年启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抢救和保护工程,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陆续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等,一系列保护措施随之出台。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受到多学科关注,包括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行政学、民族学、文学、文艺学等。研究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特点、保护原则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法律保护、商业开发式保护、国外经验借鉴、教育保护等。
相关的专著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云驹,2004);《民间文化保护前沿话语》(白庚胜,2006);《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200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册》(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这四本书以描述为主,理论研究较有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保护的倡议”(1989),提到对技艺拥有者与传播者的保护,主要措施是通过展示、教授学习的方式保证其传承与发扬。但是如何保证传承与发扬,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抢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言》(林秋朔,2004),认为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培养体系,传承渠道不畅,但是没有提出解决措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看民间文化组织参与的重要性》(张笃勤,2005)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民间,主要在民间流布,这种鲜明的民众特色使其保护离不开民间组织;《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探究》(张卫民,2005),提出树立让全民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的教育目标,形成保护模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教育》(汪立珍,2005),认为应该从法规、各级管理机构、教育(全民参与意识)多种方面建立保护机制,而在保护方式上,可分为抢救式保存、博物馆保存、传习机构传承、学校教育(在中小学普及传播传统文化外,还可以在综合大学和艺术院校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课程或专业),逐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学校知识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教育形式》(张卫民、黄文伟,2006),提出开设选修课、讲座等形式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及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三条途径进行传播;《对当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思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谈起》(李天义、何家国,2007),指出民间音乐类文化遗产保护存在教材滞后、师资力量匮乏、没有遗产保护人才培养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旅游教育研究》(刘焱,2007)建议为发展旅游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旅游教育;《民间社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孙晓霞,2007)一文认为,在政府和学术界引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间文化自然存在、自然传承方式的特殊性,真正的能使文化生存下去的“保护”还要多依靠民间社会的力量。除了从通过教育增强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外,一些学者从提高从业者素质来保证传承的角度进行研究,《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思维》(尹凌、余风,2008),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关注传承人现状,并尝试探讨了如何保护传承人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人的培育》(林娜,2008),则从旅游文化和相关学科的建设角度谈传承人的培养等。
3.民间艺术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倾向
随着民俗学对本学科的反思,钟敬文将民俗学定义为“当代学”,“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现代”。近年来,国内关于民间艺术的研究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而呈现出新气象。学者们不再将主要精力滞留于“艺”的层面,而是注意将“艺”与其历史、地理特征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从传承人角度或以地域单元展开的民间艺术研究渐成风气,陆续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成果。一些研究者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方法,致力于对于民间艺术个案的扎实研究,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民间文艺与民俗环境——贵州民间文艺生态研究》(潘定智,1998),探讨了民间文艺和民俗环境的依存关系。他指出,民间文艺存活于特定的民俗环境,民间文艺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它们构成环境系统,和民间文艺组成一个紧密的生态系统。因此,只了解歌本,而不熟悉其产生和延续的环境,就无法感受到民歌的艺术魅力。作者以贵州古歌为例进行了说明,贵州原始信仰、祖先崇拜的盛行,在民歌歌词中的体现;反过来,在红白喜事中民歌的颂唱成为民歌存在的基础。
《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乔健,2002),作者根据乐户的职业特色将其历史上社会地位归为贱民。该书详细探讨了乐户贱民身份的形成,并从当今社会中乐户的分布、婚姻、社会关系、存在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寻找历史上乐户的社会地位痕迹,从而实现透过乐户了解传统中国中底层社会的目的,这也是该书的最终宗旨——建构“底边社会”概念。同年,他在文章《底边社会——一个对中国社会研究的新概念》(乔健,2002)中,对“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进行了更为透彻的说明,他认为乐户、厨子、茶房,连同剃头匠、杂技、说唱艺人、乞丐,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他为之命名为“底边阶级”,这些群体形成的社会为“底边社会”,在文中他论述了“底边”的特征、群体形成、社会地位及特殊的模式造就的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由于杂技艺人的历史社会地位和乐户相同、处境相似,乔健教授在界定底边阶级时将杂技艺人纳入其中,因而对了解杂技艺人历史状况有所帮助,给人启发。
《新中国戏剧史》(傅谨,2002)一书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曲的发展历程的回溯研究。作为该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曲艺艺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经历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艺人社会地位提高、文革期间艺人下放及改革开放后从艺的恢复。这些介绍的意义在于呈现了艺人们在特殊时期的遭遇,缺陷在于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讲故事”,较少听到艺人的主位性声音。
《清人社会生活》(冯尔康、常建华,2003)一书讲到清人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个等级阶梯形态,作为一级,作者简要介绍了清代艺人情况,将其分为:宫廷艺人、隶属官署或民办的艺人、营业戏班和江湖艺人。该书一大贡献是,论述了封建政府对艺人的压迫和艺人低下社会地位的关系的形成。
《有关内蒙古地方戏二人台的田野调查》(邢野,2006),探讨了内蒙古二人台民俗的产生和走西口这一迁移行为的关系,因收成不好或天灾人祸等原因到内蒙古谋生的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地的人,带去的当地民歌、秧歌、戏曲及各种乐器和器乐曲等,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特有的艺术形式——打坐腔;至清代末年发展成为以民歌加舞蹈的艺术表现形式——玩艺儿或称打玩艺儿,即二人台艺术的前身;在吸收了蒙古族民歌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艺术形式——二人台。从而证明二人台民俗是迁移文化的产物。
《从地域文化看天津曲艺说唱观众》(曹宏凯,2008),这篇文章的一个特色是以观众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观众对曲艺的喜爱是曲艺发展的基础。天津观众对曲艺的非地方保护主义传统,为各地曲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该文的立意新颖,从天津建“卫”的地理优势和移民文化的角度追溯天津曲艺的发展,遗憾的是证据略显不足,文章有些单薄。明代天津建“卫”,成为交通枢纽,交通的便利吸引了各地移民的到来,码头等地点成为演出场所,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天津曲艺说唱原生态是由天津的地理位置和移民文化交织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