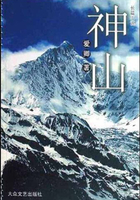特里询问这个年轻男子的时间越长,就越不相信他在说真话。有些事实看起来确凿无疑,并且与他在公寓里找到的物证相吻合:谢莉在大卫的自动应答录音电话机上留了一条信息,她过来见他,他让她进来了,他们交谈过,他开始准备做饭,她脱掉衣服进了浴缸,他去附近的商店购买鲜花和橄榄油。他们中的一个人——不是谢莉自己就是大卫——割了谢莉的手腕,所以她在浴缸里因流血过多而死。
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及其背后的意图却不太明了,大卫对于女友之死的真实情感也让人捉摸不透。有时候,他会落泪,然后生气,恼怒,甚至厌倦——特里真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感到厌倦呢?特里不断地探究整个事件中令他迷惑不解的那些部分。
“我们在你卧室里找到一个袋子,大卫,是个黑色的旅行袋。里面装的是女性衣服、书和杂志。那是她的袋子,还是你的?”
“哦,是呀,我忘了。”大卫隔着桌子怒目而视。“你们去那儿打听了,对吗,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们像一伙窃贼。这难道不犯法吗?”
“我们在调查一起可疑的死亡事件,这是不违法的,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告诉我关于这个袋子的情况。是不是她的?”
大卫转过身去,烦躁地盯着墙。“是,是,当然是她的。她经常用那个袋子。”
“那些物品是她带过去的,还是她收拾好要带走的?”
“什么?”他摇了摇头,好像这个问题毫不相干似的。
“你已经听到了。谢莉的袋子里装满了衣服和书。那么,她打算做什么?与你一起过夜呢,还是回她校园里的宿舍?”
“当然是留下来与我一起过夜。我们就是这么计划的。我打算给她准备一顿晚餐,然后一起过夜。我们经常这样做。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庆祝活动。”
“庆祝?你们庆祝什么?”
“没什么。”大卫皱了皱眉头,好像有点为难。“我已经几天没见到她了,仅此而已。我想她了。”
“好吧。所以,她拿着袋子进了卧室,然后,你们坐下来交谈,准备晚饭的时候还喝了一杯红酒。她是什么时候决定洗澡的呢?”
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嗯,我说晚饭半个小时以后就好,她说……她需要放松一下,凉快凉快,因此,我做饭时,她去洗澡了。事情就是这样,真的。”他愤愤不平地瞪着特里。“明白吗?”
“所以,她就在客厅里脱掉了衣服。”
“什么?”
“你看,她的衣服扔在沙发旁的地板上。她脱衣服的时候,你到底在哪儿?”
“我应该是在厨房吧。我不记得了。”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焦虑,还夹杂着些许不屑。
“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吗?”
“整个?你什么意思?”大卫的目光碰到特里的,然后慢慢地晃开。
“你难道不想看她脱衣服?或者跟她做爱?”
“不想。我正在做饭。”
“我明白了。是她一个人进的浴室。她是在客厅就把衣服全脱了,而人们在城墙上能看得一清二楚?”
“什么?”大卫得意地笑了。“只有像你这样不正常的人才会那么想。你应该多出来走走,警察先生。”
“在你出去购物前,谢莉在浴缸里,对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对。”大卫蜷着右手,把关节按得劈啪响。
“你跟她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了?要说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你冲她喊叫了?”
“没有,当然没有。为什么要那样?”
“好吧,你有没有告诉她你要出去一会儿,留她一个人在家?”
“噢。”他皱了皱眉。“是的,确实这样说过。”
“你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类似……我要出去一会儿,谢莉,去下面的商店里。类似这样的话。”
“那她有回答吗?”
“我不记得了。我想她说了‘可以’之类的话。或许还说了‘时间不要太长’。你知道,如果我能早点回来……”他的声音突然哽咽起来,用手腕擦了擦眼睛,仿佛抹掉了一滴眼泪……
“她可能还活着?”特里不知道这情绪有多少是真实的,还是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过去的几分钟里,大卫瞥了几眼那台磁带录音机,好像在确认自己的言语是不是全都被录了下来。此刻,他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兴许会早点打电话。那些医务人员,他们可能会救活她。”
“好吧。因此,你站在浴室门外,告诉她你要去购物。”
“是的。”
“你没有进浴室里?”
“没有。天哪,这是什么意思?”
特里温和地笑了笑。大卫的谎言马上就会被戳穿,他感到肾上腺素涌上喉咙。
“当时菜刀在什么地方,大卫?”
“我相信你的妻子已经回家了,先生。”特蕾西轻声说。
“但是……谢莉怎么办?谢莉的尸体……我想见她。”
“她在医院里,先生。你妻子已经去过那儿了。”
“是……是的,当然。噢,天哪,我太难过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依我看,安德鲁,你应该给凯瑟琳打个电话。她现在需要你。比任何人都需要你。”那位年轻的黑人女士卡罗尔,从沙发上倾身向前,握住他的手说。安德鲁·沃尔特斯热切地紧握住她的手,凝视着她的眼睛寻求安慰,然后把她的一只手按在自己脸上。这真荒唐,特蕾西想。当然,这个女孩没说错,但是,此时此刻,他需要接受或寻求的这种建议,竟然是他的情妇提出来的……他那可怜的妻子对这一切知道多少呢?好像她的烦心事还不够多似的。
“是。你说得对。”他抬头看着特蕾西。“她什么时候离开的?你觉得她现在到家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先生。”
“在通往韦瑟比的路上。哦,当然,她有手机。我先给她打个电话吧。”他费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打开并拨通了号码。他坐在那里,心烦意乱,目无焦点地呆视着落地窗外的湖面、树木,还有一群兴高采烈喂鸭子的学生。特蕾西与卡罗尔四目相对。她心中的那个问题——他妻子知道你在这儿吗——一定是写在脸上了,因为这位年轻女子轻轻摇了摇头,然后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她的情人开始讲话了。
“凯丝吗?我这儿有一个女警官。我刚听说……那这是真的了,你看到她了……哦,天呀……不,当然,她不会……他在那儿做什么?她说他们分手了,是吗,上周末?……我知道,我知道……你认为他不会……天呀!凯丝,你告诉警察了吗?他们怎么说的?……听我说,我这里有一个警察,我会问的。”
他转身面向特蕾西。“她认为她是被谋杀的。被她的男朋友大卫谋杀。”
“是的,先生,我知道,她告诉我了。我们现在不要抱任何成见。”
“但是——她说他是唯一和她在一起的人!”
“是的,先生,看起来是这样。当然,我们会调查所有可能性。”
“天哪!”安德鲁·沃尔特斯茫然地转身对着手机。“他们说正在调查。是的,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儿?……简和你在一起?……是的,我会去那儿。但是,凯丝,我想先见见她。我必须见她。然后我会直接回家……不,我在工作。只有我和那位女警官。凯丝,我会尽早回家。”
他放下电话,把脸埋在手里。半分钟后,他抬起头,脸色因为震惊而发白。“我必须去医院见我女儿,我去开车。”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特蕾西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胳膊上。“我开车送你吧,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还处于震惊中。”
“什么?没有,我很好。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
卡罗尔·威廉姆斯迅速站了起来,挡住他出门的路。“她说得对,安德鲁,确实,你现在的状态不佳。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开车送你,但你跟这位女警官去可能更明智些。现在不能再在凯瑟琳的伤口上撒盐了,是不是,亲爱的?”
安德鲁·沃尔特斯注视着她,就如同一位饥渴的人看到海市蜃楼似的。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好像不太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我的意思是,是的,可以,你说得对,当然你是对的。”她用胳膊抱住他,他也紧紧地搂着她。
“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他们告别时,特蕾西走了出去。
“菜刀?你到底在说什么,菜刀?”
“这把菜刀。”特里从衣服口袋里取出装在证据袋里的菜刀,放在桌子上。“今天下午,我在你浴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它。你认得吗?”他密切注视着大卫的反应。
“刀……我不知道,我可能认得,或许吧。”
“这是你厨房里的菜刀,对吗?是你用来切菜的那把刀吗?”
“可能是,是的。看起来是的。”
“这也很可能是用来割谢莉手腕的那把刀,因为它是在浴缸旁边的地板上被发现的。你觉得呢,大卫?”
“嗯,如果是在浴缸旁边找到的,那就很有可能。”
“但是,早些时候,你还在厨房里用它。”
“那又怎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问你,你出门前与谢莉谈话时,菜刀在什么地方,大卫,你明白吗?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从厨房到的浴室?”
“嗯,我不知道,对吧?我怎么会知道?”
“你跟她讲话时刀不在手上吗?”
“没有。没有。刀当然是在厨房里。”
“那么,你没有把它带进浴室?没有无意中把刀留在那儿?”
“没有,当然没有。我没有去浴室。我告诉过你。”
他们四目相对,特里等待着,心里断定,这个时刻,如果一个人是无辜的话,他可能会反驳,并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卫与他的目光相遇,但什么也没说。
“好的,大卫,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后来你出去了,去了附近的小店,买了鲜花和橄榄油。你跟那儿的什么人说过话吗?”
“是的,那位印度哥们儿,他是那家店的老板。”
“他以前见过你,是吗?他认识你吗?”
“是的,肯定认识。我经常去那儿。”
“你跟他聊了什么吗,一些他会有印象的事?”
“哦,我们聊足球了。他对足球很热衷。你知道,昨天利兹队击败了阿森纳队。他有埃兰路球场的季票。”
“你们还聊了其他什么吗?”
“是的,嗯,我想他还问了那些鲜花。问我为什么买花。该死……”他又用手腕擦了擦眼睛。“我很抱歉,老兄,我……我,我告诉他鲜花是用来庆祝的。庆祝谢莉回到我身边。不是为了该死的葬礼,天哪。”
“那么,他会记得这些吗?”
“是的,是的,他喜欢谢莉,对她特别有感觉。说我很幸运,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一个像她这样的姑娘。不过现在他不会再这么想了。”
“这次谈话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我又没戴该死的秒表,对吗?就几分钟吧。”
“回来的路上你还碰到过别人吗?”
“没有。我直接回来了。”
“那么,你离开了多长时间,你愿意说说吗?我知道这很难,年轻人。我只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时间。”
“十分钟。或许一刻钟。”
“你回到公寓后,接着做什么了?跟我一步一步地讲,我想了解整个过程。”
大卫深吸了一口气,好像在为将要面对的事情鼓足勇气。“我锁上门,走了进去,把橄榄油放进厨房。然后,把鲜花插在客厅桌上的花瓶里。然后——你知道,因为那些钟,公寓里的声音大得可怕……”
“什么钟?”
“大教堂的钟,你知道,他们在进行什么宗教仪式,所以敲钟,这很令人厌恶,你根本就无法思考。总之我喊了谢莉,说我回来了,但因为钟声,她估计没有听到,于是,我打开浴室的门,发现她……”
他停顿了一下,擦了擦眼睛,这一次,特里仍然不能确定,这到底是真实情感还是表演出来的?但是,他也必须表示同情,说不定这盘磁带稍后会在法庭上重放。
“基德先生,我知道这很难,但你能否准确地告诉我,你发现谢莉的时候,她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嗯,她看起来像死了一样,不是吗?浑身是血。因此,我拨打了999。接着,当我跟电话里的女人讲话时,谢莉动了动,我知道她没有死,于是,我……”
“她动了动?”特里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这让他有些震惊。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她还活着。我想……我想她看到了我。”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嗯,我当然试着抢救她。就是这样……”他摇了摇头。“很难记起来了。”
“你当时肯定很震惊。”
“震惊?是的,当然我很震惊。”大卫的眼神看起来很茫然,似乎看不见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只看到脑海中的影像。他此时的表现看起来很真实,但特里还是拿不准。这也可能是一种强烈的幻想,第一次让他编的故事显现出来。这个男孩是他所声称的那样因为发现惊悚场面而震惊吗?还是这个惊悚场面根本就是他亲手造成的?
“你最初看见她时,她的头在水下吗?”
“我想是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她整个头歪向了一边,你知道,软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一只眼睛在水下面,我走过去,扶起她的头,我确实这样做了,接着,我试图把她整个身子从浴缸里弄出来,但是做不到,因为太滑溜,也太重了。这太可怕了,我做不到,因此……我全身是血,现在还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让人感到恶心……”
“那么,你后来是怎么做的?”
“嗯,电话那头的女士告诉我要努力止血,于是,我去厨房的橱柜里拿来一个创可贴,但是没用,我贴不上,不管怎么说,创可贴也太小了,血流得到处都是,你知道,到处滑腻腻的,我感到很恶心……接着,医务人员来接替了我。但是,他们也救不了她,对吗?因此,责备我也没用。他们接受过一整套培训,但是也救不了她。为时太晚了。”
他现在看起来动了真感情。但是,大多数人回忆起死人时,都不能处之泰然。甚至杀人犯也可能会为他们的受害者哭泣。特里曾经看到过那样的情境。
“好吧,基德先生,我再问一个问题。这把菜刀。当你进到浴室里时,你看到菜刀在地板上吗?”
“什么?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我的意思是,如果菜刀在那儿,我想我一定会看见,但是,我当时在看谢莉,对吗,不是在看菜刀。”
“但是,你有没有把刀捡起来,或者是用任何方式触碰过刀?”
“把刀捡起来?没有,为什么我要那么做?”
“你可能想移开,把刀放到别的地方。”
“不。不,我想我没有那样做。我不记得任何与刀有关的事情。”
“你确定吗?”
“是的,我确定。我要那把菜刀干什么?天哪,我正在努力救谢莉,不是吗?不是要杀死她。”
“是的。”屋里突然安静下来。特里默默地看着这名年轻男子,磁带在录音机里静静地转动。他在撒谎,特里对此很有把握。但是没有证据,他的叙述看起来也言之有理。因此,如果他自己不承认有罪的话,特里和他的小组就不得不想办法去证明。他们必须仔细调查所有的证据——搞清楚菜刀上留有谁的指纹,弄明白公寓里的衣服和其他物品上能推断出什么结论。很多结论需要依赖尸体解剖以及特蕾西从女孩父母那儿得到的信息。而且,还有大卫的不在场证明。那天下午,有人在当地的商店里看到他了吗?如果看到的话,他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他看起来是哀伤、焦虑、异常活跃——抑或是相当正常和平静?
但今晚,特里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
“好吧,大卫,我明白这一切都很艰难,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现在打算提取你的指纹以便排除嫌疑。同时,纽博尔特警员会待在这儿,把你的陈述整理出来,你可以通读一遍,如果你同意他写的,就在上面签字,可以吗?如果你不同意某些内容的话,我们还可以改。我们会给你一份复制的磁带。就这些了。询问结束,现在是……”他看了一下手表。“10点37分。你在陈述上签完字后,我会给犯罪现场行动组打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检查完你的公寓。如果查完了,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想办法。”
然后,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孩子们了,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