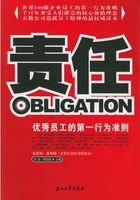四十年前,也就是公元一九六九年秋天,因珍宝岛事件的升级与引发,沈阳军区所属各兵种,大批官兵到北大荒转业。
我所在的部队是38军,驻吉林省蛟河,这是一支在朝鲜战场上最有名的部队。接到命令,我们连队直接转业到萝北县境内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第十三团,也就是现在的宝泉岭农场管理局延军农场。该场场部原来设在延兴村,紧靠黑龙江的江边。战争的需要,场部向西迁移了四十里,撤到托罗山中的洋灰垛子附近。
场部搬迁,住房紧张,再加上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当我们连队赶来的时候,现有的居民点儿早已经人满为患了。放眼望去,道路两旁到处都是帐蓬,人头攒动,喧哗声不止,姑娘们的乳罩和裤衩子就在地头的包米桔杆上晾着,且官兵正在一批批地涌来。别说是生产和战备训练,平时生活都已成了问题。在动员会上,兵团首长挥着胳膊喊道:“去荒原上安家嘛,把狼群赶走,那儿就是家园,野狼有什么可怕的,冲锋枪一响,吓出它们的尿来。但是,能不放枪,尽量还是不放,边防线上嘛,别节外生枝惹出来麻烦。你们都是军人,军人的义务,就是屯垦戍边,保家卫国。”
那是一个讲政治的年代,尤其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理由拒绝其安排。按照兵团统一的规划,我们连队到望江峰下面鸭蛋河西岸的荒原上建点儿。
“现在传达任务,”场长老白一脸严肃地说道,“鸭蛋河西岸是有名的狼窝,当地人又称那儿是野狼谷。十年以前,北京门头沟来的十三名支边青年,不了解情况,去河西岸规划,可是过河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九男四女,十三条人命,都让野狼一宿给嚼了!这次你们去建点儿,千万千万要小心哪!特别是孩子和家属。”白场长无可奈何地说,“我建议孩子妇女暂时先留在场部,等环境好了,家属再上去。”白场长又摇了摇脑袋,叹息了一声,双眼里噙着忧虑:“住房太困难啦,实在不行呢,家属就到我家里去住吧。没办法,就挤一挤吧。”
白场长所说的家属,是指连长王大奎的爱人周彩霞和他们一岁半的儿子王军军。见场长叹气,王连长就说道:“算啦,一块儿去吧。二十多人,还有三支枪呢。我就不信,狼牙比我们的刺刀还硬。”
场长一直把我们送到上路的叉道口。
三辆马车拉着帐蓬和所有的物资,离开场部,沿着鸭蛋河右岸,浩浩荡荡奔望江峰进发。
实际上我们这个连队只是一个排的建制,包括连长,三十人还不到呢。转业以前都提了一级,排长变连长,我们几个班长也变成了干部。
说实话,不转干我就得复员回老家了,我老家是大山那边嘉荫县乌拉嘎公社新立村的,都住江边,离萝北县很近。如今提干再转业分配到农场,如果是复员,那就得回农村去,农场与农村有一定的区别,农场开工资吃商品粮,回农村挣工分就是彻底的农民了。不过,当时我也有回农村的打算,我们老家的土地宽裕,资源丰富,尽管是农村,但也不算贫穷,况且我还有狩猎的技能,真要是复员回老家可能会更潇洒,也是父母们求之不得的。回老家还有一个念头,主要是结婚,未婚妻曾经到部队来过,盼我复员,双方别再熬着,村里同她一般大小的姑娘,都已结婚生子,有的孩子已经满地爬了。我也不想再过这大兵的生活,文化低,提不了干,早早晚晚也得复员,晚复员还不如早复员呢,继续再干,尽的也是义务。可是,没有想到突然接到通知,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农场,我们几个班长,同时转成了干部。天赐良机,珍惜好这次机会吧,即便进狼窝里安营扎寨,爬摸滚打,我和我的战友积极性也很高。
逆流而上,道路崎岖,马蹄声声,车辆滚动,路两旁到处是深深的杂草,高高的灌木,随风不时嗅到浓浓的膻味,同时也能看到一堆堆狼粪,拂扬着的狼毛和白花花的骨头,有的骨头早已经发霉,分不清到底是人骨还是兽骨,阴森森的,特让人恐惧。就依仗人多,如果人少了真就不敢走这条路呢。望着道边的骨头,我们猜测很可能是人骨,因为在出发以前,白场长就已经提醒了我们:“你们今天要走的那条道,是当年抗日联军出山进山必走的道路,当年,那一带多次发生过激战。路旁的骨头,基本上都是汉奸们的骨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激战的双方,我方人员牺牲后,尸骨很快就被掩埋掉了,建国后又统统迁移到了烈士陵园。日本小鬼子的尸体,人家当时就托运回国了,而只有伪警察和伪满军的尸体无人管顾,腐肉喂了秃鹫和乌鸦,骨头多数都被野狼嚼了,没嚼碎的骨头就在那儿扔着,也许这就是当汉奸应有的下场。”
后来,我核实过资料,对白场长的说法表示有些疑问,因为资料记载:在萝北县境内,抗联三军和六军的活动多数都在黑龙江沿岸,这有利于我军转移时方便,六军军长夏云杰,当年就是在我们脚下这条崎岖的路上牺牲的。当时这一带伏兵特多,警卫团全部战死,双方尸体无数。在那个年代,敌强我弱,烈士的遗体谁又来掩埋呢。如今裸露在地面上的骨头,说不定就是烈士们的遗骨,风吹雨淋,灵魂不得安宁。
我一边走路一边在想,等过些日子,大家都安顿了下来,我就找上几个战士,拿上锹镐,把这些骨头统统都埋掉,入土为安。再说了,民族矛盾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尽管面对汉奸的骨骸,后人会有许多寒心的解读,但我想还是用我们的善心良知把它埋掉吧,用我们手中的锹镐送汉奸的骨头与他的灵魂一道归宿到地狱的尽头。
狼粪、狼尿、兽毛和骨头,总让人恐惧又沉甸甸地压抑,但更没有想到,突然传来吱哇吱哇的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大伙不由得紧张起来。随着狼叫,一只大鸟呼啦啦跃起,旋着一股巨风,弄得杂草和灌木猛一阵子晃动。抬头望去,河面上空跃起一只大鸟,它全身漆黑,光秃秃的长脖子紫红,眼睛贼亮,咄咄逼人,锐利而又粗大的爪子,死死抓着一只浅灰色的小狼崽,但见那狼崽拧曲着身子吱哇吱哇哀叫。
河那岸随之有老狼嗥声传来,苍凉,无奈,急切又痛苦。嗥叫的老狼十有八九可能是只母狼,如果没有灌木丛遮着,肯定能看到它绝望的影子,仰头面冲高空,一声声哀叫。
近在迟尺,河水那边母狼在哀嗥,头顶上的大鸟双爪钳住狼崽张着巨翅腾飞、盘旋,像飞机,大伙儿不由都愣了,都张着大嘴呆呆地望着:“我的妈呀,这是什么鸟啊,巫婆吧,这么大个家伙!”
“咚咚”,突然身后传来了枪声,扭头一看,是二排长宋西枕,人们都习惯叫他宋黑子,他对空中射击刚有点儿得意,前面就传来了车老板的骂声:“妈的,找死呢你,这儿是野狼谷,随意开枪,你不要命了!”话音刚落,我们又看到,高空的秃鹫猛地一伸爪子,野狼崽随即坠落在了河滩上。秃鹫在空中拐了一个急弯,迎着阳光,向东南方飞去。
宋黑子抚枪伸了伸舌头,一脸恐惧,眼睛眯着,他想申辩但最终啥也没说,像个突然间闯了祸的孩子。
秃鹫飞走了,车老板的口气才缓和了下来,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块头,大胡子,大眼睛,眼睛一瞪满脸都是凶气。此刻见众人都有点儿发蒙,他就扬着眉毛晃了晃大鞭,略有点歉疚撇了撇嘴说道:“小爷们儿,看见吧,它狼崽子都敢抓呢,狼崽子有母狼护着它都敢下手,这个世界上它能怕谁呢。这是巫婆,天上的神鸟,别看你们手里有枪,真招惹了它们,那也是个麻烦。我赶了大半辈子马车,出门在外,什么野兽我老孙头儿都不怕,就是这种神鸟,招惹不起啊!”说着狠狠甩了两下响鞭,车轱辘继续滚动向前行进。
马车在道旁的河边停下,我们纷纷向河边跑去,想用河水洗洗手脸清爽清爽精神。在河滩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被摔死的狼崽子全身都是污血,狼皮太薄,秃鹫的利爪肯定已经切透。韩仓用手提着它的后腿:“真不轻呢,白瞎了一张皮子,你看这毛,如果在冬天,能吊两双袜子。”
于老四用手摸了摸狼头,手有些哆嗦,颤抖着说道:“这就是狼啊,除了小时候在动物园,我第一次见到自然界的野狼。这狼崽……”
没有说完,猛然听到河那岸有点动静,惊得扭头,一只白色的老狼倏忽间没了,没有看清,但可以肯定,老母狼是在守护它的崽子,见我们人多,身上还有枪支,母狼就匆忙隐去了。
回到岸上,我们重又上路,大伙儿都在感叹:“母狼怕飞禽,不可能啊”。“你问咱们排长,春木排长,你参军前就是专业猎人,这地方又离你们家不远,这只母狼,为啥它就看不住崽子,让只老雕把崽子给叼了。”
我心事重重,刚要打算回答,车老板在前面就大着嗓门嚷道:“场部领导净瞎整呢。来野狼沟开荒,这不是把狼群往死里头逼吗,逼它们搬家,往哪儿搬啊,能去国外,它们也早走了。多少年啦,我亲眼看到,这些狼是被人家外国狼打败,实在没办法,才在这儿死守。现在可好,你们刚来,还没过河呢,狼群就慌了,连自已的崽子也看不住,生生让老巫婆钻了空子。”说完又狠狠甩了一响鞭,“叭!”的一声,清脆又响亮,“驾!还带着女人和这么小的孩子,万一给吓着了又该怎么办哪!当年的知青就是个例子,十三个坟头,不是照样摆着。别看有枪,到时候也有哭鼻子的时候。驾!”又是一声清脆的响鞭。
我们走远了,身后传来老母狼的嗥声,婉转凄凉,苍凉悲痛。我们不由得回过头去看看,身后是荒原,除了杂草、灌木,能看到的仅仅是烈日下的天空。北大荒的天空湛蓝湛蓝,没有云彩也不见尘埃,只有仿佛是哭泣的狼嗥声在荒野上回荡。
听到狼哭,想想其惨状,心里都有些说不清的沉重和极心烦的压抑。
我心里头突然觉得有点儿后悔,后悔不该来国营农场转业,我毕竟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原籍相对都贫穷,转业来农场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我原籍本来也属于北大荒呀,来农场转业纯粹是多余。再说了,参军以前我就不再狩猎,这也是我父亲的志向和决定,可这次来开荒,又得与狼群发生冲突。我心里压抑,精神上郁闷,事与愿违,后悔不该来十三团转业。
可是,回头路断了,档案手续都已经办定,再回山那边,只能算个逃兵,不如意也得硬着头皮干了。
突然,又传来此起彼伏的狼叫声,像是一群狼,好像要将我们包围似的。我的后脊梁有凉风嗖嗖嗖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