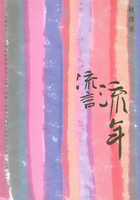有了这些积蓄,
同伴们都把我看作高不可攀的百万富翁。
看到这一大笔钱我也很开心,
每天都把它们数来数去。
我幻想着小屋里的家具、水桶、
折叠小刀、新鞋子、衣服和帽子,
这些东西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心中十分得意,
因为我成了贝夫河上最有钱的奴隶。
1845年棉花受灾被毁——圣玛丽教区急需劳力——一群奴隶被送去那里——队伍前进的队形——大高地——在萨尔河边受雇于特纳法官——在蔗糖厂里当工头——周日的劳作——奴隶的家具;购买的途径——森特维尔的雅尼老爷家的聚会——运气好——蒸汽船的船长——他不同意偷渡——回到贝夫河——看见提贝茨——帕西的忧伤——骚乱和平静——抓捕浣熊和负鼠——负鼠的狡猾——精瘦的奴隶——鱼栅的外形——纳奇兹人被杀——马歇尔挑战埃普斯——奴隶制的影响——对自由的热爱
埃普斯住在贝夫河口种植园的第一年,也就是1845年,泛滥的毛虫几乎毁了整个区域的棉花。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奴隶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闲着。后来传言说,圣玛丽教区需要一大批劳工,而且工资很高。这个教区坐落在墨西哥海湾岸边,离埃文耶尔斯大概有一百四十英里。教区里有一条名叫里约台客河的大河,它经过圣玛丽教区流进海湾。
收到此类消息后,一些种植园主做出决定,派一批奴隶到圣玛丽教区的塔克卡帕,把奴隶们租到甘蔗田里干活儿。就这样,九月里,在霍姆斯维尔聚集了一百四十七个奴隶,艾布拉姆、鲍勃和我都在其中,这些劳力中将近一半是女人。埃普斯、阿朗索·皮埃尔、亨利·托勒以及埃迪森·罗伯茨是选出来与奴隶同行并看管奴隶的白人。他们有一辆两匹马拉的小马车,还有两匹上了鞍的马专供他们使用。罗伯茨老爷的奴隶约翰赶着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马车装着毯子和补给。
下午两点钟左右,吃过饭,做好准备之后,队伍就出发了。派给我的任务就是照管毯子和补给物品,防止在路上遗失。小马车在前面领路,大马车跟在后面;奴隶走在后面,两位骑马的老爷走在最后,队伍从霍姆斯维尔出发了。
当天晚上,我们走了十到十五英里,来到一位麦克罗老爷的种植园,队伍接到命令停下休息。我们搭起火堆,每人把各自的毯子铺开在地上,躺在上面休息。白人老爷们在大马车里过夜。天亮前一个小时,监工们甩着啪啪作响的鞭子把我们叫醒,要求我们起床。奴隶们卷起毯子,纷纷递给我,我把毯子放在大马车里,队伍又开始前进了。
第二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我们浑身都湿透了,衣服上浸透了泥和水。我们赶到一个开阔的避雨处,那是一个废弃的轧棉坊,躲在下面还能勉强避避雨。由于地方不大,不够所有的人躺下。一晚上我们只能蜷缩在一起,第二天一早又和往常一样上路了。一路上,奴隶一天只吃两顿饭,和在木屋时一样,我们煮熏肉、烤玉米饼吃。我们走过拉法耶特维尔、蒙特斯维尔、新城,又经过森特维尔,鲍勃和艾布拉姆大叔在这里被雇主带走了。队伍越往前走,人数就越来越少——几乎沿途每个蔗糖种植园都需要一两个奴隶。
途中,我们经过了大高地,或者叫大牧场。那是一片广阔的平地,景色十分单调,几乎没有树木,除了偶尔在一些破烂荒废的房子旁边有那么一两棵。这里曾经人口稠密而且发展得不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荒废了。现在这里零散的居民主要靠养牛为生。我们路过时看见很多牛在那里吃草。站在大高地的中间,会让人以为自己身处海洋,一眼望不到陆地。放眼望去,目光所及全是一片萧索和荒芜。
我的雇主是特纳法官,他是个有名望的种植园主,在萨尔河口拥有大片的地产,离海湾只有几英里。萨尔河是个小溪,最后流入阿查法拉亚海湾。几天以来,我一直在特纳法官家里忙着修葺制糖厂房,后来我和其他三四十人拿着甘蔗刀被派去地里砍甘蔗。我发现,砍甘蔗要比摘棉花简单多了,而且很自然就能掌握,没过多久我就能和砍甘蔗最快的人保持一样的速度了。但是还没等砍甘蔗的季节过完,我就被调回到甘蔗厂当工头了。从制糖开始一直到结束,榨糖和熬糖的过程就日夜不停。他们把鞭子交给我,命令我用它来教训那些站着偷懒的奴隶。要是我不严格执行命令,自己也会挨鞭子。除此以外,我还负责在规定的时间组织和解散不同小组的奴隶干活。我没有规律的作息时间,而且每次只能稍稍睡一小会儿。
我猜想,其他蓄奴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一样,都允许奴隶保留周日劳动所得的报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买得起一些奢侈物品和便利用具。北方的黑人被贩卖或者绑架后,被运到贝夫河上的木屋里,身上根本没有小刀、叉子、盘子、水壶,或是任何陶罐形状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样式的家具。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奴隶唯一的家当就是一个毯子。他可以把它裹在身上,站着或是躺在地上或木板上。他可以找个葫芦来盛饭,也可以直接从玉米棒上啃着吃,随他自己喜欢。要是问老爷要一把刀、锅子,或者这类小的便利用品,只会受到嘲笑或者被主人踹一脚。木屋里任何看得见的小用具都是奴隶用周日挣的钱买来的。尽管从道德上讲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准许奴隶在安息日干活儿挣钱的确是奴隶改善生存条件的福音。否则,奴隶根本没有办法购买生活必备的器具,而他们都要自己做饭。
在制糖季节,甘蔗园里的周末和平时的工作日没什么区别。大家都明白,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安息日干活儿,也同样清楚那些雇来的奴隶,比如我雇给了特纳法官,以及后来几年新来的雇奴,都应该得到一定的报酬。在采摘棉花最繁忙的季节,老爷们也会经常要求奴隶周末加班劳动。这样奴隶就能挣些钱买小刀、水壶、烟草等必备的东西。女人更愿意放弃烟草这样的奢侈品,把她们那点儿积蓄花在购买花哨的丝绸上,好在过节的欢乐时光里点缀自己的头发。
我一直在圣玛丽教区待到1月1日,这时我已经攒够了十美元。这些都归功于我的小提琴,它是我积蓄的来源,长久以来陪伴着我,也在为奴的十二年里抚慰我的忧伤。森特维尔的雅尼老爷在种植园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白人宴会,那地方就在坦纳老爷种植园附近的一个村子。我被叫去为他们拉小提琴,参加宴会的人都很喜欢我的演奏,于是赏给我一笔钱,总共十七美元。
有了这些积蓄,同伴们都把我看作高不可攀的百万富翁。看到这一大笔钱我也很开心,每天都把它们数来数去。我幻想着小屋里的家具、水桶、折叠小刀、新鞋子、衣服和帽子,这些东西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心中十分得意,因为我成了贝夫河上最有钱的奴隶。
里约台客河上有开往森特维尔的船只。就在那里,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走到一位蒸汽船船长的面前,乞求他把我藏在船舱里。我之所以敢冒险走这一步,是因为之前我无意间听到他说话,确信他是北方人。我并没有向他细述我的人生经历,只是热切地表达了自己想要逃离奴隶制的束缚,逃到一个自由州去。他很同情我,但他说根本无法避开新奥尔良海关官员的严密检查,一旦被查出他就会受到惩罚,轮船也会被没收。我再三的恳求让他心生怜悯,但凡他能确保自身安全,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我不得不压抑住内心刚刚燃起的那团照亮胸膛的火焰——自由的希望,转身再一次走进令人绝望的无尽黑暗之中。
这件事刚过去,奴隶们就在森特维尔集合,有几位奴隶主来收奴隶干活挣的租金,我们又被遣送回贝夫河。在返程途中的一个小村庄里,我一眼瞥见了提贝茨,他正坐在一个肮脏的杂货铺里,看起来没精打采、了无生气。我敢肯定,暴躁脾气和烈酒早已让他成了废人。
我从菲比大婶和帕西那里听说,我们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帕西的麻烦越来越大了。这个可怜的女孩真是可怜。“老猪嘴”(埃普斯的外号)在别的奴隶休息的时候,常常凶狠地殴打帕西,打得比以往还要厉害。只要他从霍姆斯维尔喝得烂醉回来——在这段时间他常常这样——为了让太太高兴,他会鞭打帕西,把她打得痛不欲生,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范围,而他自己才该为此事负主要责任。但在他清醒的时候,他不会总是顺着太太无尽的报复心理。
只要除掉帕西,把她安置在看不见的地方,不管是卖掉、杀掉,还是用其他方式都行,后来这几年,这已经成了萦绕在太太心头的想法。帕西小的时候是个宠儿,就连大宅里的老爷也很喜欢她。因为与众不同的活泼和讨人喜欢的性格,帕西特别受宠,也深受喜爱。听艾布拉姆大叔说,太太年轻的时候还常常把她叫到走廊,喂她饼干和牛奶,像逗顽皮的小猫一样逗她玩耍。但是这个女人的性情发生了巨变。现在,只有愤怒这个黑色的魔鬼盘踞她的心田,用她那喷射毒液似的目光直视帕西。
从本质来说,埃普斯太太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只是她的心里充满了邪恶的嫉妒。但是除此之外,她性格中还是有很多值得人仰慕的地方。她住在切尼维尔的父亲罗伯茨先生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受到整个教区居民的尊敬。年轻时太太曾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她长得很漂亮,有修养,平常脾气很好。除了帕西,她对我们都很好,常常趁老爷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给我们送些桌上的美食。要是换个年代,而不是贝夫河岸现行的社会制度,她一定是个公认的优雅、迷人的女士。可她运气不佳,成了埃普斯的妻子。
虽然埃普斯尊重妻子,也爱妻子,但是他本性粗糙,性格中的自私总是凌驾于夫妻感情之上。
他像卑微生物那样去爱,
但他的心和灵魂无比自私。
只要不用花太多钱,他很愿意满足她的突发奇想——答应她提出的要求。在棉田里,帕西能比得上两个奴隶。哪怕用再高的价钱,老爷也不愿意卖掉帕西。因此,老爷不会考虑卖掉帕西这个主意。太太可不这么看,这个南方女人的傲慢劲儿一上来,看到帕西就妒火中烧,只有活活踹死这个可怜的奴隶才能让她心满意足。
有时候她的怒火会转向埃普斯,因为他才是引起她憎恨的源头。但最终愤怒的争吵最终会过去,一切又会恢复平静。这时帕西就会吓得发抖,哭得撕心裂肺,因为之前痛苦的经历让她清楚地知道,要是太太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埃普斯为了让她安静下来,一定会答应她鞭打帕西——埃普斯说到做到。就这样,主人宅子里夹杂着傲慢、嫉妒、复仇和贪婪的骚乱和争吵持续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帕西这个头脑简单、天生性格开朗的奴隶,承受了所有家庭风暴的袭击。
从圣玛丽教区回来的那个夏天,我想到了一个给自己补给食物的办法,虽然办法很简单却十分奏效。贝夫河上上下下很多奴隶同胞也开始效仿我的做法,而且带来的益处之大几乎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他们的恩人。那年夏天熏肉生了蛆虫,要不是饿得快要发疯,我们实在没法把肉吞下去。每周肉类的供应也不够我们吃。不光我们,整个区域的奴隶都是早在周六晚上之前就吃完了这周的补给,或者就是剩下的熏肉上爬满了令人作呕的蛆虫,让他们不得不去沼泽里捕捉浣熊和负鼠。不过这要等到晚上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之后。有些种植园主的奴隶一连几个月都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肉食。我们捕猎没有受到禁止,因为这样熏肉房也可以少熏一些肉,而且猎杀浣熊也可以让玉米秆少受些破坏。奴隶们手拿木棍,牵着猎狗去捕捉浣熊,因为他们不允许奴隶使用枪支武器。
浣熊的肉很可口,但是与烤熟的负鼠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美味了。负鼠是又圆又长的小动物,一般皮毛颜色发白,鼻子长得像猪,尾巴又特别像老鼠。它们在树根和橡胶树上打洞,动作缓慢笨拙。但是它们又很狡猾机灵。只要感受到一根小棍轻微的咔嚓声,它们就会在地上翻过身来装死。要是捕猎者离开它去追另一只负鼠,没有用力扭断它的脖子,很可能等他回来时,就再也找不到这只负鼠了。这小小的动物比敌人聪明多了——它们“玩装死”——又逃掉。但是干了一天的累活儿,疲惫的奴隶们打不起精神去沼泽捕猎来当晚饭,大多数时候,奴隶们宁愿不吃晚饭就躺在木屋地上睡觉。从奴隶主的利益出发,奴隶不应该因饥饿而损害身体,而同样出于奴隶主利益的考虑,奴隶也不应该因为吃得太多而变胖。奴隶主认为,身材偏瘦、精干的奴隶才最适合干活儿,就像赛马一样。在沿雷德河两岸的蔗糖园和棉花种植园里常常能看到大批精干的奴隶。
需求是发明创作的源泉。我的木屋离河岸不远,所以我决心做一个捕获食物的工具,这样就不需要大半夜往树林里钻。那就是做一个捕鱼栅。我先构思好应该怎样做,第二天开始着手制作。也许我不能全面准确地告诉读者它的构造,但下文的描述也能大概提供它的外观特征:
先做一个两到三英尺宽的框架,可以根据河水的深度适当调整框架的高度。然后在木框的三面钉上板条,板条不能钉得太靠近,不然水流无法自由穿过。在木框的第四面的两端木桩上刻上凹槽,再安上一道能在刻槽内自由滑动的门。然后再安装一个可以自由移动到顶部的底板。在底板的中央钻一个螺孔,将一根手柄或者圆棍的一端插入孔中,另一端松松地固定在底板背面,要保证它能转动。手柄从移动底板的中间向上一直升到木框顶端,也可以超出一些。手柄的上下都钻上小孔,里面插上小棍子,并让它们伸向各个方向。只要有鱼游过,不管是大鱼还是小鱼,一定会碰到木棍。最后再把框架放进水里,并固定好。
把鱼栅的小门拉起来并用一根棍子固定好,把棍子一端放在内侧槽口里,另一端放在手柄上刻的槽口,这样就安好鱼栅了。用一小撮湿的玉米面和棉絮揉在一起做成诱饵,变硬后再放进鱼栅里面。要是有鱼游过升起的小门去咬鱼饵,肯定会碰到其中一根小棍,带动手柄转动,这样就碰倒支撑小门的棍子,门掉下来就能把鱼关进来了。抓住顶部的把手,就能把活动的底板提出水面,把鱼取出来。也许在我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这样的鱼栅,但是我从没见过。贝夫河里鱼群众多,体形偏大,十分美味。从那以后,我和同伴们就很少缺鱼吃。就如同打开了一个矿藏,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食物来源。直到今天,那些在岸边饱受辛劳、忍饥挨饿、遭受奴役的非洲儿女们从没想过要去获取这条缓慢的河流里丰饶的物产。
就在这段时间,我们旁边的种植园里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这件事显示出那里的社会状况,以及有仇必报的风气。在河口对岸,正对着我们奴隶住宿地方的就是马歇尔老爷的种植园,他的家族是全镇最富有的贵族。
一天,一位来自纳奇兹附近地区的先生与他商量想要购买这片地产的事情。有人急匆匆地跑来报信说马歇尔老爷园里正在打架,打得很厉害——都流血了——要不马上把双方拉开,结果会很严重。
我们匆忙赶到马歇尔老爷家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大吃一惊。一间房间的地板上,横躺着那位来自纳奇兹先生的尸体,而马歇尔先生浑身满是伤口和鲜血,怒火冲天,来回踱步,“大喊着威胁和杀戮的话”。原来他们在商谈过程中产生了矛盾,接着两人开始大声争吵起来,拔出各自的武器,开始一场恶斗,可悲的结局就这样发生了。此后,马歇尔并没有被囚禁起来。在马克斯维尔举行了一场调查和审判,却宣布他无罪释放,回到种植园后,他仿佛更受大家的尊敬了,在我看来,可能是因为他的灵魂浸染了同胞的鲜血。
对这件事,埃普斯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陪着马歇尔先生去马克斯维尔,在任何场合都大声为他辩解,但他做的这些却没能阻止马歇尔后来想要他的命。他们两人因为在赌桌上发生口角,最后演变成一场决斗。一天,马歇尔横跨在马背上,手持手枪和猎刀出现在老爷家门口,叫嚷着要他出来决一死战,要是埃普斯不肯出来,以后马歇尔就叫他窝囊废,一见他就会像打狗一样一枪崩了他。在我看来,埃普斯不是因为胆小或是处事小心,而是因为受到妻子影响,没有出来迎接马歇尔的挑战。但是后来两个人又达成和解,从此以后两人的关系很亲密。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北方各州,打架双方都会受到惩罚,但是这种事在南方各州却频繁发生,事后也不会有人关注,更不会有什么评论。每人随身佩戴猎刀,要是两人吵闹起来,就开始相互用刀劈砍,刺杀对方,完全不像文明开化的人,更像是野蛮人。
残忍的奴隶制让他们人性中仁慈和善良的情感渐渐变得残暴。每日目睹受苦难的人——听奴隶们痛苦的尖叫——看着奴隶在无情鞭打下扭动的躯体——被狗撕咬、吞掉——悄然死去,不装棺材也不裹布,直接扔进土里埋掉——要不是因为奴隶制,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惨事;他们也不会如此野蛮轻率地对待人的生命。确实,在埃文耶尔斯教区也有很多善良正直的人,比如威廉·福特老爷这样的人,他们看到奴隶遭受苦难会同情、可怜他们,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有许多敏感、充满怜悯之心的人,他们不会漠然坐视任何由上天赐予生命的生物遭受磨难。奴隶主的残忍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制度的弊端。他们无法抵住周围环境和习惯的影响。从小时起,他们的所见所闻就让他们明白,棍棒就是用来责打奴隶的,长大后他们肯定是无法改变这个观点的。
有仁慈的奴隶主,就有惨无人道的奴隶主。同样有吃得好、穿得暖的幸福奴隶,就一定有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的悲惨奴隶。然而在我看来,允许这些冤屈和残暴存在的制度,是残忍野蛮、毫无公正可言的。有人写小说来描述奴隶卑微的生活,有的真实可信,有的却虚假杜撰。他们常常自作聪明地说什么“糊涂是福”,躺在扶手椅里对奴隶生活的乐趣大谈特谈。就让他们去田里受受苦;和奴隶一起住在小屋里;让他靠吃玉米棒过活;让他亲眼看看奴隶遭受鞭打、追捕、践踏的情景,他们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只有他们了解穷苦奴隶的内心——听听他们隐秘的心声——那些在白人面前不敢说出的话;让他们陪着奴隶在寂静的黑夜中守望——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和对“生活、自由、幸福的追求”,他们才会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奴隶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也都珍惜内心对自由的热爱,就像他们一样地热切。